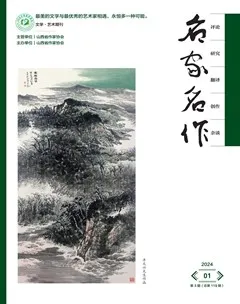《花園茶會》與《從奧米勒斯城出走的人》中幸福和不幸的比較分析
劉一菲
[摘要] 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的短篇小說《花園茶會》與厄休拉·勒古恩的短篇小說《從奧米勒斯城出走的人》對于主題“幸福”與“不幸”的呈現方式具有相似性,即喜與悲的對立之勢相互沖蕩,使得社會背景更為復雜、人物塑造更加立體。從“二元對立”視角出發,分析其間社會環境描寫和人物心理描寫存在的共性特征,由此關聯文本揭秘幸福與不幸分化的普遍成因:傳統規則的絕對束縛壓迫個體自由意志,社會復雜性致使人心多變。二元對立的視角正適用于剖析此類復雜性社會議題,由此人心固有的矛盾特征也得以揭示。
[關? 鍵? 詞] 《花園茶會》;《從奧米勒斯城出走的人》;二元對立;幸福;不幸
凱瑟琳·曼斯菲爾德作為20世紀英國最杰出的短篇小說家之一,以其獨特的藝術構想和對平凡生活細致入微的捕捉為人所知。其優秀作品《花園茶會》在結構上分為中產階級舉辦花園茶會的布景以及意外身亡工人的居住地兩個場景。《從奧米勒斯城出走的人》(下文均簡稱《奧米勒斯》)為美國作家厄休拉·勒古恩的優秀短篇小說之一,其所呈現的主要畫面為“夏慶節”市民的狂歡和一個囚于地下室的孩子的情狀兩類布景。視角所及,發現兩篇小說皆通過對比手法突出共同主題——幸福與不幸,即幸福繁榮的表象下暗藏不幸絕望的社會現實。
在國外,對于《花園茶會》,學者重點傾向于作品間的比較研究,同時突出精神分析理論對人物性格的成因分析,諸如 Vieco, Francisco (2020)將其與弗吉尼亞· 伍爾夫的《達洛維夫人》中所呈現的不同代際女主人間的不完美慶祝活動進行比較分析[1];Mitchell, Moira(2017)從文內細節入手,通過對女主人公的細節刻畫,分析其潛意識暗含內容[2]。在國內,學者的研究方向主要分為三大類:第一類側重于對藝術手法的分析,如象征主義、敘事視角、頓悟等。作品諸如王瑤瑤(2019)對文中“帽子”象征意義的解析[3],余玲玲(2015)從敘事視角入手分析文中選擇性全知視角與人物有限視角的運用[4]。第二類側重于將作者生平與作品主題與人物結合分析。第三類則是運用新的批評理論,如女性主義、結構主義、交際話語進行研究詮釋。學者對于《奧米勒斯》的研究相對于《花園茶會》較為有限,國外學者對該文的研究重點在于揭露其烏托邦成分,如Mamola, Gabriel(2018)從“反烏托邦”角度加以解讀,揭露故事的虛構特征[5];國內學者研究角度相對多樣,多從結構主義、倫理觀、象征意義入手,如葛悠然(2019)的他者倫理分析[6]等。由上可見,對兩部作品的比較分析較為罕見,從二元對立角度出發的分析較少,然因其具有共同主題和相似的藝術手法,所以二者均有從二元對立視角分析的可行性。故筆者將借用二元對立理論,分析兩篇小說呈現的環境對立性與人物對立性,在比較分析中闡述二者共同的深刻主題——幸福和不幸。
一、社會生存環境的二元對立
在對人物生活環境的描寫中,兩篇小說不約而同使用對比手法突出社會矛盾,環境描寫相似度較高,皆呈現“喜”與“悲”對立的特征。
在《花園茶會》中,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生存環境的明暗對比突出了階級差距所致的“喜”與“悲”。故事伊始,晨曦之下的薛家花園便映入眼簾:“溫煦和暖,沒有風,也沒有云,藍天上籠著淡淡的金色的煙靄,……整片草地和種矢菊的深色平坦的玫瑰形花壇似乎都在發光,……玫瑰在一夜之間,開放了幾百朵。”[7]聚焦于此,不難發現作者通過顏色渲染出中產階級家庭明媚光亮的環境,“藍”“金”的色彩映襯著似發光的薛家花園,“矢菊”和“玫瑰”雖未直接提及顏色卻意蘊鮮明。同時,從外至內,從優越的天氣條件到精致的院內布景都在說明這是舉辦茶會的極佳時刻,全家人對此滿懷喜悅與期盼,此之謂“喜”。然而,隨著情節發展,不同的一面漸被揭示。工人斯考特的意外身亡很快將注意力吸引到下層人民的居住場所:“它們是些簡陋的漆成巧克力色的小房子。院子里的小塊地上什么都沒有,除了白菜幫子、病母雞和番茄醬的罐頭殼,……胡同里煙熏火燎,又黑又暗。”[7]上述描寫中“巧克力色”“黑”和“暗”是對工人居住地的色彩刻畫,在這樣昏暗的環境中,隱藏的不僅是極為有限的生存資源,還有凄慘悲涼的人生境遇,此之謂“悲”。
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山上與山下居住布局的對比,揭示了上述“喜”與“悲”的客觀成因。至蘿拉被派去看望逝者家人時,上述場景成因漸得披露:“那些小房子擠在一個胡同里,在山坡下面,坡上是薛宅”“道路白閃閃的,下面洼地上的一座座小房子籠罩在深深的陰影中”[7]。從側面分析可知,山上的薛家無疑是伊甸園般的存在,然而工人階級只配居住在山下擁擠之地,被陰影籠罩。也正是山坡上充足的通風與采光使得藍天綿延、花朵盛開,為茶會的舉辦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天氣條件;相反,山下居所易積水,陰暗潮濕,土壤條件較差且泥石流等自然災害頻發,也能解釋為什么山下房屋呈巧克力色、糧食資源極致匱乏。
《奧米勒斯》中,“夏慶節”游行市民的慶祝與地下室被囚低能兒的悲苦同樣形成對比,空間變換中“喜”與“悲”盡顯。篇章起始是對“夏慶節”游行歡愉場景的極致渲染,自由得以淋漓盡致地展現。“游行的人一路載歌載舞,成群的小孩在隊伍中興高采烈地奔跑,他們的歡笑聲似高翔于空中的燕子的聲鳴一般,蓋過游行隊伍的鼓樂聲與歌唱聲”[8],“那些馬都沒有上鞍具,……它們揚著鼻子,歡騰跳躍,相互炫耀,興奮異常”[8]。高空翱翔的燕子和自由奔馳的馬暗喻參與“夏慶節”的市民,他們心中滿懷幸福與期盼,盛大的慶典活動已然開啟,萬般事物皆似烏托邦般美好。
然而接下來作者并未進一步渲染,而是轉入敘述者干預對該場景進行評述,從而將文本引入了深層意識。“城區街道上聞到的‘德魯斯麻醉藥品散發的沁人心脾的香味”[8],隱晦打破完美的表象。既然這座城市毫無罪惡與痛苦,為何有毒品存在?顯然事實并非表面所見。通過進一步敘述,那個孩子的悲慘遭遇漸被揭示。地下室中“有個上了鎖的門,但沒有窗戶,充滿塵埃的光線從有隙的墻板里透過來,這光線間接來自地窖處某一個結滿蜘蛛網的窗戶……”[8]。在灰塵遍布、空間狹小、潮濕陰暗、臟亂無序的地方卻有個小孩,性別與年齡難以分辨,已然成為低能兒,這一場景顯然與前文所述形成兩個極端,極致的“喜”與絕望的“悲”對比鮮明,不免令人好奇背后原因。
二、人物心理活動的二元對立
在對人物心理矛盾的呈現上,兩篇小說具有相似性,即表面上人物生活在幸福和諧中,實則苦不堪言。因為社會傳統根深蒂固,明知錯誤卻無力改變,由此陷入個人道德與群體利益的艱難抉擇。
《花園茶會》中,女主人公蘿拉深陷于中產階級的物質富足,卻被工人階級美好的精神世界所吸引,萌生了超越階級的想法。然而階級傳統與自身勢微使這鴻溝難以逾越,由此她內心掙扎不已。首先,蘿拉作為中產階級家庭的小女兒,權力的規訓從小便開始,行為舉止應像女主人般規范,所以她在第一次見到工人時就試圖模仿母親的樣子,“努力板著臉,甚至裝作有點近視,模仿著她母親的聲調,但是聽起來非常矯揉造作”[7],企圖用這種方式顯示她的權威性與優越感。在傳統階級認知中,工人本應服務于中產階級的幸福生活,這屬謀生手段,不值得同情憐憫。雖是如此,年幼善良的蘿拉卻并未受階級壁壘的制約。面對她的冷漠,工人們愿對她微笑,這與她所接觸到的同階級“傻頭傻腦的青年們”[7]完全不同,所以她在一定程度上被隨和友好的工人們吸引。并且當她看到“高個子工人彎身捏著薰衣草的嫩枝,聞著拇指和食指上的香氣”[7]時,她吃驚于工人的可愛與細膩,萌生“為什么不能有工人朋友”[7]的想法。認知的覺醒使蘿拉初步懷疑她所在的階級環境和教育思想,這種階級的傳統規訓與個體思想的初步獨立之間的沖突逐漸形成。
隨后,沖突在面臨“鄰居”斯考特意外身亡的消息時進一步顯現,理想與現實的對立使得蘿拉天真的愿望再一度破滅。出于良善,蘿拉認為應該取消茶會,然而“你很不通情達理,蘿拉。那樣的人并不指望我們犧牲什么。要是照你現在這樣,弄得大家都不盡興,那也很不近人情吧”[7],幻想終破滅。面對母親的權威和階級束縛,年幼的蘿拉毫無反抗之力。受困于身份藩籬,與工人成為朋友的美夢破滅,勢單力薄的她想做卻不能做的矛盾心理躍然紙上,最后只得乖乖舉辦茶會。茶會后,應父母要求,帶宴會殘羹剩飯去拜訪死者的家人也并非出于本意,然恰是這次經歷讓蘿拉認清現實。所見殘破、饑寒不堪的工人生活讓她一時間難以接受,心中友善有愛的理想世界不復存在。終兩遍問哥哥道:“人生是不是……”[7]是她對幸福和不幸認知的開始,也是對階級壁壘的真正覺知。
《奧米勒斯》中,離開奧米勒斯的年輕人同情地下室孩子的不幸遭遇,但當個人道德與群體利益沖突時,個體無力感頓涌心頭。當青年去看望孩子后,“他們往往會痛哭流涕,或是悲憤難抑”“有時某個青年男女去看了那孩子之后并不回家痛哭流涕或是震怒發狂,事實上,根本就不會再回家”[8]。由此可見,年輕人有悲憫之心,想要做些什么卻囚于現實,因為“為給一個人創造幸福的機會而破壞千萬人的幸福,無疑是將罪惡引進奧米勒斯城”[8]。文中并未對為何令一個孩子不幸就能換得全體市民的幸福做出解釋,依筆者之見,背后體現的是反烏托邦思想。正如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所呈現的,一種被烏托邦式的平等和集體主義的外衣所覆蓋的極權主義最終將導致一個悲劇社會。事實上,被烏托邦式的自由平等的外衣所覆蓋的現代“文明”也必使人心背離。公民們和孩子一樣并不自由,即使知道孩子是無辜的,但這邪惡的存在是享受整個“文明”的根源。他們因自己的沉默與不作為受到內心譴責,但面對個人道德感的滿足和群體利益的實現時,不是每個人都有勇氣做出選擇。
三、結束語
聚焦“幸福”與“不幸”的二元對立主題,研究發現兩篇小說環境描寫皆含對比,人物心理皆系掙扎矛盾。社會層面的“喜”與“悲”分化明顯,根深蒂固的傳統藩籬與人的新興獨立意識相悖,個體無力感頓然涌現,不覺陷入個人道德與群體利益的矛盾抉擇。
《花園茶會》里中產階級的豪華宴會之“喜”與工人意外身亡之“悲”對比鮮明,女主人公蘿拉享受著階級身份帶來的優越感卻受囚于此,無法實現個人意志;《奧米勒斯》里“夏慶節”市民狂歡之“喜”與地下室囚禁低能兒之“悲”反差強烈,選擇離開奧米勒斯城的年輕人同情地下室孩子的遭遇,卻受囚于現代“文明”實現所必要的暗勢力,無力采取措施。綜上所述,社會復雜性致人心多變性,傳統規訓的束縛壓迫個體自由意志,“二元對立”視角適用于分析此類文本,由此揭露潛在的人性矛盾。
參考文獻:
[1] Vieco,Francisco.(Im)perfect celeb-rations by intergenerational hostesses: Katherine Mansfield's “The Garden Party”and Virginia Woolfs Mrs. Dallowa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2020,20(1): 93-111.
[2]Mitchell,Moira. Hidden in Full View: A Subliminal Reading of The Garden Party by Katherine Mansfield.[J]. English Studies,2017,98(8):995-1003.
[3]王瑤瑤.淺析《花園茶會》中的“帽子”意象[J].文學教育(上),2019(9):50-51.
[4]余玲玲.《園會》敘述視角的探究[J].校園英語, 2015(34):253-254.
[5]Mamola, Gabriel. Walking Towards Elfland: Fantasy and Utopia in Ursula K. Le Guins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J]. Extrapolation: A Journal of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Extrapolation), 2018,59(2):149-162.
[6]葛悠然.直面他者:論《從奧米勒斯城出走的人們》中的他者倫理[J].海外英語,2019(22): 232-233.
[7]Mansfield, K.?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Katherine Mansfield[M]. Wordsworth Edition Ltd,2006.
[8]Le Guin,Ursula. 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M]. New York: Bantam Books,1976:251-259.
作者單位:中國地質大學(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