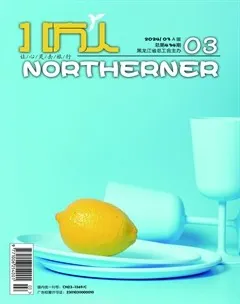老頑童的藝術(shù)之道

童年經(jīng)歷影響一生
我是山東人,一開始讀私塾,每個寒暑假交一塊錢可以進去寫字。先生對我們寫字的要求非常嚴(yán)格。我5歲開始練習(xí)書法,6歲開始畫畫。我很淘氣,先生看我的性格適合練顏魯公(顏真卿)的字,就讓我練顏體。現(xiàn)在來看,不論我后來畫畫還是雕塑,都離不開我們民族的瑰寶——書法作根基。我今年87歲了,寫了82年的書法。我在書法上的成績恐怕更大一些,因為練得早。
6歲的時候,我跑到土地廟里掏土地爺塑像的屁股,掏出來《四體千字文》《說文古籀補》《六書分類》等好幾本古書。那時候我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不知道這些跟書法有關(guān)系,只是把它們當(dāng)成畫來看,很喜歡。到現(xiàn)在,我還是一直把古文字當(dāng)成畫來看待,所以后來創(chuàng)作了《天書》。
離開私塾后,我進了濟南貧民小學(xué),窮人的孩子只能上這個學(xué)校。但是這所學(xué)校很注重教育,學(xué)校當(dāng)時請了很多名人來演講和上課,包括著名學(xué)者趙元任、演員白云、書畫家陳叔亮等名人,我小時候都見過。當(dāng)時的音樂課還聽貝多芬、莫扎特的曲子,但是那時候不知道是誰的音樂。
青少年時期所受的教育和啟蒙能夠影響人一輩子。大家都知道我的畫很多,但是不賣,外面流通的99%的畫都是假的,我的畫全部捐給國家,這跟我小時候所受的教育有關(guān)系。我12歲就參軍了,跟隨的司令員是一位老八路,他對我的影響很大。
后來成立了濟南四里山“烈士紀(jì)念塔建設(shè)委員會”,要修烈士塔,司令員看我喜歡畫畫,就把我調(diào)到浮雕組,跟隨王昭善、薛俊蓮、劉素、張金壽等藝術(shù)家學(xué)習(xí)。我當(dāng)時13歲,一下子認(rèn)識了那么多藝術(shù)家,很興奮,開始接觸雕塑。后來我做了不少雕塑,現(xiàn)在我在國內(nèi)外的城市雕塑有50多座。
因為參與修建烈士紀(jì)念塔,我知道革命成果是多么來之不易。退伍后,我到話劇團表演話劇,之后又當(dāng)了小學(xué)美術(shù)老師。17歲的時候,我一邊教小學(xué),一邊出版了教材《繪畫基本知識》,這個教材很受歡迎。
美院恩師助我成才
后來,我遇到一位蘇州美專畢業(yè)的女老師,她鼓勵我報考中央美院附中。1955年我到北京報考附中時,中央美院的龐薰琹老師親自跟我談話,他告訴我:“你直接考大學(xué)讀美院吧,考不上的話,明年還可以再來考。”我用了21天時間,突擊學(xué)習(xí)高中的功課,最后考了第八名。
在美院,我學(xué)到了很多東西。
龐薰琹老師是我們學(xué)院的院長,在裝飾繪畫上給我?guī)砹撕芏鄦l(fā),我到現(xiàn)在畫的東西都有裝飾紋。
葉淺予老師教我們畫速寫。他說“畫馬三塊瓦”,這個概括提煉影響了我一輩子。受這個啟發(fā),我開始畫牛、畫鹿、畫羊,畫牛是方的,畫羊是六角形的,這是我自己總結(jié)出來的。掌握了這些概括提煉的方法后,我想怎么畫就怎么畫,因為老師教會了我基本的方法。
黃永玉也是給我很大影響的老師。一支好幾個指頭粗的毛筆夠大了吧?但如果用來畫人民大會堂上懸掛的那種大畫還是不夠。那幅巨大的駿馬圖,一個馬屁股就有1.5米,用毛筆根本畫不了,只有用板刷才能畫下來。用板刷畫國畫是黃永玉老師發(fā)明的,再寬再大的地方都可以畫。我跟黃永玉老師學(xué)會了工具改革。
鄭可老師教我造型,我給他當(dāng)助教,學(xué)到了不少東西。我后來這樣總結(jié):“形象只要解決了,材料不是問題。”布的、木頭的、石頭的、草的、燒的、雕的、織的、繡的,都可以做出來。各種工藝材料可以塑造各種不同的造型,只要形象解決了,材料都不是問題。我從老師那里得到了很多這樣的啟示。
我的班主任是周令釗老師,天安門城樓上第一幅毛主席像就是他畫的。他對待我們就像是對待自己的孩子。大學(xué)三年級時他帶領(lǐng)我們參與設(shè)計了人民大會堂。人民大會堂天頂上那個滿天星燈就有他的貢獻。
老師們教了我這么多東西,我當(dāng)然非常感激,但是如果不經(jīng)過自己的實踐,不加以變通,不去創(chuàng)新,也不可能成才。所以在學(xué)校里學(xué)到了東西,到社會上以后要通過自己的實踐,進一步把學(xué)到的東西往前推進,一步、兩步逐漸發(fā)展,才有可能實現(xiàn)更新?lián)Q代。
“陜北老奶奶”的接班人
1977年,我的“藝術(shù)大篷車”開始下鄉(xiāng),這個對我教育非常大。我們走遍了全國,走向了世界各地,雖然也有碰鼻子的時候,也有走得不對勁的時候,但是至今已經(jīng)快47年了,“藝術(shù)大篷車”每年仍堅持下鄉(xiāng),最多的一次走了3萬多公里。我必須腳踏實地,當(dāng)一個接地氣的藝術(shù)家。
1985年,我們到了寧夏賀蘭縣的大山里,看到了賀蘭山巖畫。當(dāng)時,我的藝術(shù)發(fā)展正處在十字路口,我不能總是跟著學(xué)院派教我的寫實主義走,但又沒有找到自己的藝術(shù)方向。我看到賀蘭山巖畫,一下子就開竅了。藝術(shù)到底有法嗎?藝術(shù)無法,無法之法才是藝術(shù)的大法。賀蘭山巖畫就是如此,古人無法,他們畫得那么自由。我回來把桌子一拍,大吼一聲:“這就是我的路!”這些巖畫改變了我的一生。
我的作品為什么后來走向了世界?因為篆字、賀蘭山巖畫,還有古時候的一些文字符號、記號,它們都沒有框框,無論什么時候看它們,都像是在看畫一樣,我一直用這個思路來理解篆字,理解那些無人認(rèn)識的古文字。這不是和我的畫聯(lián)系起來了嗎?一些人留學(xué)歸來,凈想著用國外的藝術(shù)取代中國的藝術(shù),那是大錯特錯,太小看我們中華民族了。藝術(shù)形象的提煉是最難的,沒想到賀蘭山巖畫一下子讓我開了竅,成為我在繪畫、書法上的轉(zhuǎn)折點。
接觸民間、接觸人民,也對我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我對各種不同的藝術(shù)門類都很感興趣,于是到田間地頭向民間藝人學(xué)習(xí)各種民間藝術(shù)技法。下鄉(xiāng)后,當(dāng)然不能一味向人家索取,必須得拿出點東西來和人家交流才行。還要入鄉(xiāng)隨俗,我到新疆唱新疆歌,到了蘇州唱評彈,這樣一下子就和民間藝人融合在了一起。我們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同畫畫,講到傷心事,大家還抱在一起嗚嗚大哭。只有這樣,人家才會和你交朋友,才會把真東西教給你。
我設(shè)計的福娃、國航標(biāo)志等,靈感都來自民間。國航標(biāo)志的靈感來自云南晉寧石寨山出土的西漢中期的青銅鳳凰手杖頭。中華民族有著非常厚重的歷史積淀,到民間去,那里有學(xué)不完的東西,那里有俯拾即是、取之不盡的藝術(shù)寶藏。
藝術(shù)無法,它強調(diào)個性,強調(diào)獨立性,強調(diào)民族性,這三個特點是藝術(shù)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必備條件。
我是從民間藝術(shù)中汲取營養(yǎng)而成長起來的。我覺得,我跟著中國大地上的“陜北老奶奶”們是沒錯的,她們的身后是長城、黃河、長江、喜馬拉雅山……我是“中國的兒子”。我也大言不慚、問心無愧地講:我是中國的藝術(shù)家,是中國“陜北老奶奶”的接班人。
“天書”創(chuàng)作的七字訣
2007年,我耗費34年心血搜集、書寫的古文字圖錄《天書》問世。這些古文字是從散落各地的陶瓷、青銅器、龜甲、石刻等殘片之中搜集起來的,語音、釋義都不可考。
啟功老師生前是全國政協(xié)的書畫室主任,我是副主任。老先生有一次拄著個拐杖,見了我的本子,問:“這是什么東西?我怎么不認(rèn)識?”我說:“這是古文字界的東西,我撿起來的。”他聽了之后,鼓勵我把這些古文字寫下來。他叨叨了不知道多少次,說你一定要把它寫出來。后來季羨林老師、黃苗子老師、李學(xué)勤老師、黃永玉老師都鼓勵我寫,所以我終于寫了出來。迄今為止,《天書》出版了4本,我現(xiàn)在正在寫第5本、第6本。現(xiàn)在“天書”字體在文創(chuàng)中被廣泛應(yīng)用,年輕人很喜歡用這種字體。我還給勞力士表設(shè)計了天書款。我感覺我不是在做潮玩,而是在“玩潮”。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天書”的創(chuàng)作心得,一共有7個關(guān)鍵字——“選、拓、臨、仿、脫、變、飛”。
首先,我們學(xué)書法的時候千萬記住,要選對帖子,這個帖子是柳公權(quán)的還是魏碑,要根據(jù)個人特點來選。我小時候上私塾,先生根據(jù)我的性格特點讓我學(xué)習(xí)顏魯公的字。顏體對我的書法風(fēng)格影響很大。選完之后是“拓”,就是描紅。接著就是臨摹。再后來是仿著寫,也就是不看帖背著寫,還要寫得像“老師”。“脫”是質(zhì)變的前兆,必須脫殼,要有一種信念寫出自己的風(fēng)格來。寫多了以后就“變”了,藝術(shù)要不斷求變,慢慢就成了自己的風(fēng)格。熟練以后就可以“飛”了,自由飛翔,想怎么寫就怎么寫,進入全新的創(chuàng)造階段。
我有一個很深的體會:我們要傳承傳統(tǒng),不要忘了老祖宗。古人寫字的時候,寫法很原始,不管是在骨頭上刻還是在石頭上刻,他們都沒有條條框框,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寫出來的字用現(xiàn)在的審美來看,也會很受感動。但是,傳統(tǒng)也需要發(fā)展,也需要我們?nèi)ブ匦聞?chuàng)造。我們不能老是停留在過去的時代,不能老是畫牡丹、畫蝦米,我韓美林也得跟著這個時代走。
一個民族如果沒落,文化就會衰弱;一個民族如果興旺,文化一定會復(fù)興。文化很重要,雖然看不到、摸不著,但是它實實在在地存在著。
(摘自2023年4月14日《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