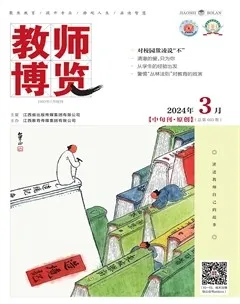《長安三萬里》:揮之不去的萬古愁
沈魯


2023年夏天上映的影片《長安三萬里》引來一陣“唐詩熱”,不少家長和孩子在大銀幕前與片中的人物一道誦讀起了那些千年不朽的傳世佳句。這種銀幕內外的精神互動,再次令我們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詩詞歌賦”產生了深深的審美認同。
一部動畫影片,就這樣集中傳達出了這些生動詩文賴以生成的生命現場,也完成了一次“詩歌唐朝”的想象性滿足。然而詩歌并非本片的全部,《長安三萬里》實現了一次“于無聲處聽驚雷”的故事改編。因為影片本身的故事并不復雜,也不是唐詩的電影版,而是在虛構的高適與李白的命運圖卷里展現出一種驚雷般的永遠的人生困局,那就是“萬古愁”。
李白有詩:“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太年輕的時候,是不會懂這“萬古愁”的。李白開始也不懂,高適也不懂,但后來他們都懂了,不得不懂。人生教會了他們必須與“萬古愁”和解,只有和解后,才會找到自己來時的路。
“萬古愁”最憐“人生苦短”。白駒過隙,時光匆匆,轉眼今日已成昨日,昨日已成回憶。與其痛心疾首于流光的稍縱即逝,喟嘆萬事成蹉跎,不如重新振奮精神,用一種新的姿態、新的風貌投入新的生活。李白驚人的才華與高適從容的堅持都是可貴的資本,策馬偶遇的兩個年輕人,在通向“長安”的道路上,不斷嘗試、拼搏、奮爭、隱忍、冒險……這是萬兩黃金也換不回的寶貴財富。如日中天的帝國,正需這樣有朝氣、有活力、有膽識、有魄力的奮發有為的新青年。然而,現實卻總是不一定讓每個刻苦勤勉的日子都得到回報——李白與高適帶著他們各自的青春沖動迎頭撞上時代的捉弄,搞得滿身傷痛和滿心疲憊。人生數載,寒暑春秋,三萬里志趣,路卻在何方?
“萬古愁”最怕“知己難覓”。在人生的無數困局里,若能得一知己,便會少一些缺憾,多一分希望。李白與高適的分分合合、起起落落,見證著人生的反復無常、悲歡交集,也成就了兩個曠世才子令人唏噓的人生傳奇。在唐帝國盛世的假面之下,普通人的人生遭際依舊離不開世俗的喧囂和現實的逼迫。無論是李白的“惟有飲者留其名”,還是高適的“天下誰人不識君”,都是于困厄中迸發出的豪情,打發這無聊的羈絆和兇狠的生活波折。這豪情穿云裂帛,扼住命運的咽喉,直面人世間的凄凄慘慘戚戚,以獨立的人格挑戰世情的磨礪。從這個意義上說,《長安三萬里》不是給不諳世事的孩子看的動畫,而是給所有在命運的征途上受過傷的成人看的寓言。“白云千載空悠悠”,獨自看天邊的白云,極目遠眺,自在飛翔于藍天之上、白云之間的是個夢。夢從一生開始,夢從痛苦開始。驀然回首,孤煙一縷,縹緲而上,凄楚哀怨,笑罵嗔怪,惜英雄隕落,憐少俠孤寂,怨紅顏命苦,嘆風塵無奈。
“萬古愁”最喜“風流人物”。李白與高適是無可替代的,是大氣的,是不可用言辭說盡的,是縹緲的幻象,是大唐獨具神韻的人文景致。解讀李白與高適,是在觀賞大唐的風情畫卷,是在觸摸長安金碧輝煌的宮門城墻,是在呼吸大唐歷史的氣息。千載而下,李白與高適的才情,李白與高適的風骨,李白與高適的放誕豪氣,李白與高適的俠骨柔腸,都緊緊牽引著華夏這片土地,華夏這個民族。若無李白與高適,通覽中華文明古國千年的文化景觀,一幕獨具特色的景象將消逝,令人扼腕嘆息;若無李白與高適,可能便找尋不到那已迷失在歷史煙塵中的大唐王朝。風流人物與他們各自的人生詩篇,成為長安派往現代的使者,跨越時空的隔絕,向現世今人傳遞歷史風情的喃喃細語。還歷史以真實,還人生以過程。
“萬古愁”最惡“盛世迷夢”。盡管片中的高適堅信“詩在,文在,長安在”,但其實,我們都知“長安終不在”。這部電影有“詩人”,有“詩歌”,有“詩意”,有“詩情”,但電影的核心價值卻在不斷警示我們,“詩”的背后也正是皇權支配下的帝國不堪面對的“荒唐”與“荒涼”。《長安三萬里》所講述的李白與高適的“逐夢”之旅,在表面上依然是一個“普通人”自強不息的故事。在通往“長安”的道路上,他們對出人頭地的渴望是如此強烈,以至于他們做出種種努力與妥協,以期實現自我的價值。這種對自我價值的追求,也可以視為對帝國實際權力運行機制的不平等與不合理的反抗。屢屢遭遇挫敗,不是被排斥,就是被利用。帝國在這些浸染著無數人的鮮活生命體驗與人生觀照的詩句里,早已顯得那么浮夸與無能,正如“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正如“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那些普通人心中燃動的那團理想的火,也難以不斷承受帝國無情的碾壓。從這個意義上說,“長安可以不在”,但是“詩在,文在,春秋在,春秋終不負”。
《長安三萬里》選擇了一個并不好講的故事,卻講出了故事里最深情的人生喟嘆。初聞唐詩似高歌,今觀長安淚難遮。三萬里壯志難酬,抬望眼已是流年。
(作者單位:南昌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