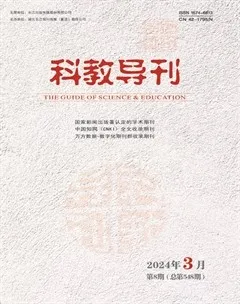同伴介入法應用于我國自閉癥兒童干預的研究述評
王松華
(江西科技師范大學有機功能分子研究所 江西 南昌 330013;江西科技師范大學教育學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簡稱CDC)最新報告顯示,自閉癥譜系障礙兒童(即ASD,以下簡稱自閉癥兒童)患病率已達1/36。自閉癥是一種神經性發育障礙類疾病,患者具有興趣狹隘、行為刻板、社交缺陷等特征,在社交、生活、學習及未來生涯發展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困難,及早發現、及時干預治療對于自閉癥兒童的生活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同伴介入法是以行為主義心理學理論為基礎,選擇社交能力較強的普通兒童作為自閉癥兒童的干預伙伴,經由研究者訓練后使他們能與自閉癥兒童建立恰當的社交模式、強化自閉癥兒童適切的社交行為,從而改善自閉癥兒童溝通缺陷、提高其社交能力的一種干預方法。同伴介入法可以提供交往互動的機會,一方面,使自閉癥兒童可以與普通兒童進行互動并向其學習社交技能;另一方面也使得參與干預的普通兒童在與自閉癥兒童積極互動的同時,不斷提高自身的同理心和發展水平。此外,已有研究探討了在融合情境下使用同伴介入法對自閉癥兒童社交進行干預的有效性,發現同伴介入法在融合情境中使用會有較好的維持效度與泛化效果[1]。基于此,本研究將從干預參與人員、干預目標行為、研究設計、干預結果方面出發,梳理分析我國應用同伴介入法對自閉癥兒童進行干預研究的現狀,以期為同伴介入法在我國自閉癥兒童干預中的應用及相關研究的開展提供參考。
1 研究方法
本文以中國知網(CNKI)為文獻檢索來源,檢索時采用“同伴介入法”“同伴介入”“PIM”聯合“自閉癥”“孤獨癥”“自閉癥譜系障礙”“孤獨癥譜系障礙”“ASD”主題詞為檢索項進行高級檢索。初步檢索共得到146 篇文獻,通過剔除綜述類、會議、重復不相關文獻并通過摘要閱讀、瀏覽全文的方式進行篩選,最終獲得15 篇文獻納入分析。
2 研究結果
2.1 參與人員
從被試特征上來看,所納入的15 篇文獻中共有157 名被試都診斷為自閉癥,其中明確報告性別男生和女生的數量分別為115 名、41 名,男生居多,年齡范圍在4―23 歲,但多以自閉癥兒童為主。其中8 項研究選擇以1 名自閉癥兒童為被試,4 項研究選擇3―9 名自閉癥兒童為干預對象,3 項研究選擇36―50 名自閉癥兒童為被試進行干預實驗,總體上以1 名自閉癥兒童為目標的居多。
從參與干預同伴特征來看,納入分析的研究中明確告知參與同伴數量,其目標兒童與同伴數量配比范圍為1∶1―1∶5,一般多選擇1 名目標兒童配3 名普通同伴。且研究選擇的同伴數量會受同伴介入具體方式的影響,納入分析研究中主要采用提示強化同伴介入策略,其次為主動發起+提示強化這一混合型介入策略。此外也有研究者采用同伴介入結合其他干預方法的方式,如彭若婕結合了關鍵反應訓練對自閉癥兒童的社交溝通能力進行干預[2]。
2.2 干預目標
納入分析的文獻中干預目標行為主要有社交溝通能力、適應能力、不良情緒、日常生活能力。其中目標行為為社交技能的研究共有13 項,占87%。可見社會交往是研究者重點關注的方向,其對于改善自閉癥兒童的表達交流,提高其溝通交往能力具有重要影響。此外,郭麗莎、謝雙勵對自閉癥兒童的適應能力進行干預,以提高其在校生活適應能力[3-4]。
2.3 干預研究設計
上述研究中采用了單一被試多基線實驗設計、隨機對照實驗、行動研究等實驗設計,其中6 項研究采用單一被試多基線實驗設計,5 項研究采用行動研究法,3 項研究采用隨機對照實驗,從干預設計來看,單一被試實驗設計中被試人數為3 人以下,而隨機對照實驗中被試人數多達36人以上,即干預對象人數少時多采用單一被試實驗設計。在單一被試多基線設計中,基線期對被試不做任何干預,研究者觀察記錄被試目標行為出現次數,并在其表現穩定后進入干預期進行同伴介入策略干預,研究者采取與基線期同樣的觀察記錄形式,探索同伴介入法對被試目標行為的影響。干預結束后進入維持期,撤除干預,考查干預效果的維持或泛化情況。而A―B―A―B 實驗設計,研究者在第一次干預及干預效果趨于穩定后,等被試第二個基線期也表現出穩定情形便召回同伴進行二次干預,通過兩次同伴介入干預的前后數據變化來反映干預效果。
2.4 干預結果
15 篇文獻均顯示取得了積極的干預效果,有效改善或提高了目標行為,表明同伴介入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改善自閉癥兒童的社交技能、不良情緒,提高其在校生活的適應能力,具體表現為目標兒童主動發起、回應行為次數增加,不良情緒發生次數減少,交往形式更為豐富。但在目標行為的維持與泛化效果方面,上述研究結果不盡相同。有3 項研究表明有良好的維持效果,1 項研究報告了行為泛化,其中也有研究指出目標行為的維持效果不顯著,自發性互動低,有部分目標行為未得到明顯改善。
3 討論
3.1 研究進展
總體來看,近年我國越來越多研究者采用同伴介入法干預自閉癥兒童,且干預結果顯示同伴介入法有利于改善自閉癥兒童的社交、適應能力、生活能力、不良情緒。相較于2020 年以前,2020 年后至今有一些新進展。首先,文獻數量上大幅增加,我國有越來越多研究者進行同伴介入法的干預,且集中在對自閉癥兒童社交能力的干預,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閉癥兒童社交缺陷的局面。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單一被試實驗設計的研究數量增加,且在干預期對實驗的控制及活動設計更加合理,研究信度增加。再次,同伴介入策略不局限于提升強化、接近和主動發起,而是與其他有效的干預方法相結合,如關鍵反應訓練、游戲活動、教學活動等,為有效干預自閉癥兒童的方式提供多種實踐和參考。此外,干預場所也更加關注自閉癥兒童的生活、學習,在自然情景中實施,關注引發兒童興趣參與研究,從而產生更多的主動性行為,如走廊或食堂排隊時、用餐、體育活動等。最后,研究者運用同伴介入法對自閉癥兒童的干預主要集中于社交方面,并取得積極結果,不僅得到維持,且出現了泛化行為。在此過程中,研究者與教師共同配合,運用言語、眼神提示、延時等策略幫助同伴及目標兒童,使研究進行下去。
3.2 展望
3.2.1 增加同伴介入法本土化實證研究
目前我國已有研究者運用單一被試多基線實驗設計進行同伴介入法干預自閉癥兒童的研究,但數量上相對較少,且在干預目標上多集中于社交行為及能力的增加和提高,而對于自閉癥兒童其他方面的干預亟待加強。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需密切關注社會及自閉癥兒童的發展需求,把握有待解決的問題,結合當下科技及方法進展,擴展今后的研究方向并探索更多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今后研究可增加被試數量并豐富其多樣性,也可多考慮進行隨機對照實驗及其他研究設計,并在實踐中考慮嚴謹性,控制無關變量對實驗的干擾,提升研究的信效度。
3.2.2 建立被試與同伴之間的良好關系,增加社交可能性
同伴介入法以同伴關系為主要切入點[5],因此,使自閉癥兒童與合作同伴之間建立良好的關系和積極的情感聯系,對于增加彼此的社交意愿、促進共同成長具有重要意義。積極的同伴關系不僅可以拉近自閉癥兒童與同伴的距離,而且幫助同伴及普通兒童更好地理解自閉癥兒童的情緒、行為、興趣等,發現其身上的優點,從而產生共情,愿意主動伸出幫助之手。在此過程中,教師具有重要影響地位。教師可以組織與自閉癥相關的活動、班會,從認識自閉癥兒童著手,了解其與普通兒童的不同之處,講明原因為何,引導兒童認識到可以通過大家的努力而使自閉癥兒童有所改善,產生主動幫助的意愿[6]。
3.2.3 豐富介入同伴的多樣性
納入分析的15 項研究中,有11 項研究都是在幼兒園、小學、特殊學校中進行[7],同伴選擇主要為同班同學。在這些場所進行同伴介入法無疑需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時間精力,給學校、教師、家長帶來不便和壓力,妨礙教學任務的進程。研究還可以選擇在不同環境場所,與不同同伴進行。如將干預場所延伸至家庭、日常生活活動,將兄弟姐妹納入同伴選擇。有研究表明將兄弟姐妹作為執行干預同伴可以有效提高自閉癥兒童的社交能力,因此,將兄弟姐妹作為普通同伴介入自閉癥兒童的干預研究,有利于擺脫地點場所的限制,緩解人力、資源的壓力,有利于增加自閉癥兒童與其他人溝通互動的可能性,也使得干預研究更加靈活。
3.2.4 探索同伴介入法與其他方法相結合的方式
上述研究表明同伴介入法能有效改善或提高自閉癥兒童的社交、適應能力等。然而研究者還應加大探索力度,面對自閉癥兒童各方面改善及發展的需求,積極探索與其他有效方法相結合,協同幫助解決自閉癥兒童的問題及行為。如與關鍵反應訓練、社會故事、游戲活動、圖片交換溝通系統、應用行為分析等方法的有效結合,進而提高干預的有效性,推動干預目標的達成。同時,研究者在積極探索干預方法的結合方式時,也需考慮方法的適用性與目標的作用性,以及在進行實踐過程中對無關因素影響等的考量,從而發揮綜合干預方法的有效性。
3.2.5 研究不足
一是研究數量不足。經檢索發現,當前我國運用同伴介入法干預自閉癥兒童的干預研究不足20 篇,此研究數量有待增加。同時,在目標行為上多集中于社交方面,負面情緒、學校生活適應這兩方面各僅2 篇研究進行干預,不僅其有效性還需進一步驗證,而且其研究結果也缺乏可比性。二是被試數量相對較少。上述研究中以一名被試進行的研究占半數以上,其實驗有效性仍待考量及驗證。且在單一被試實驗設計中,嚴謹性也有待提高,主要體現在對無關變量的控制存在一定的隨機性,包括場所、同伴、資料數據的收集等。三是同伴選擇上較為單一。上述研究多以同學為主,選擇標準多從基本同齡、學習成績、好交際、樂于助人、自愿、監護人同意這幾方面出發,未考慮更多的納入范圍。四是對目標行為的維持及泛化效果探究不夠。在上述15 篇文獻中僅有5 項研究說明了維持或泛化情況,1 項研究說明干預目標存在時間上的延時效應,因此,對于同伴介入法應用于自閉癥兒童在時間上的作用未深入探究也無從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