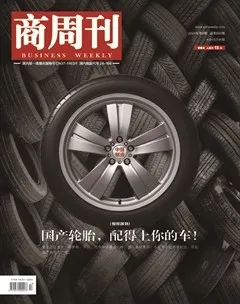桑葉成肴
崔啟昌
清明時節,放眼野外,葉綠花繁,芳姿搖曳。這個時候若在江南,有道口福繞不過:“神仙草”成就的美味菜肴。
“神仙草”本名為桑葉。桑葉是蠶寶寶們唯一的“主食”。北方人“咬春”的食單上少有桑葉菜肴的身影,不是不稀罕這口,早些年只是對其知之不多而白白負了桑葉的一腔赤情。
春里,江南人尤愛“桑肴”,他們自恃家鄉春來早的優勢,熟念著嘗百草的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說給桑葉“人參熱補,桑葉清補”的好話,打著“食藥同源”的旗幟,一春復一春,對著采得的鮮嫩可人的桑葉,難抵美味誘惑,急切切道著“吃了它”的心聲。
“柳花深巷午雞鳴,桑葉尖新綠未成。坐睡覺來無一事,滿窗晴日看蠶生。”宋代范成大《春日田園雜興》中的詩句,如今說來,多少讓江南人覺得詩人對不住時光:面對恰好時節,桑樹已經用鮮亮的嫩芽發出“食其時鮮”的邀請,他竟還慵懶地在坐椅上瞌睡,抑或睡眼朦朧地看蠶寶寶俯在桑葉上“刷刷”地吞嚼那些“嫩綠”,實是荒廢了光陰,耽誤了嘗鮮“桑肴”。
有年去無錫,是剛過清明不多日的一個清朗天,眼簾里田間清綠,山野朗潤。中午,接待我們的一干攝影家告知,午餐有兩道“桑肴”要嘗。桑肴?何物?這令久居江北海邊的我們面面相覷起來。等菜齊備上桌,兩道湛綠湛綠的菜品格外吸引我們。介紹得知,其中一道是涼拌桑葉;一道是桑葉上湯。推杯換盞時,我們貪婪的吃相連自個兒也覺得怪不好意思,而無錫同行絲毫情面也沒給范成大,說詩人不惜大自然之饋贈,慵懶中竟讓新生的桑樹嫩葉漸漸老了去。聽后,我真正體會到了他們對“桑肴”的喜歡程度是超級的高。
還有一年,是臨近清明,我和同伴去江西上饒看花,逗留三四天,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臨街的食肆里,在寬敞的排檔里,在規模頗大裝潢考究的酒店里餐餐都有“桑肴”可點。涼拌、熱炒、做湯、當餡,嫩桑葉的使處甚廣,成肴后的桑葉菜品男男女女各路食客普遍喜食。我和同伴依海而居,菜肴偏向海貨,幾天時間里,必點的“海米桑葉湯”久吃不厭。席間,打聽服務生,詢其桑葉成肴當地人喜愛的原由,她們說,桑葉食藥同源,連古人都著書立說。再是江南氣溫升得快,稍縱,嫩桑葉的美滋味就溜走了。若等,便是霜降后的桑葉茶了。
桑樹,北方亦多有栽植,其用途多為養蠶或采收桑葚果子。桑葉成肴就飯,確實不常見。不過,隨著社會發展,南北往來頻繁,北方人烹制桑葉吃不再稀奇。三峽移民那會兒,老家遷來幾十戶重慶人,他們很勤奮,轉年,三四家重慶餐館開張,桑葉肉絲、桑葉粉絲湯、桑葉餡水餃等等,讓住海邊的、吃海鮮的青島當地人大開了胃口。若干青島土著也是傍著食藥同源的理論,對重慶人自故鄉快運來的一兜兜新鮮嫩桑葉從知之不多,漸變為情有獨鐘了。
三年前,我住的小區邊上開張了一家湘菜館,一干人馬全著民族服裝,服務也熱情,我常帶家人光顧,每每落座,服務生便熱情地上前用帶有長沙口音的“普通話”介紹菜品。其實不光我,由于湘菜館的嫩桑葉自長沙快遞而來,且與江北有著較長的生長時間差,咱當地人吃著新鮮不說還養生,遠近的若干食者都當起了回頭客,湘菜館的生意可謂興隆。
季節恰好時,青島人的餐桌上若有“桑肴”,多是跟海貨匹配混搭。涼拌時加蛤蜊肉或者竹蟶肉,做湯時擱蝦米、干魚絲,包餃子、包子時放鮮貝柱,每道菜品風味各異。結合風俗習慣,配以本幫食材,烹制幾道當地食客喜歡的菜品,這是切合實際的實踐與創新,別的領域是這樣,飲食行業當然也不例外。
眼下已臨桑葉當采季,再淋幾番春雨,桑樹便會迅速披上青綠,嫩嫩的桑芽兒冒出了頭,就該動身郊外攏幾籃桑葉回家了。至于煮湯、熱炒、涼拌、當餡,還是煎蛋、蒸魚、酥炸,就看自個兒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