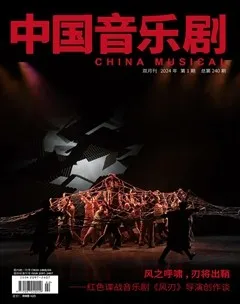桂林抗戰(zhàn)音樂家林路的音樂活動研究
朱韻



摘要:桂林文化城以文藝抗戰(zhàn)而著名,轟轟烈烈的歌詠運動早已成為抗戰(zhàn)文藝的代表性符號之一。林路便是為桂林歌詠運動做出重要貢獻的一員。1938年12月—1943年4月,林路駐留桂林四年多。在此期間,他積極參演各大歌詠運動、組織參與戰(zhàn)友紀念會以及擔任歌詠團體負責人,為桂林的抗戰(zhàn)歌詠事業(yè)、新音樂運動的發(fā)展做出了努力。在烽火歲月里,他逐步成為桂林新音樂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桂林抗戰(zhàn)歌詠運動領(lǐng)導人之一。
關(guān)鍵詞:林路;桂林歌詠運動;抗戰(zhàn)音樂
一、參演歌詠運動
1938—1944年是桂林開展歌詠運動最頻繁、最廣泛的時間。林路恰逢于1938年12月抵達桂林,1943年4月離桂。林路既是中共黨員,又是一名青年男高音音樂家,他積極地投身桂林救亡歌詠運動當中。因此,無論是桂林歌詠的客觀條件,還是林路的自身因素,都促使了林路在駐留桂林的四年多時間里積極活躍于各大歌詠運動當中,具體活動參見表1。
從林路參與的歌詠活動可見,1939年初到桂林,林路就開始積極參與各項歌詠活動,其歌詠活動的參與一直持續(xù)至1942年,在這幾年間,其參與的大大小小歌詠活動共計15場,參與的形式不一。其中,1940年參與的歌詠活動是影響力最廣泛、參與人數(shù)眾多的活動,如桂林音樂界紀念抗戰(zhàn)建國三周年音樂大會、新安旅行團公演的大型舞劇《虎爺》、抗宣一隊聯(lián)誼會的新歌劇《軍民進行曲》等,前兩者在演出后都應(yīng)觀眾續(xù)演。以上三場活動所上演的作品都有力地突破了中國以往合唱、舞劇、新歌劇的形式,引起了巨大轟動和劇烈反響。不僅鼓舞了群眾,將抗日救亡歌詠運動推向了高潮,而且通過作品有力地傳播了新音樂創(chuàng)作思想的宗旨——民族化、大眾化,對于新音樂運動的發(fā)展有著推動作用,對我國合唱作品、歌舞劇的建立和創(chuàng)作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而林路在上述活動中,并不局限于演唱的參與形式,甚至擔任起歌詠活動的指揮、協(xié)助伴奏、指導排練等角色,為活動投入了大量精力。尤其在桂林音樂界紀念抗戰(zhàn)建國三周年音樂大會,林路擔任壓軸作品《黃河大合唱》的指揮兼演唱,以飽滿熱血的精神指揮二百余人的合唱團,該場演出獲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功,引起了國民黨中央系反動勢力的恐慌[1],也因此掀起了桂林之后歌詠大合唱的高潮。
此外,從表1可見,1941年是林路在桂林參加歌詠活動數(shù)量最多的一年,共參與了八場活動。這也歸因于1941年是皖南事變導致桂林文藝運動進入低潮的一年。迫于低潮現(xiàn)象,桂林音樂界積極以各類名目籌備舉辦歌詠活動,以此達到推動桂林救亡音樂運動再次發(fā)展的目的。由此,林路作為桂林音樂協(xié)會的一員,也做出了巨大貢獻,如參與了桂林歷史上重要的音樂活動,“為響應(yīng)‘政工號獻機及籌建音樂工作室音樂演奏會”“千人大合唱”“露天歌舞大會”等,在音樂會上,林路激情演唱抗戰(zhàn)歌曲,并且作為“露天歌舞大會”的籌備委員,積極地與歐陽予倩、劉式昕、楊紀等人共同統(tǒng)籌此次音樂會。
值得一提的是,“千人大合唱”歌詠活動是在林路、廖行健、白寧等人的秘密組織下進行排練,在正式演唱那天極為轟動,各學校、各合唱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涌聚體育場,使得國民黨頑固派措手不及。在會上,各團體演唱了眾多愛國抗戰(zhàn)歌曲,最后全場七千余人齊唱《義勇軍進行曲》,歌聲在桂林文化城中久久回蕩。此次活動的成功舉辦很好地體現(xiàn)了林路和共同參與此次活動的其他進步人士
的革命素養(yǎng)與隨機應(yīng)變的組織能力。同時,體現(xiàn)了現(xiàn)場群體的凝聚力,彰顯了群眾抗戰(zhàn)的勇氣和決心。總的來說,在林路和其他進步音樂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這些活動再度唱響革命嘹亮激昂的歌聲,改變了自皖南事變導致桂林文藝運動進入低潮的形勢,喚起了人民群眾的抗戰(zhàn)斗志,激發(fā)了桂林文藝界的工作熱情,為抗戰(zhàn)革命的勝利打下了堅實基礎(chǔ)。
林路在桂林救亡歌詠運動中所做的貢獻不可低估。他成功地指揮著名《黃河大合唱》,排練指導新歌劇《軍民進行曲》,籌備組織千人大合唱,將歌詠活動的影響力發(fā)揮到最大化,使之在桂林轟動一時。這不僅有力地將桂林歌詠運動推向新的高水平發(fā)展階段,而且成功推動了桂林新音樂的發(fā)展,就如他為《七七之歌》特刊撰文《用工作來回答與感謝》所指出的:“這三年來新音樂運動的進步,決不是僅僅在工作上得到普遍的開展而已;技術(shù)方面,也早把‘叫換成‘唱,把單音的‘齊唱換成復音的‘合唱了;而且,還怎樣在作曲的方法上、樂器的應(yīng)用上繼續(xù)努力,以期能達到建立真正民族音樂的地步。”誠然,以上歌詠活動的影響力并不是林路一人之力所為,共同參與的音樂工作者都是歌詠活動成功舉行并影響廣泛的作用因素。不可否認的是,林路作為云集桂林的諸多文藝將士之一,他在桂林歌詠活動中的點滴貢獻極為可貴。
二、組織和參與音樂悼念會
在武漢時期,林路就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文藝宣傳部,經(jīng)常與張曙共事,兩人便結(jié)下了深厚友誼。武漢淪陷之后,張曙、林路等人隨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抵桂。一周后,張曙不幸在桂林遇到日本轟炸而逝世。由于當時的情況較為特殊,張曙逝世只是由三廳《救亡日報》演劇隊的同志一起趕到了文昌門,在林路、周鋼鳴、高灝等許多同志的協(xié)助下,把張曙和他女兒的遺體殮入棺中,默默地向張曙同志的遺體告別,并未舉行追悼會。直至1939年2月27日張曙殉難后的第二年春天才補開追悼會。
如表2所示,林路在桂林時期共參加了張曙三次悼念會。其中,第一次張曙的追悼會便是由林路組織牽頭,于3月12日在新華戲院正式舉行,會上,林路等人相繼發(fā)言。緊接著,廣西音樂會全體會員演唱了由凌鶴與任光專門為追悼會創(chuàng)作的《挽歌》以及張曙到桂后遇難前新創(chuàng)作的歌曲《我們要報仇》《負傷戰(zhàn)士歌》和其他遺作《胡阿毛》《日落西山》《盧溝月》,等等。之后,1939年12月24日,由抗宣一隊、新安旅行團等發(fā)起,聯(lián)合全市音樂團體和群眾組織,在樂群社大禮堂舉行張曙殉難周年紀念大會,林路在會上演唱張曙的歌曲遺作。26日,桂林音樂界舉行張曙殉難周年紀念會總結(jié)及第一次座談會,林路、章枚等各團體代表十余人到會。此外,1942年12月24日,張曙殉難四周年。正值田漢在桂,于11月23日又邀同林路、李凌、李也非、安娥等人去掃墓,在張曙墓前的草地上舉行野祭儀式。田漢主祭并簡單報告了張曙的生平。林路對張曙的遇難做了補充,并報告了張曙的學生時代。會上最后由五隊劉式琨指揮,合唱了張曙遺作《壯丁上前線》《日落西山》等歌曲[2] 。
周恩來總理曾這樣評價張曙:“張曙先生之可貴在于和聶耳同為文化戰(zhàn)線上的兩員猛將,給全民抗戰(zhàn)起了偉大的推動作用。救亡歌詠便是最顯明的,這功績是永遠永遠不磨滅的。”[3]從周恩來的評價中可以認為,張曙是救亡歌詠運動的凝聚力象征之一。桂林音樂界舉辦張曙追悼會、紀念會有利于以張曙精神激發(fā)民眾對敵人的仇恨,促進桂林抗戰(zhàn)歌詠運動的大力開展,號召保衛(wèi)大西南。同時,張曙的創(chuàng)作精神與理念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給予研究抗戰(zhàn)音樂工作者們一些創(chuàng)作性啟發(fā)。而林路作為眾多參會工作者之一,積極組織和參與戰(zhàn)友張曙的追悼會和紀念會,并為張曙逝世發(fā)文作歌,例如發(fā)布《征求張曙先生遺作啟示》,撰文《從武漢到桂林》《聶耳死了嗎》,作歌《戰(zhàn)士的埋葬》。由此可見,無論是作為組織者,還是作為參與者,林路都為張曙紀念會做了大量工作,真切地體現(xiàn)了他與張曙深厚的戰(zhàn)友之情。并且,張曙作為抗戰(zhàn)音樂宣傳中的重要一員,林路通過對張曙的紀念也彰顯了他接任張曙工作的決心以及對張曙抗戰(zhàn)精神的繼承。
林路除了組織張曙的追悼會,在桂期間還參加了其他音樂家的逝世紀念音樂會。如紀念黃自逝世兩周年遺作演奏會、聶耳逝世五周年紀念大會、聶耳逝世七周年紀念會的工作會議。以上活動事跡深刻彰顯了林路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溫度的音樂革命家。
三、組織訓練歌詠團體
抗日救亡時期,桂林的歌詠運動空前繁盛,大量歌詠團體、演劇隊組建產(chǎn)生。據(jù)統(tǒng)計,群眾性歌詠團體達三四十個,另有幾十個專業(yè)、業(yè)余話劇團體的歌詠隊。其中主要活躍的團體有廣西音樂會歌詠團、廣西藝術(shù)師資訓練班學生歌詠團、廣西藝術(shù)館歌詠團、抗宣一隊、演劇九隊、廣西地方建設(shè)干校、青年學生歌詠隊等。這些群體在桂林抗日救亡期間積極地帶動群眾開展各種歌詠活動,在桂林文藝史上占有功不可沒的地位。
林路作為桂林歌詠運動的組織者和骨干力量,對歌詠運動的貢獻不止是參演,而且成功地指揮領(lǐng)導了廣西地方建設(shè)干部學校歌詠隊、樂群社歌詠團等歌詠團體(詳見表3)開展各類歌詠活動。歌詠運動作為戰(zhàn)時宣傳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歌詠活動能聲勢浩大地展開必定離不開各歌詠團體。根據(jù)表3所示的參演活動可見,林路領(lǐng)導的歌詠團體參演了桂林界具有重要意義的歌詠活動,并且會后都產(chǎn)生了不同影響。因此,可以認為,林路領(lǐng)導歌詠團體的這一貢獻進一步推動了桂林歌詠運動的發(fā)展,壯大了桂林歌詠的隊伍。
更為突出的是,在歌詠工作當中,林路還在理論上提出關(guān)于歌詠運動的發(fā)展現(xiàn)狀及見解,本文中闡述的觀點給予桂林文藝界一定的參考意義。例如,在《音樂陣線》創(chuàng)刊號中發(fā)出的創(chuàng)刊詞《為保衛(wèi)西南而歌》中,提出歌詠工作的四個“不夠”:第一,歌曲的產(chǎn)量不夠;第二,歌詠的活動不夠;第三,歌詠組織得不夠;第四,同志聯(lián)系得不夠。對于以上四點不足,林路做出相應(yīng)對策:一是動員所有作曲家、詩人創(chuàng)造時代的歌曲,并盡量采取民歌創(chuàng)作;二是經(jīng)常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歌詠行動,建立歌詠運動的根據(jù)地;三是盡量發(fā)動歌詠組織,并使原有的歌詠組織健全;四是建立經(jīng)常的聯(lián)系,建立一個總的領(lǐng)導機構(gòu)[4]。因此,在這樣的理念下,林路不僅經(jīng)常積極組織各歌詠團體活動,而且對歌詠團體進行規(guī)范化的訓練,如廣西藝術(shù)館的音樂合唱班,訓練期為六個月,學習內(nèi)容有合唱、練聲、樂理及音樂講話等。這為桂林歌詠培養(yǎng)了一支專業(yè)隊伍,不僅使得各歌詠團演唱水平得到了一定提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桂林抗戰(zhàn)歌詠的層次。
誠然,林路領(lǐng)導的歌詠團體不多,但是以上團體在抗日救亡期間發(fā)揮的作用以及林路的領(lǐng)導能力是值得肯定的。一方面,它們積極組織和參加桂林各種旨在宣傳抗戰(zhàn)的音樂活動,以氣勢澎拜、激昂壯闊的戰(zhàn)歌成功動員全民抗戰(zhàn),激發(fā)抗日救國斗志。其聲勢浩蕩的歌詠活動構(gòu)成了桂林文化城奇特文化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另一方面,林路以專業(yè)的音樂素養(yǎng)領(lǐng)導培訓歌詠團體,使得歌詠團體有組織、有能力地開展和參與各類音樂歌詠會,這對桂林歌詠運動的發(fā)展具有一定的建設(shè)性意義。此外,從林路的歌詠領(lǐng)導工作中也足以說明,他在桂林歌詠運動中具有代表性的地位和突出的工作能力。
四、結(jié)語
在桂林駐留的四年多時間里,林路的滿腔熱血都揮灑在桂林這片歌海當中,他積極傳播進步的新音樂作品,高唱愛國主義新音樂歌曲。就如他主編的《音樂陣線》所言:“抗戰(zhàn)開展了新音樂運動,新音樂運動推動了抗戰(zhàn)。”新音樂與抗戰(zhàn)二者相輔相成,他以自己嘹亮的歌聲唱出了新音樂作品蘊含的不屈不撓的抗戰(zhàn)精神。盡管桂林文化城人才薈萃,但不可否認的是,林路在桂林開展、參與的歌詠工作使得他成為桂林抗戰(zhàn)音樂的代表人物之一、駐桂的重要新音樂人之一。
【項目:研究生創(chuàng)新項目《桂林抗戰(zhàn)音樂家林路的音樂活動研究》XJYC2023005結(jié)題成果】
(作者單位:廣西藝術(shù)學院)
參考文獻:
[1]陸鏗榮,左超英.抗戰(zhàn)音樂史上珍貴的一頁——《黃河大合唱》在國統(tǒng)區(qū)桂林的傳播[J].音樂研究,2001(02).
[2]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紀念館編著.《豐碑——桂林抗戰(zhàn)紀實文物史料圖集》.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8.
[3]中國音樂家協(xié)會著. 張曙紀念文集[M]. 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 2015:8.
[4]郭沫若.《救亡日報》1939年12月24日音樂陳線旬刊創(chuàng)刊號.
[5]郭沫若.《救亡日報》桂林版.1939.1.10.
[6]賀衷寒.《掃蕩報》桂林版.1938.12.15.
[7]王小昆. 桂林抗戰(zhàn)音樂文化研究[M]. 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 2005:7.
[8]李莉. 廣西音樂文化歷史研究[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