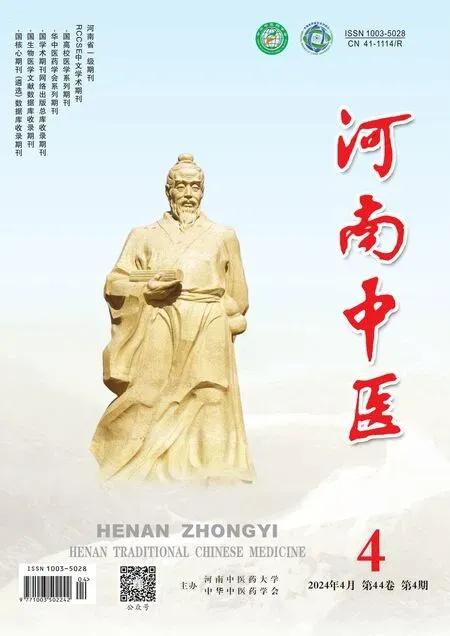理中湯加減治療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臨床研究*
王月明,李澤鵬,周曉玲,沈新輝
1.柳州市中醫醫院,柳州市壯醫醫院,廣西 柳州 545001; 2.廣西中醫藥大學,廣西 南寧 530200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是指排除酒精及相關因素導致的以肝脂肪變性、脂肪沉積為主要病理變化的代謝應激性肝損傷,與胰島素抵抗與遺傳易感等因素密切相關。NAFLD可逐漸進展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肝硬化及肝細胞癌等[1]。近年來,NAFLD的發病率隨著肥胖和代謝綜合征的增多而逐年上升,在我國成人中發病率已達20%~33%,在肥胖人群中的發病率可達75%[2]。
本課題組前期分別對代謝綜合征與NAFLD患者進行中醫體質研究,結果顯示,陽虛體質患者分別占80%和71.3%,并且以陽虛兼痰濕質為主[3-4]。基于此結果,本課題組認為NAFLD的發病與機體脾陽不足、脾失健運、痰濕蘊結有關,據此提出了溫中健脾的治法,并且在動物實驗中驗證了溫中健脾法對NAFLD大鼠具有明顯的治療作用[5-6]。本次研究圍繞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核心病機——脾陽不足,以溫中健脾之理中湯為主方,隨證加減,觀察其對患者肝功能指標、血脂、血糖等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柳州市中醫醫院門診及住院部收治NAFLD患者110例,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每組各55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具體資料見表1。本研究已通過柳州市中醫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倫理審批號:2020JUN-KY-YN-037-01)。

表1 兩組NAFLD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1.2 病例納入標準(1)符合《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防治指南(2018 更新版)》[7]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診斷標準;(2)臨床辨證為NAFLD脾陽不足證,主癥為形體肥胖,右脅下隱痛,周身困重,次癥為乏力,脘痞,食少,畏寒肢冷,口淡不渴,大便溏瀉,舌淡苔白潤,脈沉細或沉遲無力;(3)年齡18~65 周歲,性別不限;(4)臨床肝功能檢查提示血清轉氨酶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amine aminotransferase,ALT)、門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谷氨酰胺轉肽酶(glutamine transpeptidase,GGT)升高;(5)4周內無其他方案治療史,告知研究事項后,患者或其家屬簽署知情同意書。
1.3 病例排除標準(1)合并其他嚴重的消化系統疾病、心腦血管疾病、呼吸系統疾病、泌尿系統疾病、血液系統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神經系統疾病等患者;(2)嚴重肝功能損傷(轉氨酶超過正常值上限10倍,伴或不伴有膽紅素超過正常值上限2倍);(3)患有甲狀腺功能異常、惡性腫瘤等影響血糖血脂疾病者;(4)同時使用降血脂藥、降血糖藥、益生菌等其他治療NAFLD藥物者;(5)妊娠期、哺乳期婦女或正在備孕的育齡婦女;(6)有中藥過敏史或其他原因不宜服用中藥治療者。
1.4 治療方法對照組給予多烯磷脂酰膽堿[賽諾菲(北京)制藥有限公司,批號:國藥準字H20059010]治療,每次2粒,每日3次,連續治療12周,在治療的同時進行健康飲食及合理運動的指導和培訓。觀察組在對照組治療的基礎上加用理中湯,方藥組成:人參15 g,干姜15 g,炙甘草15 g,白術15 g。合并肝郁氣滯者加柴胡12 g,白芍12 g,枳殼12 g;合并痰濕內蘊者加陳皮 12 g,茯苓15 g,澤瀉15 g;合并濕熱蘊結者加茵陳15 g,虎杖12 g,澤瀉15 g;合并痰瘀互結者加陳皮12 g,山楂15 g,丹參15 g。每日1劑,上藥加入適量水,常規煎煮過濾后,分早晚2次溫服,連續治療12周。
1.5 觀察指標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8]對兩組患者治療前后中醫證候進行評分,主癥形體肥胖、周身困重、右脅肋不適或脹滿等按無(0分)、輕度(2分)、中度(4分)、重度(6分)計分;次癥乏力、脘痞、食少、畏寒肢冷、口淡不渴、大便溏瀉等按無(0分)、輕度(1分)、中度(2分)、重度(3分)計分,分數越高,證候越嚴重。
檢測兩組患者治療前后ALT、 AST、 GGT、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CHOL)、三酰甘油(triglyceride,TG)、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LDL-C)水平。檢測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glucose,FBG)、空腹胰島素(fasting insulin,FINS)、糖化血紅蛋白A1c(Hemoglobin A1c,HbA1c)水平,并根據公式HOMA-IR=FPG(mmol·L-1)×FINS(μU·mL-1)/22.5,計算胰島素抵抗指數情況;采用肝臟瞬時彈性成像測量肝臟硬度值(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LSM)和受控衰減參數值(controlled attenuation parameter,CAP)。
1.6 療效判定標準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8]制定。顯效:中醫證候積分減少率>70%,轉氨酶恢復正常,血脂、血糖及胰島素抵抗指數下降超過30%,肝臟瞬時彈性成像明顯改善;有效:中醫證候積分減少率為40%~<70%,但轉氨酶、血脂、血糖及胰島素抵抗指數下降超過20%,肝臟瞬時彈性成像一定程度改善;無效:中醫證候積分減少率<40%,各項檢驗及檢查未見明顯改善。
中醫證候積分減少率=(治療前積分-治療后積分)/治療前積分×100%
有效率=(顯效+有效)/×100%

2 結果
2.1 兩組NAFLD患者臨床療效比較觀察組有效率為85.45%,高于對照組的54.55%(P<0.05),見表2。

表2 兩組NAFLD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例(%)
2.2 兩組NAFLD患者治療前后肝功能指標比較兩組患者治療后ALT、AST、GGT水平低于本組治療前,治療后觀察組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3。

表3 兩組NAFLD患者治療前后 肝功能指標比較
2.3 兩組NAFLD患者治療前后FBG、FINS、HbA1c、HOMA-IR比較兩組患者治療后FBG、HOMA-IR、FINS、HbA1c低于本組治療前,且治療后觀察組FBG、HOMA-IR低于對照組(P<0.05),治療后觀察組FINS、HbA1c水平與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兩組NAFLD患者治療前后FBG、FINS、HbA1c、HOMA-IR比較
2.4 兩組NAFLD患者治療前后血脂水平比較兩組患者治療后CHOL、TG、LDL-C水平低于本組治療前,治療后觀察組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5。

表5 兩組NAFLD患者治療前后CHOL、TG、 LDL-C比較
2.5 兩組NAFLD患者治療前后LSM、CAP水平比較兩組患者治療后LSM、CAP水平低于本組治療前,且治療后觀察組CAP水平低于對照組(P<0.05),治療后觀察組LSM水平與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6。

表6 兩組NAFLD患者治療前后 LSM、CAP水平比較
2.6 兩組NAFLD患者治療前后中醫證候積分比較兩組患者治療后中醫證候積分低于本組治療前,治療后觀察組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7。

表7 兩組NAFLD患者治療前后 中醫證候積分比較 分)
3 討論
NAFLD隨著病情進展可發展為肝纖維化、肝硬化甚至肝癌[9],且有研究表明,NAFLD的發生與代謝綜合征、心血管疾病及腸道腫瘤等疾病密切相關[10-12]。目前,國內外對于NAFLD的治療仍以改變飲食結構、減輕體質量、降血脂、抗氧化或抗炎等綜合干預為主[13- 14]。近年來,中醫藥在NAFLD的治療中取得了可觀的成績,大量研究結果表明[15-17],中醫藥對于NAFLD或NASH有明顯療效。在NAFLD發生發展過程中有多個病機過程參與,包括脾失健運、肝失疏泄、腎氣不足、痰濕內阻、痰瘀互結等[18]。諸多研究者對于NAFLD的認識不盡相同,且由于地域、人群特征的不同,發病特征也有差異,不同醫家選方用藥各有不同。因此,當前中醫藥治療NAFLD的研究中存在辨證論治難以統一、方藥靶向不清等問題。針對這一問題,本課題組前期運用可視化中醫辨證手段——醫用紅外熱成像技術,對NAFLD患者中醫體質與證型分布特點進行研究,發現中醫體質分布最多的為陽虛兼痰濕質,證候分布較多的為脾陽虛證、濕濁內停證[4]。因此,可推測NAFLD是由于機體脾陽不足、脾失健運導致的痰濕積聚于肝臟而形成。
《中西匯通醫經精義》中有“脾生膏脂”“脂脾所司”的記載。NAFLD雖病位在肝,但其發病與脾胃功能異常密切相關,并以脾陽不足為關鍵[19]。《黃帝內經靈樞集注》述:“中焦之氣,蒸津液,化其精微,溢于外則皮肉膏肥,余于內則膏肓豐滿。”脂肪即膏脂,是人體津液的產物,由脾胃運化水谷生成,并依賴于脾陽的溫煦及脾臟運化功能散精于肝,布散周身,濡養臟腑、四肢。當水谷精微攝入過多,超過脾氣散精的范疇,或其他因素導致脾陽不振,運化失職,水谷精微物質不能散布四周,津液在皮肉或膏脂間聚積為痰濕,則發生肥胖和NAFLD。痰濕停留體內必困于脾,又會加重脾陽不足,因而NAFLD患者可能出現倦怠、食欲不振、腹部脹滿、四肢不溫或大便黏等癥狀[20]。
文獻研究發現,歷代醫家治療NAFLD的方藥多集中在溫中、健脾、祛濕、理氣等幾個方面,并且溫中健脾是最主要的治法[21]。理中湯出自《傷寒論》,為溫中健脾經典方劑,由人參、白術、干姜、炙甘草組成,人參、白術和炙甘草均具有健脾益氣之功,加干姜助溫運蒸化,四藥合用溫補脾陽,推動“中焦之氣”,從而“蒸津液,化其精微”。研究顯示,理中湯在減輕肝臟氧化應激、增強肝臟抗炎抗氧化能力,抑制肝脂肪變性等方面中發揮作用[22-23]。臨床研究結果提示,加味理中湯治療NAFLD,可降低患者轉氨酶、血脂水平,改善NAFLD程度[24]。因此,本次研究以理中湯為NAFLD的主要靶向治療方劑,針對NAFLD的核心病機進行治療,并根據患者臨床表現的不同“標證”加味,符合中醫辨證論治原則與臨床實際。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治療后中醫證候積分明顯低于對照組,可見理中湯可明顯減輕患者臨床癥狀,改善生活質量,療效更顯著。
胰島素抵抗是NAFLD發病機制中的重要一環[25],“二次打擊”學說中提出,胰島素抵抗導致肝細胞合成和轉運三酰甘油功能紊亂,脂質過度聚集于細胞內,為NAFLD發生的“首次打擊”[26];細胞內增加的游離脂肪酸使得線粒體β氧化作用增強,活性氧產生增多,引起氧化應激、炎癥,損傷肝細胞,形成“第二次打擊”[27]。ALT、GGT與AST主要存在于肝細胞胞質與細胞核內,當肝細胞破壞時,ALT、AST、GGT釋放,血清中濃度升高。因此,選擇上述指標作為檢測肝細胞功能與肝臟受損程度的敏感指標。本研究結果顯示,與治療前比較,觀察組患者血清ALT、AST及GGT明顯下降,且低于同期對照組(P<0.05),提示肝細胞損傷減輕。再對胰島素抵抗指數與血清CHOL、TG、LDL-C水平進行分析,發現觀察組患者胰島素抵抗指數及血脂水平均低于治療前(P<0.05),推測理中湯可改善患者胰島素抵抗,促進肝細胞對脂肪的攝取與轉化功能,降低脂質聚集對肝細胞的損傷,而這一作用與中焦虛寒得以糾正,脾陽推動中焦運化,促進脂質代謝作用相契合。運用瞬時彈性成像技術,對患者肝臟脂肪變性程度進行定量評估,結果顯示,觀察組患者肝臟脂肪變性程度較治療前明顯下降,且低于同期對照組(P<0.05),更為直觀地說明了理中湯具有治療NAFLD,發揮了防止肝臟纖維化的作用。
綜上所述,理中湯加減治療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可有效改善患者肝功能指標、血脂水平及胰島素抵抗情況,緩解臨床癥狀,提高生活質量。但本次觀察療程較短,樣本量較少,且溫中健脾法治療NAFLD的作用及機制尚未清楚。因此,在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中,將以多樣本、多中心、多療程的方式進行深入研究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