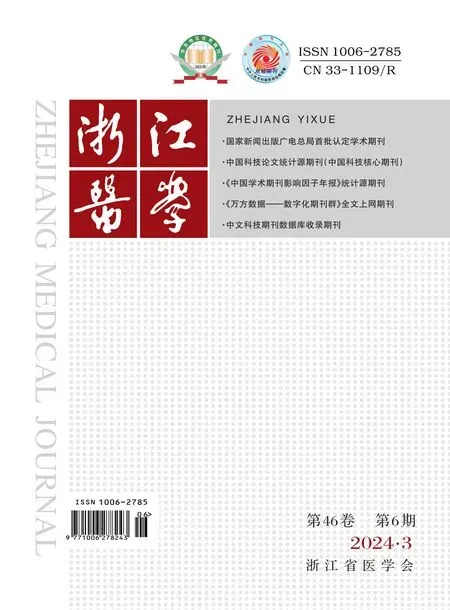血小板活化因子水平對急性腦梗死靜脈溶栓后血管再閉塞的預測效能
何思思 黃向東 陳建媚 茅新蕾
急性腦梗死約占腦血管病的75%,造成嚴重的社會經濟負擔[1]。超早期采用重組組織型纖溶酶原激活劑(recombinant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rt-PA)靜脈溶栓是改善急性腦梗死結局最有效的藥物治療手段[2-3]。靜脈溶栓后部分患者會發生再閉塞而導致預后不良[4]。溶栓后血管再閉塞主要原因可能與再通后遺留的局部栓子、內皮損傷,甚至溶栓藥物本身所誘發的血小板活化聚集有關[5]。血小板活化因子(platelet activating factor,PAF)是血管內皮功能損傷、血小板活化的特異性生物標志物,在動脈粥樣硬化、炎癥性疾病的診斷方面有重要臨床價值[6-7]。本研究旨在揭示血漿PAF 水平對急性腦梗死靜脈溶栓后血管再閉塞的預測效能,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選擇2019 年1 月至2022 年6 月在溫州市中心醫院神經內科住院并實施rt-PA 治療的急性腦梗死患者276 例,其中男174 例,女102 例;年齡52.00~81.00(65.45±7.51)歲;BMI 21.21~30.79(25.40±1.79)kg/m2;吸煙史148 例,飲酒史147 例;合并糖尿病105 例,高血壓164 例,冠心病89 例,高脂血癥144 例;使用抗血小板藥物188 例,他汀類162 例,抗凝藥物42例;入院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評分8~27 分,中位數評分13(12,16)分;后循環腦梗死60 例。將溶栓后血管再閉塞的患者61 例納入觀察組,未發生者215 例納入對照組。納入標準:符合中華醫學會2018 年制定的急性腦梗死診斷和rtPA 靜脈溶栓治療標準[3];靜脈溶栓后血管閉塞改善。排除標準:近1 個月內手術及感染史;嚴重心、肝、肺、腎功能不全、惡性腫瘤及免疫系統疾病等;拒絕參與研究及臨床資料缺失。本研究經本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批準文號:L2024-03-020),患者家屬均簽署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一般資料收集 參照中華醫學會2018 年制定的標準,采用rt-PA(阿替普酶)對兩組患者進行靜脈溶栓和規范化治療。入院時記錄患者性別、年齡、BMI、收縮壓、舒張壓、吸煙史、飲酒史、合并疾病、藥物使用情況和梗死部位等資料,采用NIHSS 評價患者神經功能狀態。溶栓后血管再閉塞定義為溶栓后24 h以內,在溶栓有效時最低NIHSS 評分基礎上惡化2 分及以上,且影像學除外顱內出血[8-9]。
1.2.2 實驗室檢查 靜脈溶栓前抽取患者靜脈血5 mL,離心后分離,采用ELISA 法測定PAF 水平(貨號:XGE990882,上海西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同時檢測血常規、生化、凝血功能等,記錄PLT、TC、TG、HDL-C、LDL-C、血糖、APTT、PT、Fib等指標。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3.0 和R4.2.1 統計軟件。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Mann-WhitneyU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 確切概率法。將上述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納入二元logistic 回歸模型,采用逐步回歸法揭示靜脈溶栓后再閉塞的獨立預測因素。將靜脈溶栓后再閉塞的獨立預測因素組合成預測模型,采用ROC 曲線評估血漿PAF 水平及預測模型的預測效能。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和血清指標比較 觀察組患者BMI、NIHSS 評分、后循環腦梗死比例、血糖和血漿PAF 水平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兩組患者其他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及血清指標比較
2.2 靜脈溶栓后血管再閉塞預測因子的多因素分析將BMI、NIHSS 評分、后循環腦梗死比例、血糖和血漿PAF 水平這5 項指標納入二元logistic 回歸模型,結果顯示,NIHSS 評分、后循環腦梗死和血漿PAF 水平均是靜脈溶栓后血管再閉塞的影響因素(均P<0.05),見表2。

表2 影響靜脈溶栓后血管再閉塞的二元logistic 回歸分析
2.3 logistic 回歸模型建立、驗證和效能評價 基于多因素分析的結果,用NIHSS 評分、后循環腦梗死和血漿PAF 水平構建急性腦梗死患者rt-PA 靜脈溶栓后血管再閉塞的預測模型。血漿PAF 水平預測靜脈溶栓后血管再閉塞的AUC 為0.725(95%CI:0.632~0.778,P<0.001),最佳閾值為221.50 ng/L,靈敏度為0.739,特異度為0.688。預測模型預測急性腦梗死患者靜脈使用rtPA 溶栓后血管再閉塞的AUC 為0.816(95%CI:0.748~0.874,P<0.001),見圖1。

圖1 預測模型預測急性腦梗死患者靜脈使用rt-PA 溶栓后血管再閉塞的ROC 曲線
3 討論
急性腦梗死是神經內科常見病,該病發生后一定時間內顱內梗死病灶缺血半暗帶細胞損傷的可逆性是罹患此病的患者早期溶栓治療的病理生理基礎,該治療方案有利于急性腦梗死患者恢復腦組織血流灌注、減輕腦神經缺損以及改善預后[10]。rt-PA 為第二代溶栓藥物,半衰期短、無抗原性,誘導纖溶酶原進一步成為纖溶酶溶解血塊,對血栓部位具有較強選擇性,可特異性激活血栓中纖溶酶原起到溶解血栓的作用。目前臨床上實施rt-PA 靜脈溶栓是多國指南推薦的急性腦梗死最重要治療方式之一[3]。但是,相關研究表明靜脈溶栓的血管再通率僅為46%,且再通病例中血管再閉塞的發生率高達14%~34%[4]。本研究血管再閉塞的發生率為22.1%。
血管再閉塞主要原因可能是部分再通后遺留的局部栓子、內皮損傷,甚至纖溶酶自身導致的血小板活化,進而引發再閉塞,說明血小板功能活化是急性腦梗死患者靜脈使用rt-PA 溶栓治療后血管再閉塞的重要因素[9]。由于早期使用抗血小板藥物治療可能增加出血性轉化風險,因此出于安全性考慮,目前臨床指南推薦溶栓時間窗為24 h,且排除顱內出血情況后再加用抗血小板藥物治療。然而,大多數溶栓后血管再閉塞發生在責任血管再通后24 h 內,甚至可發生于溶栓治療后的數分鐘內[11],使得部分患者錯過了治療最佳時機,導致不良預后。因此,如何早期識別溶栓治療后血管再閉塞,判斷高危患者再發血管病事件的風險具有重要意義。
PAF 最早是由德國科學家發現,是嗜堿性粒細胞受到攻擊時產生的一類可溶性脂質分子,可行使血小板活化和聚集等生物學功能,檢測血漿PAF 水平可間接反映血小板的功能狀況。隨著研究深入,PAF 已被視作腦卒中病理生理過程中從血栓形成到缺血損害的關鍵點,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12]。既往研究發現,PAF在下肢動脈粥樣硬化、膿毒性休克中發揮重要作用[7,13]。黃麗等[14]發現血漿PAF 水平在短暫性腦缺血發作進展為腦梗死的患者中顯著高于對照組,并且對腦梗死的發生具有一定的預測效能。然而,PAF在急性腦梗死患者溶栓后血管再閉塞中的作用并不明確,缺乏相關報道。本研究發現,觀察組患者血漿PAF 水平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基于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的結果,入院時NIHSS 評分、后循環腦梗死和血漿PAF 水平與靜脈溶栓后血管再閉塞呈獨立相關關系。本研究繪制PAF預測溶栓后血管再閉塞的ROC曲線,血漿PAF水平預測靜脈溶栓后血管再閉塞的AUC 為0.725,最佳閾值是221.50 ng/L,靈敏度為0.739,特異度為0.688。
Yoshida 等[15]認為,PAF 可參與炎癥反應與血管內皮損傷,促進血栓形成。因此,血小板功能狀態的差異可能與溶栓后血管再閉塞有關,而PAF 與血管再閉塞的發生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其機制可能與PAF 通過介導內皮損傷后的血小板活化聚集有關[16]。
本研究還發現急性腦梗死患者入院時NIHSS 評分和后循環腦梗死與靜脈溶栓后血管再閉塞呈獨立相關關系,表現為入院時NIHSS 評分越高,梗死部位發生于后循環,溶栓后血管再閉塞的風險就越高。Gong等[17]發現在接受靜脈溶栓治療的急性腦梗死患者中,NIHSS 評分可能與溶栓后早期神經功能惡化有關。后循環腦梗死多與椎基底動脈粥樣硬化病變原位血栓形成有關,臨床表現形式復雜多樣,預后較差[18]。因此,NIHSS 評分和后循環腦梗死也可能是靜脈溶栓后血管再閉塞的獨立預測因素。基于血漿PAF 水平、NIHSS 評分和后循環腦梗死構建的預測模型預測溶栓后血管再閉塞的AUC 為0.816。然而,本研究為單中心、前瞻性研究,樣本量較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因采用NIHSS 評分的變化作為判斷血管再閉塞的依據,在反映血管狀況方面有所欠缺。雖然本研究具有上述局限性,但是仍對血漿PAF 水平與溶栓后血管再閉塞之間的關系具有一定的提示意義,可為進一步多中心、大規模前瞻性研究提供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