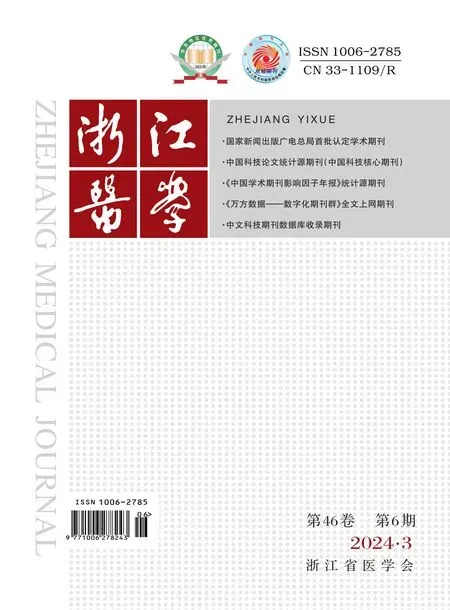血管內超聲檢測對缺血伴非阻塞性冠狀動脈疾病患者用藥及預后的影響
吳彥 胡燕華 邊長勇
缺血伴非阻塞性冠狀動脈(下稱冠脈)疾病(ischemia and non-obstructiv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INOCA)指具有心肌缺血相關表現,但冠脈造影(coronary angiography,CAG)檢查未發現阻塞性冠脈狹窄的疾病,冠脈狹窄程度≤50%[1]。研究證實,INOCA患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MACE)風險顯著升高,但發病機制尚不明確[2-4],由于目前INOCA 尚缺乏足夠的循證醫學診療依據,臨床醫師往往忽視積極的用藥治療。與CAG 比較,血管內超聲(intravascular ultrasound,IVUS)在評估冠脈病變的形態、性質及分布等方面具有一定優勢。本研究分析IVUS對INOCA患者用藥及預后的影響,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選擇2019 年8 月至2021 年7 月上海市普陀區利群醫院心內科收治的INOCA 患者160 例,男47例,女113 例;年齡40~81(64.85±7.60)歲。納入標準:有胸悶、胸痛癥狀,心電圖ST-T 改變,結合CAG 檢查診斷為INOCA 的首診患者。排除標準:合并嚴重糖尿病、肝腎功能損傷;其他不能耐受常規冠脈疾病用藥;妊娠;隨訪過程中依從性不佳。根據患者有無行IVUS 檢查將患者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1。本研究經本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批準文號:RT-202014),患者或家屬均知情同意。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1.2 方法
1.2.1 影像學檢查 采用德國西門子公司醫用血管造影X 線機(Artis zee 系列)對兩組患者行CAG 檢查,采集冠脈狹窄程度、有無肌橋等信息。觀察組另行IVUS檢查,采用美國波士頓公司的IVUS 系統(探頭頻率60 MHz,機械或旋轉式探頭),于CAG 檢查后采集冠脈斑塊負荷、斑塊穩定性、有無肌橋等信息。肌橋的明確診斷觀察組以IVUS 為準,對照組以CAG 為準。對觀察組按IVUS 檢查結果再分為重度狹窄亞組(斑塊負荷≥30%)和輕度狹窄亞組(斑塊負荷<30%)。
1.2.2 隨訪 分別于兩組患者出院后1、3、6、9、12個月門診隨訪或電話隨訪,記錄兩組患者用藥情況和1 年內發生MACE 的情況。(1)用藥情況。包括他汀類藥物、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angiotensio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ACEI)、血管緊張素受體拮抗劑(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ARB)、β 受體阻滯劑、鈣通道阻滯劑。比較重度狹窄、輕度狹窄亞組患者用藥情況,包括他汀類藥物、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上述7 類藥物。計算兩組患者用藥總分:將上述7 類藥物各計為1分,患者每服用其中1類藥物得1分,未服用該類藥物得0 分,所得分值的總和即為該患者的用藥總分(0~7 分)。(2)1 年內發生MACE 的情況。包括再發心絞痛、再次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心源性死亡、嚴重心律失常等。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6.0 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兩組患者用藥總分為結果變量,建立線性回歸模型,分析有無行IVUS 檢查對兩組患者用藥總分的影響。以兩組患者1 年內有無發生MACE 為結果變量,將有無行IVUS 檢查、CAG 評級、有無服用他汀類藥物、阿司匹林、氯吡格雷、ACEI、ARB、β 受體阻滯劑、鈣通道阻滯劑作為自變量,采用Cox 回歸模型,分析兩組患者1 年內發生MACE 的影響因素。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影像學檢查結果比較 觀察組IVUS發現CAG 無法發現的不穩定斑塊38 例(47.5%),并發現CAG 未發現的肌橋5 例(6.3%)。兩組患者CAG 檢查的冠脈狹窄程度、CAG 發現的肌橋占比、明確診斷的肌橋占比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影像學檢查結果比較
2.2 兩組患者用藥情況比較 觀察組ACEI、ARB、β受體阻滯劑的使用率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兩組患者他汀類藥物、阿司匹林、氯吡格雷、鈣通道阻滯劑的使用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用藥情況比較[例(%)]
2.3 重度狹窄、輕度狹窄亞組患者用藥情況比較 重度狹窄亞組他汀類藥物的使用率高于輕度狹窄亞組,鈣通道阻滯劑的使用率低于輕度狹窄亞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兩亞組其他藥物的使用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4。

表4 重度狹窄、輕度狹窄亞組患者用藥情況比較[例(%)]
2.4 兩組患者用藥總分和有無行IVUS 檢查的回歸分析 回歸分析顯示,行IVUS 檢查是兩組患者用藥總分的影響因素(P<0.05),見表5。

表5 兩組患者用藥總分和有無行IVUS 檢查的回歸分析
2.5 兩組患者1 年內發生MACE 的比較 隨訪1 年內,觀察組發生MACE 3 例(3.8%),對照組發生MACE 10例(12.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103,P=0.043)。
2.6 兩組患者1年內發生MACE的影響因素分析 Cox回歸模型顯示,行IVUS 檢查和CAG 評級是兩組患者1 年內發生MACE 的影響因素(均P<0.05),見表6。
3 討論
INOCA 是一組復雜的臨床綜合征,其發生機制可能是多重因素共同參與的結果[5]。INOCA 患者多同時合并冠脈粥樣硬化,如果沒有得到明確診斷和及時治療,可導致MACE 風險升高,甚至猝死等嚴重后果[6]。CAG 作為冠脈疾病診斷的金標準,受限于二維成像,難以檢測出冠脈血管壁的病變特點[7]。為補充CAG 的不足,IVUS 等評估手段逐漸開始在臨床使用,可以獲取冠脈橫截面圖像,檢測出斑塊負荷、斑塊性質等信息[8]。全面地了解冠脈情況,有助于臨床醫師指導患者用藥,從而影響患者的預后。
本研究發現,觀察組IVUS 發現CAG 無法發現的不穩定斑塊38 例(47.5%),并發現CAG 未發現的肌橋5 例(6.3%),提示IVUS 識別冠脈斑塊和肌橋的靈敏度比CAG 高,可發現CAG 未發現的隱匿性病變,并在評估斑塊穩定性方面比CAG更有優勢[9-10]。觀察組ACEI、ARB、β 受體阻滯劑的使用率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提示通過IVUS檢查讓臨床醫師更全面、準確地把握患者的冠脈病變情況,促進了早期患者用藥。其中,ACEI、ARB 類藥物是冠心病使用的基礎藥物[11],通常與β 受體阻滯劑等藥物聯用協同改善患者冠脈狹窄,對不穩定斑塊有積極治療作用[12]。重度狹窄亞組他汀類藥物的使用率高于輕度狹窄亞組,鈣通道阻滯劑的使用率低于輕度狹窄亞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提示IVUS能夠協助臨床醫師更好地了解冠脈斑塊情況,從而促進患者用藥[13]。回歸分析顯示,行IVUS檢查是兩組患者用藥總分的影響因素。隨訪1 年內,觀察組發生MACE 3 例(3.8%),對照組發生MACE 10 例(12.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Cox風險分析顯示,行IVUS檢查和CAG分級是兩組患者1 年內發生MACE 的影響因素。以上結果,一方面說明IVUS 能夠對CAG 進行更好的補充,提供更精細的評估和預測MACE 的依據[14-16];另一方面也說明IVUS能夠為患者用藥提供更多信息,通過改變患者用藥決策從而改善患者的預后。聯用CAG 和IVUS,可在冠脈疾病的診療中發揮更大效用[17]。
綜上所述,行IVUS 檢查能夠指導INOCA 患者用藥,改善預后,值得推廣。然而本研究尚存在不足之處:研究樣本量較小,未深入分析冠脈病變的多重影響因素,今后還需進一步論證;研究時間較短,隨訪1年時間,而很多冠脈疾病處于慢性階段,故后續研究需延長隨訪時間[5,18];行IVUS 檢查的患者可能對自我健康的關注度更高,患者用藥更積極,造成一定的偏倚,需要通過進一步的前瞻性對照研究進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