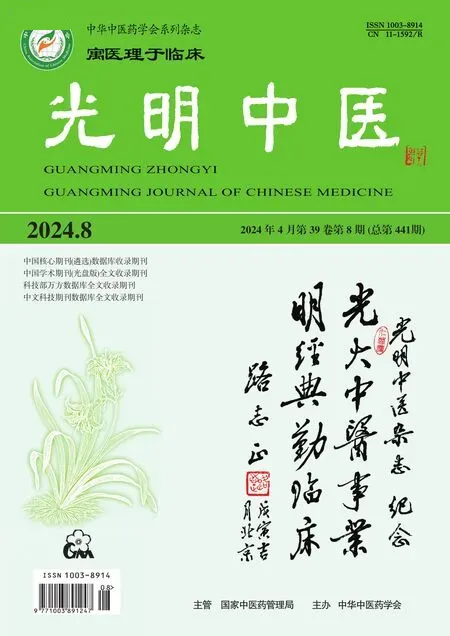中和思想指導下葦莖湯治療胸腔積液臨床觀察*
張佳秀 朱保成
胸腔積液是胸膜腔內積聚了過多液體的一類病癥,可由多種肺部疾病引起,臨床將其分為漏出性胸腔積液和滲出性胸腔積液[1]。漏出性胸腔積液的最常見病因為充血性心力衰竭,在急性腎小球腎炎、肝硬化等疾病中也可見到。而滲出性胸腔積液常見于結核性胸腔積液、類肺炎性胸腔積液、惡性胸腔積液,其中以結核性胸腔積液在臨床滲出性胸腔積液中最為常見[2-4]。胸腔積液屬于中醫學“痰飲、懸飲、飲證”范疇,是在多種致病因素作用下導致肺、脾、腎等功能失調,津液不歸正化,或代謝失常水飲停于胸腔而致的痰飲類疾病。中醫病因病機認為,胸腔積液的發生多因外邪犯肺、飲食傷及脾胃、素體陽虛或肝膽濕熱等導致肺、脾、腎等功能失常,氣機失調,津液變生水濕痰飲,停聚胸膈。其病因以內因、內熱、虛邪、水濕等常見,病機以痰熱蘊肺、水飲內停、痰瘀互結、氣陰兩虛、肺脾兩虛、血瘀多見,主要病位在胸膈,病變臟腑涉及肺、脾、腎、肝等。胸腔積液的主要癥狀以胸悶、氣短、呼吸困難為常見,在治療上常以胸腔閉式引流聯合藥物治療為主,可減少積液量、緩解憋悶等癥狀,但在重大疾病如肺癌、肺心病為病因引起胸腔積液的治療中,效果欠佳[5]。
葦莖湯是由唐代名醫孫思邈等所收集的方劑,是清肺化痰、逐瘀排膿的著名經方,該方的藥物組成及配伍相對簡易,由桃仁、薏苡仁、冬瓜仁、葦莖組成,是中醫治療肺癰(熱毒壅滯、痰瘀互結證)的名方。中和醫派在長期臨床實踐中發現,對于在胸腔積液患者的治療過程中聯合應用葦莖湯,能夠有效減輕患者的憋悶癥狀,促進積液代謝,減少滲出[6],故做以下研究報道。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擇2022年1月—2023年1月九江市第一人民醫院心內科門診治療胸腔積液患者60例,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觀察組和試驗組,各30例。其中,試驗組男女各15例;年齡18~80歲,平均(66.53±4.03)歲;平均胸腔積液深度(3.77±1.71)cm。觀察組男女各15例;年齡18~80歲,平均(67.67±5.34)歲;平均胸腔積液深度(3.77±1.71)cm。2組基線數據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 診斷標準西醫診斷:胸腔積液診斷標準:參照惡性胸腔積液診斷與治療專家共識[7]及胸腔積液診斷的中國專家共識[8],擬定以下診斷標準: ①癥狀體征:呼吸困難、喘憋、氣短、胸痛、胸悶、咳嗽,伴全身癥狀如體質量下降、 納差、乏力,晚期兼見惡液質。肺部叩診濁音,聽診呼吸音減弱或消失,觸覺語顫減弱。 ②經B超證實存在胸腔積液者。中醫診斷:參考《中醫內科學》[9]懸飲病的論述及《實用中醫診斷學》[10]氣血津液辨證要點,中醫辨病屬懸飲病,辨證屬瘀水互結證,臨床可見喘憋、氣短、咳嗽、胸悶、胸痛等癥狀及身體困重、小便不利、面色晦暗、口唇青紫、胸痛夜間尤甚,痛處固定等兼癥,即可診斷。
1.3 納入標準①符合中醫、西醫診斷標準,由呼吸系統疾病引起該癥者; ②經B超檢驗胸腔積液深度3~5 cm的滲出性胸腔積液者;③預計生存期≥3 個月; ④年齡在 18~90歲(包括 18、90 歲);⑤無心、肝、腎疾病等其他嚴重的合并疾病; ⑥依從性好,無精神病史及嚴重的心理障礙,意識清楚且自愿參與。
1.4 排除標準①有嚴重基礎病或并發癥,如免疫系統疾病、血液病、重癥感染性疾病者;②經檢查積液見血性分泌物者;③正在接受放化療治療者;④發病后近2個月內參加過其他研究者。
1.5 方法
1.5.1 基礎治療根據患者自身情況進行內科常規對癥處理,適當應用消炎、抗感染及控制基礎病等治療。
1.5.2 分組治療觀察組采用常規西醫治療;試驗組在西醫治療的基礎上采用葦莖湯治療。葦莖湯組成:葦莖30 g,薏苡仁、冬瓜仁各 15 g,桃仁50枚。將方劑正確配比后,用水煎至500 ml,早中晚各1次服用,每日1劑。根據患者不同病情進行臨證加減,如:積液成膿液者可加甘草、桔梗、浙貝母;方劑正確配比后,用水煎至300 ml,早晚各1次服用,每日1劑。14 d為1個療程,共3個療程。
1.6 觀察指標及療效評價標準療效:治療后對2組患者行B超檢測胸水量,顯效:治療后患者主要癥狀、胸水消失或基本消失;有效:治療后患者胸水量減少≥50%;無效:治療后患者癥狀胸水量無改善或加重,胸水量減少<50%。總有效率=(顯效+有效)例數/總例數×100%。肺功能指標:治療后使用肺功能測試儀測試2組FVC、FEV1、FEV1/FVC、PEER指標水平。

2 結果
2.1 療效2組比較,試驗組治療總有效率高于觀察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2組患者療效比較 (例,%)
2.2 肺功能治療后,試驗組FVC、FEV1、FEV1/FVC、PEER均高于觀察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2組患者治療后肺功能比較 (例,
3 討論
胸腔積液與“懸飲”緊密相扣,為臨床常見病癥。中醫整體觀念強調人是一個整體,五臟之傷皆可生痰,但發病主要是肺、脾、腎功能失調,水液不運而化為痰飲停于胸膈。肺居上焦而主氣,又宣發肅降和通調水道,為水之上源。外感邪氣傷肺,或痰瘀氣滯,或氣陰不足,均可致肺氣失于宣達,通調失職,津液失于布散聚而為痰。脾主運化水濕,是人體氣機升降之樞紐。若濕邪困脾,或脾陽、脾氣虧虛而致脾虛不運,水谷不化,上不能輸精以養肺,反而變生痰飲于肺,下不能助腎以制水,水寒之氣反傷腎,必致水液內停,流溢四處波及五臟。腎在下焦,為主水之臟,司膀胱而泌清濁,其氣化功能正常才能使水液得以升清降濁。若腎氣腎陽不足,蒸化失司則可致水濕泛濫。
東漢張仲景在《金匱要略》中對懸飲病名描述有云:“飲后水流在脅下,咳唾引痛,謂之懸飲”。“懸飲”屬于中醫學中廣義“痰飲”的范疇,痰飲為患,由肺、脾、腎功能失常,三焦不利,氣化失司,津液聚化而成,其中尤以脾之失運為發病之關鍵。《金匱玉函要略輯義》中記載:“三焦氣塞,脈道壅閉……又因脾土不能宣達”。表明三焦氣機失于調達疏泄,又兼脾臟運化水液失司是導致水飲生成的重要因素。綜上,懸飲由肺脾腎三臟水液代謝功能失常,致機體經脈氣血津液運行受阻,營衛郁滯,三焦水道不通,化生水飲,停聚于胸脅所引起。中和醫派認為,“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精并行”為胸腔積液病因病機的論述奠定了基礎。懸飲由于肺脾腎三臟水液代謝功能失常,機體經脈氣血津液運行受阻,三焦水道不通,水飲停聚于胸脅而致病,引起胸腔積液的基礎病,如感染、炎癥、肺癌等本身便能阻遏臟腑經絡氣血運行,致氣滯血瘀痰濁熱毒內生,瘀血日久進一步阻滯氣機,影響肺脾腎及三焦行其運化布散水液、通調水道之職能,津液停聚化生水飲與瘀血互結于胸脅而發為此病,治療以利水活血、通陽化氣為主,輔以健脾助運,以杜生痰之源,以助水濕運化。治療上中和醫派認為應遵從“病痰飲者, 當以溫者和之”的原則,治法當以溫陽健脾以助運化為本,杜生痰之源,助水濕運化,并通過滲濕、攻逐之法達到標本兼顧的目的[11,12]。葦莖湯是古代名家根據臨床經驗用來治療“肺癰”的效方,由葦莖、薏苡仁、冬瓜仁、桃仁組成,多用于熱毒壅肺,痰瘀互結,血敗肉腐成癰所致的呼吸系統疾病,治療以清肺化痰,逐瘀排膿為主[13-17]。《黃帝內經》有言:“熱盛則肉腐,肉腐則成膿”,邪熱犯肺,傷及血脈,致熱壅血瘀,若久不消散則血敗肉腐,乃成肺癰;癰膿潰破,借口咽而出,故咳吐腥臭黃痰膿血;痰熱瘀血,互阻胸中,因而胸中隱痛;舌紅苔黃膩,脈滑數皆痰熱內盛之象[18]。方中葦莖甘、寒,歸肺、胃經,其性甘寒輕浮,善清肺熱,故為君藥。葦莖又叫蘆根,有研究表明,蘆根提取物蘆根多糖具有抗氧化、抗炎、保護肝腎等作用[19,20]。冬瓜仁味甘,性微寒,入肺、小腸經,有清熱化痰,利濕排膿之功,能清上徹下,肅降肺氣,與葦莖配合則清肺宣壅,滌痰排膿。冬瓜子水提物及甲醇提取物可清除氧自由基,對抗脂質過氧化,冬瓜子甲醇及乙醇提取物均有良好的抗炎、解熱、鎮痛作用[21]。薏苡仁味甘、淡,性涼,歸脾、胃、肺經,其甘淡微寒,上清肺熱而排膿,下利腸胃而滲濕,二者共為臣藥。薏苡仁的主要活性成分酯類化合物可抑制腫瘤細胞增殖,非淀粉多糖化合物可增強免疫活性,多酚類物質發揮抗氧化作用、下調促炎介質表達,黃酮類化合物可抗氧化、清除氧自由基,內酰胺類化合物抗炎鎮痛作用良好,三萜類化合物可抗癌、降低血壓[22]。桃仁味苦、甘,性平,歸心、肝、大腸經。《名醫別錄》記載:“止咳逆上氣,消心下堅,除卒暴擊血,破癥瘕,通脈,止痛”。活血逐瘀,可助消癰,是為佐藥。方僅四藥,結構嚴謹,藥性平和,共具清熱化痰、逐瘀排膿之效[23,24]。
臨床研究可見,葦莖湯治療痰熱壅肺型重癥肺炎,臨床癥狀改善優于對照組,且能快速下調血清降鈣素原,降低序貫器官功能衰竭評估評分,減少二次感染的風險[25]。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葦莖湯化裁在減輕炎癥反應,改善肺循環及氣道阻塞等方面有明顯療效,可明顯提高重癥患者治愈率,對于新冠感染高熱期、內閉外脫期及正虛邪戀期的患者,運用千金葦莖湯加減治療,可防治肺纖維化,具有協同增效之功。葦莖湯在慢性呼吸疾病當中可改善患者肺功能及動脈血氣等指標,明顯患者提高生活質量。中藥口服與留置引流管、胸腔內灌注等有創治療相比,具有方便易行、依從性高、安全性高等優點[26-29]。西醫臨床中,長時間應用利尿藥會導致患者電解質紊亂,引起乏力、惡心嘔吐、肌肉痙攣、心律失常等不良反應,而留置引流管、胸膜固定術等有創治療的對象大多為大量胸水患者,并不適用于輕、中癥患者,中藥聯合西藥的治療為少、中量胸腔積液患者與不耐受有創療法的患者提供了另一種治療思路,可緩解臨床癥狀,提升治療效果[30-33]。
中和醫派長期的臨床實踐當中,總結各醫家的臨床經驗及試驗研究,進一步應用和發揮葦莖湯的臨床應用。葦莖湯化裁在減輕炎癥反應,改善肺循環及氣道阻塞等方面有明顯療效,可明顯提高重癥患者治愈率,值得臨床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