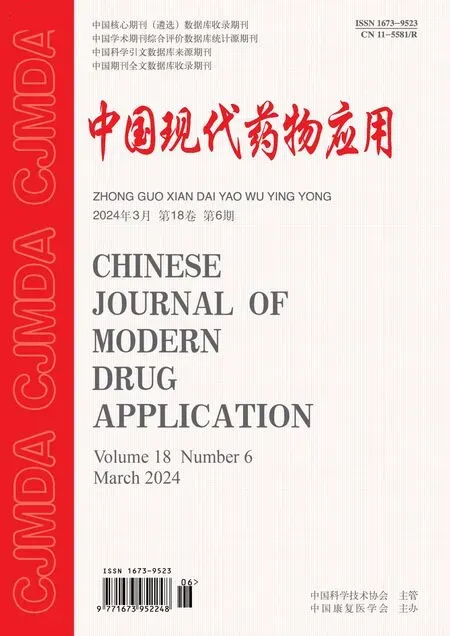妊娠期糖尿病對于子代新生兒B族鏈球菌感染免疫功能的影響研究
鄭晨 朱瑩雯 石嫻靜 張黛佳 沈秋萍
感染性疾病是新生兒期死亡的主要病因之一, 其中B 族鏈球菌(group B streptococcus, GBS)是臨床最為常見的革蘭陽性球菌之一, 同時也是引起新生兒敗血癥的主要病原體, 可導致肺炎、腦炎等嚴重感染, 甚至多器官功能衰竭。目前已證實與血糖正常的女性相比,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患者的外陰陰道感染率和陰道生態失調率更高[1]。流行病學證據表明, 在GDM 孕婦泌尿生殖器標本中分離出的最常見細菌是GBS, 北美孕婦中經菌落調整后的比例為21%~25%, 全球為18%[2]。因此, 孕母存在GDM 為其子代新生兒發生GBS 感染的高危因素之一[3]。目前GDM 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問題。但目前對于新生兒存在GBS 感染時GDM 孕母對子代免疫功能的影響需更多研究。因此, 本研究通過將GBS 感染新生兒分為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以及孕母非GDM 新生兒感染組, 另選同期單純性高膽紅素血癥住院新生兒作為非感染對照組, 應用流式細胞術檢測三組新生兒的外周血CD3+、CD4+、CD8+T 細胞計數以及CD4+/CD8+水 平, 炎 癥 因 子IL-6、IL-10、IL-6/IL-10 以 及CD3-CD56+CD16+NK 細胞的水平。探討GDM 孕母分娩新生兒在先天性感染的情況下其免疫系統變化以及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蘇州大學附屬常熟市第一人民醫院新生兒科自2020 年12 月~2023 年3 月期間GBS感染的住院新生兒102 例, 其中細菌性肺炎新生兒50 例, 敗血癥新生兒52 例;將48 例母親存在GDM的新生兒納入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 其余54 例母親孕期血糖監測正常的新生兒納入孕母非GDM 新生兒感染組, 另選擇同期住院單純性高膽紅素血癥新生兒52 例為非感染對照組。三組新生兒均為足月產新生兒, Apgar 評分:1 min 評分均≥8 分, 5 min 評分均為10 分。三組間孕母年齡、新生兒性別、出生胎齡、出生體重、分娩方式比較, 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孕母體質量指數(BMI)高于孕母非GDM 新生兒感染組和非感染對照組, 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三組一般資料比較(n, ±s)

表1 三組一般資料比較(n, ±s)
注:與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比較, aP<0.05
項目 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n=48) 孕母非GDM 新生兒感染組(n=54) 非感染對照組(n=52)新生兒性別(男/女) 25/23 28/26 27/25新生兒出生體重(g) 3885±503 3268±476 3503±417分娩方式(順/剖) 32/16 37/17 40/12新生兒出生胎齡(周) 38.68±1.32 38.33±1.56 38.75±1.69孕母BMI(kg/m2) 25.17±4.52 18.23±2.51a 20.45±3.28a孕母年齡(歲) 33±5 32±7 31±6
1.2 納入及排除標準 GBS 感染新生兒納入標準:①新生兒早發型GBS 肺炎:生后出現氣促、呻吟、吐沫、發紺、呼吸暫停等肺炎的臨床表現, 影像學檢查符合肺炎表現, 氣管內分泌物或生后1 h 內胃液培養GBS陽性[4];②新生兒早發型GBS 敗血癥[5]:存在敗血癥相關臨床表現, 血液非特異性感染指標≥2 項陽性, 且血培養或無菌腔體內培養出GBS 病原體;③母親孕期陰道分泌物GBS DNA 陽性。其中母親孕期GDM 診斷符合2014 年《妊娠合并糖尿病診治指南》[6]以及中華醫學會后續發布的《妊娠期高血糖診治指南(2022)》[7]。GBS 感染新生兒排除標準:①孕母孕前糖尿病者;②孕母孕前有免疫系統疾病及家族史;③孕母同時有其他妊娠期合并癥及并發癥者;④孕母孕周<37 周。非感染對照組納入標準:新生兒血總膽紅素以間接膽紅素值升高為主, 無窒息、感染、肝功能異常, 膽紅素水平未達換血指征, 非溶血性疾病所致黃疸, 新生兒TORCH 以及巨細胞病毒脫氧核糖核酸(CMV-DNA)檢查陰性, 孕母孕期及圍生期未患感染性疾病, 無不良孕產史、無基礎疾病及慢性疾病(包括GDM), 無特殊藥物使用史, 父母均無嚴重過敏性疾病, 無家族遺傳性疾病史。本研究經常熟市第一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所有新生兒家屬簽署知情同意書。
1.3 研究方法 入組新生兒在入院 24~48 h 內用肝素鈉抗凝負壓真空采血管采取空腹靜脈血2 ml, 在 4 h內對標本進行標記處理。采用流式細胞術(流式細胞 儀 器:安 捷 倫D2060R) 檢 測CD3+、CD4+、CD8+、CD3-CD56+CD16+NK 細 胞 計 數(CD3+、CD4+、CD8+、CD56+、CD16+檢測試劑:江蘇鹿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IL-6、IL-10 水平(細胞因子聯合檢測試劑盒:杭州賽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批號:JS-SOP-006)。
1.4 觀察指標 比較三組新生兒免疫指標水平, 分析NK 細胞與淋巴細胞亞群的相關性。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6.0 進行統計分析。正態分布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 三組資料的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 組間兩兩比較采用LSD-t 法;非正態分布資料采用中位數(第25 百分位數, 第75 百分位數)[M(P25, P75)]表示, 三組間比較采用Kruskal-Wallis 檢驗;相關性檢驗采用Pearson 檢驗。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三組新生兒免疫指標水平比較 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新生兒的CD3+、CD4+、CD8+、CD4+/CD8+、CD3-CD56+CD16+細胞計數均明顯低于孕母非GDM 新生兒感染組和非感染對照組, 孕母非GDM 新生兒感染組低于非感染對照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新生兒的IL-6、IL-6/IL-10 水平均高于孕母非GDM 新生兒感染組, 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和孕母非GDM 新生兒感染組新生兒的IL-6、IL-10 水平均高于非感染對照組, 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新生兒的IL-6/IL-10 水平高于非感染對照組, 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和孕母非GDM 新生兒感染組新生兒的IL-10 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孕母非GDM 新生兒感染組和非感染對照組新生兒的IL-6/IL-10 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三組新生兒免疫指標水平比較[ ±s, M(P25, P75)]

表2 三組新生兒免疫指標水平比較[ ±s, M(P25, P75)]
注:與孕母非GDM 新生兒感染組比較, aP<0.05;與非感染對照組比較, bP<0.05
項目 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n=48)孕母非GDM 新生兒感染組(n=54) 非感染對照組(n=52) F/H P CD3+細胞計數(個/μl) 2001±790ab 2495±559b 3635±833 14.914 <0.05 CD4+細胞計數(個/μl) 1380(1110, 1618)ab 1682(1460, 1917)b 2969(2017, 3286) 20.809 <0.05 CD8+細胞計數(個/μl) 546±214ab 651±281b 971±245 12.773 <0.05 CD4+/CD8+ 2.13±0.70ab 2.71±1.09b 3.44±0.73 9.070 <0.05 CD3-CD56+CD16+細胞計數(個/μl) 119±57ab 206±57b 399±56 93.603 <0.05 IL-6(pg/ml) 149.91(72.12, 478.37)ab 40.73(35.56, 78.89)b 6.98(4.52, 10.12) 37.432 <0.05 IL-10(pg/ml) 17.49(6.60, 21.79)b 10.34(5.73, 21.43)b 1.57(4.52, 10.12) 25.314 <0.05 IL-6/IL-10 13.98(7.43, 21.16)ab 3.96(3.41, 6.44) 3.50(2.84, 4.20) 33.113 <0.05
2.2 相關性分析 經Pearson 相關性分析, CD3-CD56+CD16+NK 細胞與CD3+、CD4+以及CD8+T 細胞呈正相關(r=0.588、0.580、0.461, P<0.05)。見表3。

表3 NK 細胞與淋巴細胞亞群的相關性分析
3 討論
早發型GBS 感染的新生兒約90%在出生后12 h內進展為新生兒肺炎或敗血癥, 晚發型GBS 感染新生兒中約50%出現腦膜炎[8]。這種年齡特異性易感性原因可能與新生兒的免疫系統特點有關。研究表明, 孕期母體營養的失衡, 無論是缺乏還是過量, 都會對新生兒出生時的免疫力和生命早期的免疫成熟產生相當大的影響[9]。因此了解影響新生兒先天免疫系統的因素,尤其母體因素的影響, 對于制定產前干預以及產后康復策略至關重要。
本研究結果顯示, 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新生兒的CD3+、CD4+、CD8+、CD4+/CD8+、CD3-CD56+CD16+細胞計數均明顯低于孕母非GDM 新生兒感染組和非感染對照組, 孕母非GDM 新生兒感染組低于非感染對照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在感染GBS情況時, GDM 孕母娩出新生兒的免疫功能有明顯降低且存在細胞免疫調節紊亂情況。細胞因子方面: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新生兒的IL-6、IL-6/IL-10 水平均高于孕母非GDM 新生兒感染組, 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和孕母非GDM 新生兒感染組新生兒的IL-6、IL-10 水平均高于非感染對照組, 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新生兒的IL-6/IL-10 水平高于非感染對照組, 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和孕母非GDM 新生兒感染組新生兒的IL-10 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孕母非GDM 新生兒感染組和非感染對照組新生兒的IL-6/IL-10 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T 淋巴細胞亞群對維持機體細胞免疫功能相對穩定具有重要意義。CD3+是外周血成熟T 淋巴細胞的標記物, 其水平下降反映T細胞免疫功能降低。CD4+是輔助性T細胞、調節性T細胞的表面抗原, CD8+主要為細胞毒性T細胞亞群的表面抗原。在正常狀態下, 初始CD8+T 細胞的啟動是以高度可控的方式進行的, 主要是為了防止對正常健康組織產生反應, 前提是需要細胞內在和外在因素的混合物來正確擴增初始CD8+T 細胞并使其發揮功能, 在各種外源性因素中, CD4+T 細胞的幫助是形成初級CD8+T 細胞反應的關鍵。在CD4+T 細胞的幫助下, 在CD8+T 細胞內發生指導性編程防止腫瘤壞死因子相關的凋亡誘導配體(TRAIL)介導的CD8+T 淋巴細胞的活化, 從而誘導細胞死亡。因而在感染期間由于CD4+T 細胞的數量減少和功能缺陷可導致大量CD8+T 細胞反應受損[10]。CD4+/CD8+是評價機體免疫功能的主要指標之一[11],感染新生兒的CD4+/CD8+較非感染對照組低, 提示感染新生兒細胞免疫功能受到抑制。本研究顯示, 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CD3+、CD4+以及CD4+/CD8+水平較非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低, 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 提示孕母患GDM 的子代新生兒當存在感染情況時T 細胞功能受到更明顯的抑制, 且存在細胞免疫功能紊亂。韓國近年的文獻顯示[12], 其國內母親患有GDM 的新生兒敗血癥發病率明顯高于母親血糖監測正常組, 考慮如本研究所示GDM 孕母的子代免疫系統功能不全可能為致病原因之一。
一旦GBS 通過宿主細胞屏障進入血流或深部組織, 則需要機體啟動固有免疫反應進行清除。NK 細胞是固有免疫應答中的關鍵細胞, 其主體為CD3-CD16+CD56+淋巴細胞, NK 細胞表面CD16 表達陽性率達90%, CD56 表達陽性率達95%, CD3 往往不表達[13],其代表較成熟的NK 細胞, 殺傷功能強。在非致敏條件下即可產生細胞因子、趨化因子和溶細胞效應, 從而在感染和傷害暴露的早期快速調節免疫反應并直接參與宿主防御[14]。本研究中GBS 感染新生兒CD3-CD16+CD56+NK 細胞計數均低于非感染對照組(P<0.05),考慮為感染后NK 細胞消耗所致。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CD3-CD16+CD56+NK 細胞計數低于非孕母GDM新生兒感染組, 兩者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 提示孕母存在GDM 的宮內環境對于娩出新生兒的固有免疫功能存在影響。既往有研究發現, 患GDM 的孕母臍血中CD3-CD16+CD56+NK 細胞明顯減少, 考慮原因為患GDM 女性在妊娠期免疫平衡發生改變, 全身環境為促炎環境所致[15]。本研究與既往研究雖角度不同, 但結論一致。由此可以推論, 由于該類新生兒固有免疫功能低下會使得患GDM 的孕母娩出的新生兒對GBS更具有特殊的易感性。
本研究中, 與非感染對照組相比, GBS 感染新生兒的炎癥細胞因子IL-6、IL-10 水平明顯增高。其中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新生兒的IL-6、IL-6/IL-10水平均高于孕母非GDM 新生兒感染組新生兒。IL-6是在炎癥過程中產生大量的促炎細胞因子。IL-6 作為T 細胞活化的信號, 其誘導B 細胞分泌抗體和細胞毒性T 細胞分化, 參與全身炎癥和自身免疫反應[16]。同時胎盤產生的高IL-6 可進入母體和胎兒循環[17], 考慮此為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新生兒IL-6 水平較非孕母GDM 感染組明顯增高的原因。已知GDM 不僅是一種代謝性疾病, 也是一種低級炎癥反應, 這種炎癥性疾病普遍存在于血清、脂肪組織和胎盤中[18]。通過胎盤中物質的交換, GDM 孕母的胎兒在子宮內就經歷了慢性的炎癥過程, 使得GDM 母親分娩的新生兒出現感染的風險增加[19], 甚至發生胎兒炎癥反應綜合征(fetal inf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FIRS)。而FIRS 的 特征即為胎兒血漿IL-6 濃度的升高[20]。此外, 產前炎癥還可導致循環和肺部免疫細胞反應性降低[21]。本研究中GBS 感染新生兒IL-6 均明顯高于非感染新生兒, 同時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IL-6 水平明顯高于非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 與以上相關文獻結論相符。
IL-10 在預防膿毒癥期間過度的促炎反應中發揮著重要作用[22]。IL-10 由不同類型的免疫系統細胞產生, 如單核細胞、巨噬細胞、T 和B 淋巴細胞以及NK細胞。研究表明, IL-10 的適當反應對全身炎癥反應綜合 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具有保護作用, 可以抑制促炎細胞因子產生[23], 但另一方面高水平的IL-10 與兒童、成人敗血癥的不良預后相關。由于IL-6 和IL-10 在炎癥過程中具有促進/耐受作用, 以控制通常的炎癥反應, 因此兩者之間的失衡可能導致過度炎癥或免疫抑制[24]。
目前相關研究結果顯示, 細菌感染后, 相比較其他細胞因子, IL-6 水平和IL-6/IL-10 水平對診斷新生兒敗血癥具有更高的敏感度和特異度[25]。IL-6/IL-10也可作為新生兒敗血癥有效抗菌治療的標志物[25]。因此本研究選擇上述指標進行分組分析, 結果顯示孕母GDM 新生兒感染組IL-6/IL-10 明顯高于孕母非GDM新生兒感染組以及非感染對照組, 提示孕母患GDM 的新生兒存在感染情況時出現更明顯的促炎介質以及抗炎介質的失衡。已知這些炎癥因子的產生和釋放以及平衡失調會使得一開始具有抗感染保護作用的炎癥反應轉為損傷自身組織器官的過度炎癥反應[26], 激活的巨噬細胞過度釋放介質可能會刺激多形核白細胞產生活性氧, 進而導致組織損傷和多器官衰竭, 進一步誘導新生兒膿毒癥初期的全身炎癥反應[27], 因此更可能影響孕母患GDM 的新生兒感染的預后。既往的臨床數據中發現, 并發新生兒壞死性小腸結腸炎(NEC)的新生兒感染病例IL-6/IL-10 比無并發癥的病例平均水平高9.5 倍。這一結果也提示IL-6 水平的異常升高而沒有IL-10 的調節可能是并發癥的重要指標[28]。
本研究支持孕母患GDM 的情況會造成一系列新生兒免疫系統的損傷, 特別是在新生兒存在感染情況下。既往研究表明, NK 細胞與淋巴組織和非淋巴組織中的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s, DC)之間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 從而進一步對CD4+T 細胞和CD8+T 細胞應對感染的反應產生顯著影響[29]。同時, 本研究探討了CD3-CD16+CD56+NK細胞與CD3+、CD4+和CD8+的關系,結果為CD3-CD56+CD16+NK 細胞與CD3+、CD4+以及CD8+T 細胞呈正相關(r=0.588、0.580、0.461, P<0.05),也與上述文獻結果相一致。因此免疫系統的損傷存在“一損俱損”的情況。
綜上所述, GDM 不僅對孕婦本身有影響, 對其胎兒的宮內環境以及娩出后新生兒的免疫功能均在明顯的影響, 新生兒的免疫功能受損直接影響新生兒感染性疾病的嚴重程度和預后, 因此, 防治GDM 對于防治新生兒感染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 新生兒GBS 感染早期癥狀具有隱匿性, 因此及時對高危兒進行早期診斷、早期評估、早期治療對于臨床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于母親患有GDM 的新生兒, 在臨床工作中需注意免疫功能的監測, 對于明顯免疫功能受損的新生兒, 必要時需進行更積極的支持治療以及抗感染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