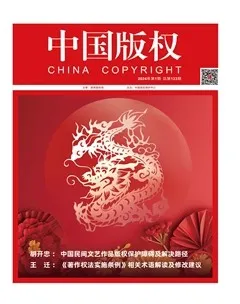論網絡版權侵權信息披露制度
呂炳斌 李壯
關鍵詞:版權侵權;信息披露;“通知-必要措施”規則;目的解釋;個人信息保護法
一、問題的提出
網絡版權侵權信息披露是解決網絡版權侵權的重要環節,司法實踐中對信息披露存在兩種傾向性見解,但兩種見解均存在一定問題。見解一是直接或間接認定網絡服務提供者存在網絡用戶信息披露的義務。但在并無有效法律依據的情況下,法院徑行認定網絡服務提供者存在信息披露義務,于法無據。見解二是認為網絡用戶信息披露是網絡服務提供者主張免責的證據。能否提供上傳者的用戶名、注冊IP地址、注冊時間、上傳IP地址、上傳時間以及聯系方式等證據,是判斷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屬于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的綜合考量因素。網絡服務提供者基于其自身侵權免責舉證的需要,往往會主動向司法機關披露網絡用戶信息。但在司法機關并未責令披露網絡用戶信息時,主動披露行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以下簡稱《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為履行法定職責或者法定義務所必需”的法律規范相沖突,違反了網絡服務提供者對網絡用戶信息的保密義務。
既有研究對信息披露制度的問題有所察覺,但從立法論出發的制度構建不僅存在內部沖突,還存在對信息披露模式認識不清的問題。部分立法論學者主張以公力救濟模式構建信息披露制度,賦予著作權人信息披露請求權,并允許著作權人通過法院行使信息披露請求權。該主張本質上為著作權人創設了一項請求權,但吊詭的是,網絡服務提供者拒絕履行并不承擔民事責任,而是對其可以施加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在實體法權利義務的內容上,添加訴訟程序內容,使得權利義務關系混亂而矛盾重重。而主張私力救濟模式,或者私力救濟與公力救濟相結合的學者,建議構建以“通知-反通知”規則為基礎的信息披露模式。但“通知-反通知”規則并未創設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披露義務。即使著作權人要求信息披露符合規則要件,但信息披露與否仍取決于網絡用戶是否同意,網絡服務提供者不存在與著作權人信息披露請求權對應的披露義務。因此“通知一反通知”規則本質上并非私力救濟模式。
通過立法論解決問題,可謂是最直接的路徑,但終究遠水解不了近渴,況且立法論本身存在諸多問題。在立法論尚未付諸實施的當下,并沒有直接的法律規范依據,司法實踐中的侵權信息披露問題該如何解決?本文嘗試從當下法律規范特別是著作權法相關配套法規及司法解釋出發,以“通知一必要措施”規則為切入點,展開網絡版權侵權信息披露制度的解釋論。
二、信息披露制度的解釋論切入點:“通知-必要措施”規則
(一)“通知-必要措施”規則的開放性特征
從“通知-刪除”規則到“通知-必要措施”規則,呈現出不斷增強的適用靈活性和開放性特征,而開放性特征構成了“信息披露”可以解釋為“必要措施”的基礎。
早期的“通知-刪除”規則將網絡服務提供者進行分類的做法,因不具有開放性而存在疏漏。我國在創設“通知-刪除”規則時受美國《數字千年版權法案》(以下簡稱DMCA)避風港規則的影響,在《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中對網絡服務提供者進行了分類,確定“通知-刪除”規則適用的類型。類型化的做法可以在著作權人、網絡服務提供者、網絡用戶之間尋找到利益平衡點,但類型化的做法面臨的問題是一旦出現了新型的網絡服務類型,如何重新找到平衡點。美國唱片業協會與威瑞森互聯網案所引發的爭議驗證了這個問題。新型的P2P技術造成版權侵權問題日益嚴重,但DMCA制定時P2P技術尚未普及,并非法律規范所規制的對象,因此明確規定適用類型的法院傳票制度無法適用于P2P領域。重寫DMCA以使其適應新的、不可預見的互聯網架構并不是法院的職權范圍,無論這種發展對音樂行業造成了多大的損害,或對電影和軟件行業構成了多大的威脅,法院在裁判中也只能對權利人表示惋惜。
“通知-必要措施”規則的開放性特征源于原《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以下簡稱原《侵權責任法》)。原《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在《條例》的基礎上,將刪除、斷開鏈接擴張到了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網絡服務提供者采取的措施種類擴大,不再局限于刪除、斷開鏈接。必要措施意義涵蓋極廣,給予了法院充分的司法空間,這是立法面對新型信息網絡發展所采取的及時調整。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保留了“通知-必要措施”規則,但對于《民法典》中的“通知-必要措施”規則的解釋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其一,從文義解釋出發,必要措施以實現與“刪除、斷開鏈接”的同等效果為準,即防止侵權損害內容擴大,使第三人不能再接觸該侵權內容。其二,對必要措施的解釋應當符合規范目的。“通知-必要措施”規則是以實現救濟著作權人權利、限制網絡服務提供者責任、保障網絡用戶權益為目的。DMCA創設的“通知-刪除”規則所采取的“刪除、禁止訪問”措施是依照當時的情形,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礎上,對著作權人實現最大程度保護,對網絡用戶實現最小程度損害,對互聯網產業發展影響最小的措施。對于當下我國新興的網絡服務提供者,《條例》規定的“刪除、斷開鏈接”是否還是合適的利益平衡點,需要對具體的網絡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務內容進行剖析論證,依據規范目的,正確理解“必要措施”的內涵。
是否承認規則的開放性特征導致司法實踐兩種不同觀點的分野。杭州刀豆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與長沙百贊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o(以下簡稱微信小程序案)與阿里云計算有限公司與北京樂動卓越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以下簡稱服務器租賃案)即是例證。微信小程序案一審法院對必要措施采取了文義解釋的立場,“刪除、斷開鏈接”與“等必要措施”意義基本相同,采取目的性限縮解釋,以《條例》中“刪除、斷開鏈接”的適用對象,限縮原《侵權責任法》“等必要措施”的適用對象。具有開放性特征的“通知-必要措施”規則被重新改造為“通知-刪除”規則。與之相反的是,微信小程序案二審法院及服務器租賃案法院則采用了目的解釋,其主要考慮如下:首先,案涉新型網絡服務提供者不屬于《條例》所規范的類型,應適用原《侵權責任法》“通知-必要措施”規則;接著,在考慮采用何種必要措施時,基于法律上對必要措施采取了開放態度,為實現權利人、網絡服務提供者、網絡用戶之間的利益平衡,應綜合考量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供服務的性質、形式、種類,侵權行為的表現形式、特點、嚴重程度等具體因素,以技術上能夠實現,合理且不超必要限度為宜。
“通知-必要措施”規則開放性特征不僅為司法實踐認可,學界也有此主張。從微信小程序案二審與服務器租賃案法院意見可以看出,司法實踐實際上更傾向于采用目的解釋的方式適用“通知-必要措施”規則。學者也認為“必要措施”的界定具有開放性和靈活性,“必要措施”的妥當性取決于與特定網絡服務的匹配性,可以根據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具體情形,以利益衡量的方式確定相應的具體措施。可以采取的具體必要措施,應當與具體網絡服務的類型相適應,并遵循“目的-手段”相一致的比例原則,不宜出現畸輕畸重等情形。“通知-必要措施”規則的目的在于平衡三方利益促進網絡侵權爭議解決,在此前提下“必要措施”所具有的開放性為“通知-必要措施”規則的適用創造了極大的靈活性。
(二)“通知-必要措施”規則的目的解釋:“信息披露”作為“必要措施”之內容
“通知-必要措施”規則的目的在于限制網絡服務提供者責任的同時,有效促成版權侵權爭議解決,實現權利人、網絡服務提供者、網絡用戶的利益平衡。
“通知-必要措施”規則的目的應當透過“避風港規則”進行探求。“通知-必要措施”規則肇始于“通知-刪除”規則,與傳票制度共同脫胎于DMCA規定的“避風港規則”。我國在進行制度引進的過程中,關注到了“通知-刪除”規則,但并未足夠關注到與之起到銜接作用的傳票制度。若僅從“通知-必要措施”規則自身探查其目的所在,會使其與“避風港規則”整體的目的理解發生偏差。DMCA創設的“避風港規則”包含“通知-刪除”規則與傳票制度。前者,著眼于限制網絡服務提供者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在“通知-刪除”規則中充當中立的信息傳遞者角色,由著作權人與網絡用戶對必要措施的采取進行平等的攻防對戰。后者,著眼于揭開網絡用戶的互聯網面紗,促成版權侵權爭議的解決。在“通知一刪除”規則無法有效解決侵權爭議之后,揭開網絡用戶的面紗,為著作權人提供了司法介入解決爭議的機會。至此,版權侵權爭議通過“通知一刪除”規則與傳票制度有效化解,三方利益得以實現平衡。
加拿大與日本法的“避風港規則”可以進一步佐證“通知一必要措施”規則的制度目的。加拿大制定的“避風港規則”以“通知-轉通知”和“無名氏訴訟”為主要內容。在加拿大《聯邦版權現代化法案》創設的“通知-轉通知”規則中,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著作權人通知后,負有將通知送達網絡用戶以及證據保存義務,其處于中立地位,不必采取“刪除、斷開鏈接”等措施。但著作權人可以依據民事訴訟法提出“無名氏之訴”要求網絡服務者履行信息披露。日本法的“避風港規則”設定了“通知-刪除”規則與網絡用戶信息披露義務。兩國在具體制度構建上存在差異,但均以網絡服務提供者中立性地位限制其責任,并通過信息披露促成著作權人與網絡用戶之間版權侵權爭議解決,實現三方利益平衡。
“通知-必要措施”規則的開放性特征,為彌補我國法律體系之下網絡用戶信息披露制度缺失,所造成的三者利益失衡,提供了目的解釋的空間。
為實現“通知-必要措施”規則平衡三方利益的目的,應當將“信息披露”解釋為“必要措施”的內容。網絡用戶信息披露是實現三方利益平衡的重要支點,信息披露關乎著作權人能否主張權利。在我國法的語境下,沒有網絡用戶的信息即無被告,沒有被告則無法主張權利。何者為必要措施?從“通知-刪除”規則到“通知-必要措施”規則,改變的是措施的內容,不變的是貫穿始終的制度目的——三方利益平衡。早期的利益平衡以事后的刪除、斷開鏈接為必要,當下的平衡以根據不同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具體內容采取審慎、合理的措施為必要。換言之,有利于利益平衡的措施為必要措施。既往的“通知一刪除”規則是封閉的規則,并沒有為之后可能出現的新情況預留變通的空間,無論如何,“披露涉嫌侵權的網絡用戶信息”必然不能被“刪除、斷開鏈接”的意義所包含。但“通知一必要措施”規則的開放性具有這樣的可能,“披露涉嫌侵權的網絡用戶信息”可以被“措施”的意義所涵蓋,是否“必要”則應當結合規則目的進行解釋。在目前缺少信息披露法律規范的情況下,披露信息對于三者利益平衡自然屬于必要。因此在目的解釋之下,限制網絡服務提供者責任以及網絡用戶的信息披露問題可以統一在“通知一必要措施”規則內解決。
隨著互聯網產業的快速發展,利益平衡的制度目的已經促使“通知-刪除”規則從事后控制侵權內容擴張,演變為事前控制網絡版權侵權泛濫。將信息披露融合于“通知-必要措施”規則更具有必要性。
不同于早期互聯網產業,當下網絡服務提供者規模日趨擴張,關于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應當承擔更高注意義務的討論,是對當下三者關系是否仍然維持在平衡點上的討論。美國和歐盟都沒有真正推翻“避風港規則”的原因,其實在于著作權人與互聯網平臺之間已經就侵權過濾技術的實施有了較為成熟的合作,換言之,針對技術和產業變遷帶來的問題,發達國家更多的是通過私人創制“通知-必要措施”規則的方式來應對。著作權人與網絡服務提供者通過合作的方式,由著作權人事先提供作品庫以代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以此為基礎事先過濾網絡用戶發布的涉嫌侵權的內容,從而有效控制網絡版權侵權泛濫。私人創制的過濾措施得以運作,仍需要以“通知-必要措施”義務為基礎,但網絡服務提供者所適用的現有過濾措施并非從責任上升為義務,而是從強制轉換為自治。但本質上,基于利益平衡的制度目的,“通知-刪除”規則已經開始走向“通知-必要措施”規則。發達國家為解決面臨的問題,通過私人創制“通知-必要措施”規則提供了“通知-刪除”規則所不具有的開放性。而在我國有明確法律規定“通知-必要措施”規則的情況下,更應當通過目的解釋,將信息披露解釋為“必要措施”之內容,實現其開放性特征的價值。
三、信息披露制度的解釋論進一步展開
(一)“通知-必要措施”規則對于“信息披露”的適用
“信息披露”作為“必要措施”之內容,“通知-必要措施”規則對信息披露的適用,亦有其正當性。但也應當意識到“通知-必要措施”規則在“信息披露”適用上存在特殊性。
首先,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著作權人“信息披露通知”,應送達網絡用戶但不得立即披露信息。根據《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從權利人處接到信息披露通知的網絡服務提供者,依據“通知一必要措施”規則應當采取必要措施并轉通知網絡用戶。針對信息披露,網絡服務提供者僅有披露或者不披露兩項選擇。是否采取必要措施應當依據規則目的確定。考慮到網絡用戶信息披露不同于刪除、斷開鏈接等措施,刪除、斷開鏈接尚有恢復之途徑,而信息一旦披露,則無恢復其匿名性的方法。若允許著作權人一經請求即可獲得網絡服務提供者對網絡用戶的信息披露,網絡用戶信息面對著作權人幾無任何保護手段。因此,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權利人通知后,不應將立即披露網絡用戶信息作為必要措施。為平衡著作權人救濟其權利之需要,則應當將通知立即送達網絡用戶作為必要措施,保障網絡用戶對其信息披露的參與權,通過網絡用戶與著作權人的交涉,確定網絡用戶信息最終是否披露。
其次,網絡用戶提交反通知,應免于提交其真實身份信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網絡用戶接到轉送的通知后,可以向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交不存在侵權行為的聲明。聲明應當包括不存在侵權行為的初步證據及網絡用戶的真實身份信息。在網絡用戶接到轉通知后同意披露的情況下,信息披露再無爭議;在網絡用戶拒絕披露的情況下,因爭議雙方對是否披露網絡用戶信息存在爭議,若根據法律規定,必須在反通知中自行披露信息,則與網絡用戶真實意思違背。若網絡用戶保持沉默,因網絡服務提供者已經采取了必要措施,其僅具有程序性中立地位,而無法對雙方爭議做出實質性判斷,應予維持既有之現狀,而無權披露網絡用戶信息,著作權人應通過司法救濟保護其權利。
最后,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反通知后,應將聲明送達著作權人,并告知其有提起訴訟或投訴的權利。《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條第二款規定,權利人逾期未提起訴訟或投訴的,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終止其采取的措施。因網絡服務提供者并未采取措施,因此無論著作權人是否逾期其均不需要終止任何措施。
(二)“通知一必要措施”規則的適用缺陷
“通知-必要措施”規則的適用并未完美解決“信息披露”的問題。在反通知未提供網絡用戶信息的情況下,接到轉通知的著作權人無法向法院提起訴訟或者投訴,著作權人的權利無法得到救濟。既然“信息披露”已經構成“必要措施”的內容,在此情況下著作權人能否起訴到法院,主張網絡服務提供者應向其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此項主張能否被支持,既關涉“通知-必要措施”規則的本質屬性問題,又涉及信息披露制度解釋論的完整性問題。
“通知-必要措施”規則本質屬性是程序性糾紛化解,并未創設著作權人與網絡服務提供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
首先,“通知-必要措施”規則是程序性的規則設定。通過設置權利人“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轉通知”——網絡用戶“反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轉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終止“必要措施”,為權利人與網絡用戶相互主張權利提供了必要的溝通渠道。通過程序溝通化解部分侵權爭議,對網絡版權侵權中最急需解決的——防止侵權內容擴大問題進行磋商。
其次,“通知-必要措施”規則僅是網絡服務提供者中立性的體現。網絡服務提供者追求在網絡版權侵權爭議中免責,其正當性在于其中立性。而程序的中立性原則,與網絡服務提供者中立性完美契合,網絡服務提供者按照法定的程序實施相應的行為,即為實現其中立性。“通知-必要措施”規則是程序性地解決問題。網絡服務提供者在這一程序的運作過程中,對是否構成侵權并不進行實質判斷,僅有程序上采取或終止“必要措施”“轉通知”的負擔。“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應當及時將該通知轉送相關網絡用戶……”這里的“應當”不能被解釋為一種真正的、可以被獨立訴請要求履行的、獨立的義務,而只是一種提示性、注意性的規定。
最后,“通知一必要措施”規則創設了獨立的權利義務內容,違反該權利義務內容即可依據過錯責任原則對網絡服務提供者進行獨立歸責的觀點,將“通知-必要措施”規則視為獨立的侵權責任類型于法無據。“通知-必要措施”規則是一種依靠當事各方互動合作,并以網絡服務提供者為中介解決爭議的路徑,該程序中的權利人和被通知侵權人都是自稱和被稱的,并未經法院裁判確定,所以爭議的解決依靠當事人是否接受,在當事人不能接受時,其功能僅止于此,只能另尋其他路徑解決爭議。“通知-必要措施”規則對網絡服務提供者歸責的著眼點在于幫助侵權。《民法典》對網絡服務提供者歸責的前提是網絡用戶構成侵權以及網絡服務提供者未采取相應措施的行為,需要被認為存在過錯,這種過錯的有無,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來加以判斷,但無論如何,不能與“未采取措施”劃上等號。而即使存在過錯,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責任仍然需要視網絡用戶是否侵權而定,而網絡用戶侵權與否,需要在“通知-必要措施”規則之外確定,因此“通知-必要措施”規則并未創設獨立的權利義務內容。
基于此,著作權人不能向法院主張,網絡服務提供者應向其履行信息披露的義務。因此信息披露制度的解釋論需要進一步展開,解決“通知-必要措施”規則遺留的問題。
(三)“通知-必要措施”規則與司法救濟的結合
“通知-必要措施”規則無法通過程序性解決信息披露問題時,司法救濟應當及時介入,以保障著作權人的權利救濟。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利用信息網絡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網絡人身權益糾紛司法解釋》)針對信息披露規定的司法救濟,并非僅適用于利用信息網絡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對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一般侵權行為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因此對網絡版權侵權爭議中的信息披露,亦可適用司法救濟。
《網絡人身權益糾紛司法解釋》第二條規定法院應當受理原告依據《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及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條起訴網絡用戶或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訴訟。但是,基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及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條,無論是人身權益權利人還是著作權人,在認為存在幫助侵權的情形,即使不存在《網絡人身權益糾紛司法解釋》第二條的規定,只要符合“有明確的被告”的起訴條件,司法機關應當予以受理。換言之,著作權人認為存在通過利用信息網絡損害其版權的幫助侵權時,依據《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及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條,即可單獨或一并起訴網絡用戶或網絡服務提供者,而無須依據《網絡人身權益糾紛司法解釋》。
《網絡人身權益糾紛司法解釋》第三條將網絡用戶信息披露納入協助調查取證義務的范疇,司法機關可以責令網絡服務提供者進行信息披露。該規定似乎是將信息披露限定在人身權益糾紛范圍內,因此有學者主張,參照該司法解釋構建信息披露制度。但是,無論是人身權益權利人還是著作權人,在無法知曉網絡用戶信息而僅起訴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情況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法院調查取證的規定,為查明案件事實情況,法院根據原告的請求及案件實際情況等綜合判斷,應當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對網絡用戶信息進行披露。即使沒有《網絡人身權益糾紛司法解釋》第三條的規定,對于網絡版權侵權案件,也應當適用《民事訴訟法》調查取證規定對案涉的網絡用戶相關信息進行調查取證。
因此《網絡人身權益糾紛司法解釋》第二條、第三條并非僅適用于人身權益糾紛的特殊規定,而是對法律適用的提示,所以應當依據《民法典》《民事訴訟法》規定對網絡版權侵權信息披露適用司法救濟。
(四)信息披露制度應以《個人信息保護法》為底線
“通知-必要措施”規則構建了完整的信息披露制度框架,《個人信息保護法》則是信息披露制度具體運作的底線。網絡用戶信息屬于個人信息的范圍,無論是著作權人收集、使用還是網絡服務提供者傳輸、提供網絡用戶信息,都屬于《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四條所規制的個人信息的處理行為,因此兩者在遵守“通知-必要措施”規則的同時,還應當遵守《個人信息保護法》,堅守對網絡用戶個人信息保護的底線。
其一,網絡服務提供者不得主動向法院披露信息。司法實踐中,網絡服務提供者多主動向法院披露網絡用戶信息。我國版權侵權糾紛多以著作權人起訴網絡服務提供者,或者起訴網絡服務提供者與網絡用戶共同承擔責任為主,網絡服務提供者為避免承擔責任,更傾向于主動披露網絡用戶信息。法院未依協助調查取證義務責令網絡服務提供者披露信息時,網絡服務提供者主動進行信息披露,違反《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個人信息處理者處理個人信息應“為履行法定職責或者法定義務所必需”的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需要披露用戶信息,需要法院綜合原告的請求及案件事實等相關情況做出判斷。法院的司法過程有助于保障網絡用戶信息在必要的情況下進行披露,可以有效保障網絡用戶的合法利益。網絡服務提供者主動披露網絡用戶信息,會導致未達到披露限度的網絡用戶信息被披露。網絡服務提供者不能以侵害網絡用戶個人信息的方式,保障其自身利益。
其二,披露的網絡用戶信息應當以能證明《民事訴訟法》所要求的“有明確的被告”為限。《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六條規定個人信息處理應做到最小影響、最小范圍。無論是著作權人收集網絡用戶信息,還是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供網絡用戶信息,其目的均是揭開網絡用戶的面紗,為著作權人提供明確的被告,為其提供司法救濟,促成網絡版權侵權糾紛的解決。因此信息披露應以實現該目的為限。《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零九條第一款規定,原告提供被告的姓名或者名稱、住所等信息具體明確,足以使被告與他人相區別的,可以認定為有明確的被告。因此網絡用戶信息披露應以能明確其身份的姓名或者名稱、住所等信息為限。
四、結論
“通知-必要措施”規則的開放性特征,為網絡版權侵權信息披露制度的解釋論展開提供了切入點。而將“信息披露”解釋為“必要措施”的內容,符合“通知-必要措施”規則限制網絡服務提供者責任,促成版權侵權爭議解決,從而實現三方利益平衡的制度目的。信息披露制度解釋論的進一步展開,首先需要注意“通知-必要措施”規則適用在“信息披露”時的特殊性。收到著作權人披露信息的通知時,網絡服務提供者轉通知即為其必要措施,而無須披露信息;網絡用戶反通知時,亦可免于提交其真實身份信息。其次,“通知-必要措施”規則的程序性糾紛化解屬性,并未設定信息披露的權利義務關系,無法基于規則本身主張司法救濟。為彌補著作權人無法獲得司法救濟的缺陷,應適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調查取證規定,承認《網絡人身權益糾紛司法解釋》針對信息披露的規定對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幫助侵權行為具有普遍的適用性。最后,信息披露制度的具體運作應以《個人信息保護法》為底線,既要限制網絡服務提供者主動向司法機關披露信息,又要在信息披露的內容上以能夠明確網絡用戶身份的姓名或者名稱、住所等信息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