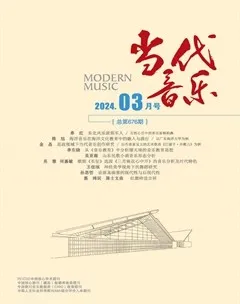中央蘇區紅色音樂口述史研究初步構想
李小兵
[摘 要] 課題對共生于中央蘇區革命實踐中的紅色音樂嘗試用口述史料與文獻、實物接通互證,通過增添紅色音樂主體的生活史、情感史和社會心靈史等活態史料以審視紅色音樂實踐的歷史過程、基本經驗和當代啟示。文章主張應站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具體歷史語境對紅色音樂實踐與中國共產黨文藝道路形成和發展、中國共產黨軍旅音樂傳統的形成、紅色音樂對蘇區精神形成的影響等話題的質性思考,從而推進紅色音樂研究朝縱深發展。
[關鍵詞] 中央蘇區;紅色音樂;紅色音樂主體;口述史
[中圖分類號] J60-02? ?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2233(2024)03-0186-03
中央蘇區主要包括贛南、閩西、粵北,其中瑞金是當時蘇維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因而贛南也就成為根據地的中心。紅色音樂是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蘇區革命戰爭為題材創作或以國外作品改編、對革命起推動作用、為民眾喜愛和傳唱的音樂作品及其發展形態。課題用口述史方法對紅色音樂主體作歷時訪談,盡可能再現、還原紅色音樂的演唱技藝和文化記憶,感受紅色音樂主體的生命史和紅色音樂情感史及價值認同,體悟紅色音樂在當下的溫度,推研紅色音樂與蘇區道路、蘇區經驗和蘇區精神的關系問題。
一、課題研究的現狀及其意義
學界對本課題的相關研究主要涉及蘇區紅色音樂研究、音樂口述史研究以及紅色音樂文化理論和實踐等方面。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在音樂學術得以極大發展的近30年中,紅色音樂卻因‘告別革命和‘重寫音樂史,而被學術界‘邊緣化了。”[1]
中央蘇區紅色音樂的學術研究相對滯后,目前總體呈零星狀,多為內部印刷的資料性匯編,公開出版的學術性著述偏少,系統研究的專題性成果不多。
劉云的《中央蘇區文化藝術史》[2]中的中央蘇區音樂史內容由負責人單獨出版[3],主要對蘇區音樂作品的題材和體裁特征、歌詞特點、曲式、曲調來源和創作手法進行了論述。《蘇區文藝運動資料》[4]編委會從1959年始對長征前后蘇區文藝進行了全面收集,但部分信息因受受訪者的記憶影響存在不確定性。凌紹生(1998)、李詩原(2020)、徐元勇(2021)先后涉及紅色音樂研究與政治的關系以及紅色音樂的傳播、版本、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等問題。2018、2019先后在上海音樂學院、井岡山大學連續舉辦的兩屆全國紅色音樂文化論壇成果豐碩,并在上海音樂學院成立了中國紅色音樂文化研究與發展中心、紅色音樂文化育人聯盟。
近30年《解放軍音樂史》①《中國共產黨延安時期音樂文化建設及其歷史貢獻研究》②《中國紅色音樂文化傳播研究》③《中國共產黨革命音樂百年發展史研究》④等項目的開展對本課題具有直接推動和催化作用。《中央蘇區紅色歌曲集》《紅色歌謠集》《抗日戰爭歌曲選集》等層出不窮的出版物也是推動紅色音樂研究前行的重要學術資源。國內音樂口述史研究興起于2000年后,2014年以來連續四屆中國音樂口述史研討會掀起了該研究的學術熱潮,成果聚焦于理論和個案研究,臧藝兵、梁茂春、謝嘉幸等均有著述論及。
紅色音樂經歷高潮、低谷、反思、重拾的歷史過程。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知識界反思運動思潮興起,革命意識形態話語權威開始受到廣泛質疑和解構。傳統現代文學史所構建的革命文藝神話開始被瓦解,“重寫音樂史”一時蔚為熱潮,多元的思想文化、多元的思潮都想尋求合理存在。紅色音樂面臨新的闡釋和注解需要,紅色音樂基因傳承的源動力、新路徑和新潛力值得學術化探索。顯然,用傳統話語解釋紅色音樂已有局限,研究蘇區紅色音樂需要更新和更多的學科理論和方法。
已有成果對蘇區紅色音樂做了一定梳理,個案研究逐漸深入;口述史方法逐漸運用到音樂學領域,開始涉及紅色音樂,并取得一定成果和經驗;學界對蘇區紅色音樂資源的教育價值、傳承和認同等關注較多。既有成果為本課題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方法借鑒,基于上述文獻梳理看,已有研究均為史料之內求歷史,忽略了對紅色音樂主體的社會生活史和心靈史等活態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研究具有存音存史的史料意義,課題組將源頭性搶救和保存口述實錄、影像圖像、聲像網絡等活態史料;項目也具有推進紅色音樂研究的學術意義,通過集多學科理論,進行口述史料與文獻、實物史料互證研究,為豐富中國特色的紅色音樂文化研究作出貢獻;同時還有資政育人的現實意義,通過挖掘紅色音樂主體的創演技藝、經驗和文化記憶,提升人人講好中國紅色音樂故事和傳承紅色音樂基因的能力,能進一步凝聚文化認同,增強文化自信。
二、內容框架、方法及思路
課題將對蘇區紅色音樂主體進行傳唱史、社會生活史和個人心靈史方面的口述訪談及資料整理分析,借此理清百年紅色音樂功能形態和創演變遷的內在邏輯與外部影響。主要內容和方法如下。
(一)紅色音樂主體信息的實證爬梳
蘇區的開辟距今已近百年,大部分紅色音樂主體年事已高或相繼謝世,健在的紅色音樂親歷者屬于稀缺人群,而且一部分已隨子女分散在全國各地居住,對該群體的尋找首要必須依托全國各地退伍軍人事務局、課題組成員所在單位和校友會、其他做過相關研究的學者提供部分信息;然后是深入當地文化部門獲取紅色音樂主體的基本信息,以便課題組統計紅色音樂主體的基本信息和去向,從而推進研究進程。
(二)在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中把握蘇區紅色音樂
中央蘇區作為蘇維埃富有起點意義的革命陣地,它在整個中國革命歷史過程中具有重要的經驗借鑒價值,對完整的中國革命具有根本性啟示。蘇區紅色音樂創作理念和特色、創作隊伍構成、文藝體制的建設以及報刊、標語、表演、演講、社團和學校等宣傳媒體的運用模式及實踐功效是具有開天辟地性質的蘇區文藝宣傳經驗。在蘇區特殊的生態環境和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領導蘇區革命如火如荼、節節勝利,彰顯了革命先輩的革命熱情和奪取政權的偉大決心。因此,對共生于百年黨史中的革命及其紅色音樂的同步考察具有全局意義。
(三)充分運用口述訪談挖掘活態史料
課題通過對贛南、閩西、粵北蘇區30位左右的紅色音樂主體樣本進行口述訪談,探索蘇區文藝體制構建、音樂團體和組織建設,以期對蘇區音樂文化與發展的體制基礎、音樂主體對紅色音樂文化的價值認同、情懷和心理感悟作全面考察;用訪談法考察蘇區在專業人才緊缺情況下創作隊伍的特殊構成方式、創作特色、作品類型、作品風格及音樂形態;悉心進行對紅色音樂主體文藝活動的口述考察,揭示蘇區是如何憑借學校教育、社團學習、音樂表演和演講、報刊標語達到為革命鼓舞士氣、瓦解敵軍、擴大紅軍、爭取勝利等目的,剖析蘇區道路、蘇區經驗、蘇區精神形成的內在邏輯。
(四)悉心收集、分析、用好現有文獻和成果資料
對現有紅色音樂文獻的收集、分析和利用,不能把眼光局限于音樂領域,而應投射到蘇區的大歷史視野和其他交叉學科文獻之中去尋找靈感。中國革命從“學俄”到逐漸“脫俄”的歷史過程中也是中國文藝宣傳的蛻變過程,缺失這種視角,我們將不能把握蘇區文藝宣傳的本質。不了解一戰后世界陣營的對立形勢,將無法真正把握蘇區革命在道路選擇上的艱難過程。
(五)注重歷史文獻、實物資料與活態多重證據接通
江西當地學者利用地緣優勢產出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對這些成果的把握和解讀是研究蘇區紅色音樂的重要環節,其中涉及的方法、視域和詳實資料是研究紅色音樂的重要基礎。紅色音樂的歷史語境與當下有一定距離,在特殊歷史時期,紅色音樂親歷者面對三座大山壓迫、面臨妻離子散、慘絕人寰的圍剿殺戮的經歷和命運遭際,他們是如何面對的?這些生活史和心靈史的面對面訴說彌足珍貴。他們對革命流血犧牲的態度、對紅色政權的期盼、認同也都彰顯在文藝宣傳的吶喊聲中,對其伴生物——紅色音樂的多重證據接通考證很有必要。
三、擬解決的三個核心問題
課題用口述資料與史料接通互參,指出蘇區紅色音樂不僅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促進了蘇區道路、蘇區經驗和蘇區精神的形成,在當下仍有精神教化和凝聚認同的跨時空意義。蘇區紅色音樂涉及內容繁雜、人員眾多,本課題重點對以下三個重要事件和主題進行探索。
(一)紅色音樂實踐與中國共產黨文藝道路形成和發展的關系探索
蘇區革命與紅色音樂相伴相生,共產黨人在革命實踐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文藝經驗,可以說蘇區革命既是紅色音樂實踐的過程,也是中國共產黨文藝道路的探索歷程,它先后經歷仿造、改造、創造的路徑。由于人手和專業水平局限,蘇區文藝工作者往往呈兼職形態,全民參與。紅軍戰士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文化的傳、幫、帶普及工作在部隊中是重要任務,識字的士兵經常在戰爭之余讀文件、唱紅歌給大家聽,這是最直接有效的宣傳教育手段。蘇區通過對工農兵文化宣傳普及,推進了工農兵隊伍的階級意志認同和精神補給,充實了紅軍主體戰斗力,使中國紅軍逐步朝有文化的現代化軍隊邁進。
蘇區繼承了三灣改編后連隊組建娛樂科的優良傳統,在《古田決議》中又創造性地提出軍隊文藝宣傳的體制建設。革命者在貼近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教育群眾的實踐中體悟深刻,廣泛設立俱樂部、列寧室和工農劇社,部隊鼓勵大家編創體現各種群眾情緒的革命歌謠,旨在讓文藝走向大眾化和準專業化的道路。蘇區文藝宣傳經驗是部隊戰斗力的催化劑,推進革命走向勝利。
蘇區開辟以來,作為外部資源的俄蘇文藝的引入熱潮壓倒了五四以來的西學傾向,影響長達50年。中國文藝道路先后經歷向西方乞靈、革命文藝、救亡文藝、抗戰文藝、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歷程,其中的成敗得失經驗必須及時作出總結。蘇區主張文藝與政治的緊密結合,宣傳工作在紅色音樂的相伴中有序開展,“拿槍”和“拿筆”的軍隊同等重視,文藝從啟蒙功效發展到當下的審美形態,符合中國特有國情。時至今日,中國共產黨人明確提出新時代文藝一定要搞清楚為什么人的問題,這些做法都是對蘇區文藝的繼承和發揚。諸多做法和成效證明蘇區音樂實踐對中國共產黨文藝道路形成和與發展提供了重要經驗和啟示,它具有起點意義、固本價值和鑄魂功效。
(二)紅色音樂實踐與中國共產黨軍旅音樂傳統形成的關系探討
軍旅音樂特指伴隨著軍隊而存在的音樂,不管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它都被需要,雖然發揮功能方式和渠道不一,但充分體現音樂與軍隊、音樂與政治相須為用特征。“一切為了打贏”是音樂為革命服務的終極目標。革命和音樂的結合與音樂之“聲音”在鼓舞戰士精神和感染戰士情緒方面的實用性優勢分不開。在相須為用中,音樂體現其實用性、功能性、教育性和審美性。
舊中國社會中農民受難最重,領導者對廣大民眾作用力的認知分析是關鍵,革命者通過文藝宣傳喚醒、發動群眾成為中心命題。軍隊及其文藝建設擺在首要位置,早在黃埔軍校時期就成立了雪花劇社,這可說是現代革命軍隊文藝發展的濫觴。支部建在連上、設立軍隊娛樂科成為中國建軍史上的重要創舉,也是我軍文藝的真正起點。類似做法在后續《古田決議》中被制度化,關于文藝宣傳的地位、作用、活動方式、領導關系、經費來源等都作出了明確闡述和規定。系列優秀的軍旅音樂理念對后來的文藝發展具有重要啟發和借鑒功用,紅色音樂與中國革命共生一體,可以說,中國人民的革命史也是一部形象生動的軍旅音樂史。
(三)紅色音樂實踐對蘇區精神形成的影響
蘇區革命必須依靠文藝宣傳工作,文藝宣傳就地選擇了紅色音樂這一神奇的“聲音”,蘇區紅色音樂與革命合為一體,使政治意識形態工作巧妙地實現藝術化,這是一種革命的實事求是。在革命實踐中,隨著蘇區文藝體制建設的完善,民間歌謠、客家山歌等本土民間音樂資源逐漸被革命體制化,成為革命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并產生巨大的革命宣傳能量。紅色音樂實踐作為蘇區革命有力的文化宣傳武器,在文藝的急需和政策的嚴格規定下,文藝工作者與部隊指戰員有機融為一體,憑借集體智慧促進宣傳工作如火如荼進行,并在組織群眾、發動群眾、教育群眾的過程中彰顯了革命集體密切聯系群眾的工作路線和作風。
蘇區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在革命戰爭年代的積淀和凝練,是具有原創意義的現代民族精神。蘇區精神是在真刀真槍的革命實踐中孕育和煉就的,也是對客家族群精神的進一步提升。毛澤東等革命集體當時對中國形勢的透徹分析,抓住了中國革命的系列核心問題——農民和土地,最終決定“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探索,具有開先河意義,體現了蘇區革命一心為民、爭創一流的信念。自始至終,具有開放、包容性的紅色音樂被植入蘇區革命的所有環節和事件中,因地制宜、形式多樣地發揮了它的超凡作用力。可以說,蘇區精神是在紅色音樂實踐的“號角”縈繞聲中形成的,深入人心、影響延綿。音樂主體通過“蘇維埃文化本土化、政治意識形態藝術化、民間文化資源體制化、審美文化形態大眾化”[5]途徑完成紅色音樂實踐,也形成了蘇區精神。
參考文獻:
[1] 李詩原.紅色音樂研究的學科理論和問題框架[J].音樂研究,2020(02):86.
[2] 劉云.中央蘇區文化藝術史[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8.
[3] 胡建軍,鄧偉民,傅利民.江西蘇區音樂文化研究[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7.
[4] 汪木蘭,鄧家琪.蘇區文藝運動資料[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
[5] 周平遠.從蘇區文藝到延安文藝——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歷史進程[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49.
(責任編輯:劉露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