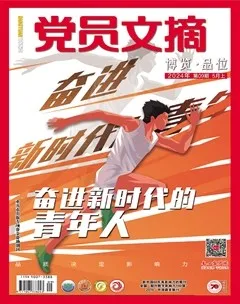兒時沙海,如今花香撲面

暮春時節,是新一代治沙人郭璽最忙碌的時候:管理養雞場、給樹苗澆水、壓沙、種樹……每一天,郭璽的日程都排得滿滿的。清晨他驅車前往甘肅省武威市古浪縣八步沙養雞場給“溜達雞”喂食,接著去蓄水池拉水、前往林場澆水,下午又轉戰到古浪縣與內蒙古自治區交界的治沙現場……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結束工作回到家中,太陽已西沉。
想起兒時,郭璽回憶說,時時與黃沙為伴,吃飯嘴里都是沙,沒有不落沙子的地方。40多年來,八步沙三代人累計完成治沙造林30多萬畝,管護封沙育林草40多萬畝,栽植各類沙生植物3000多萬株。
春暖花開,站在曾經的沙海里,微風拂來芳草清新。“我常暢想著未來,荒漠到處都開著五顏六色的花,花香撲鼻而來,沙海也會變成花海。”郭璽說。
接過爺爺的鐵鍬
1981年,隨著國家“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的啟動和實施,年過半百的古浪縣土門鎮農民郭朝明、石滿、賀發林、張潤元、程海、羅元奎六老漢,不甘心家園被沙漠吞噬,聯戶承包了八步沙,要與沙漠寸土必爭。
一頭毛驢、一輛架子車、一個大水桶和幾把鐵锨,他們開始了治沙造林。為了趕進度,全家老少齊上陣;為了省時間,索性卷起鋪蓋住進沙窩里;沒有房子住,就在沙地上挖個壕溝,用柴草搭上個地窩鋪住……
所有人都忘不了,郭璽出生的1985年,那是治沙的第四年,春天雨水格外多,六老漢種下的樹苗成活了一大半。望著一棵棵親手栽種的花棒、梭梭長出了芽,六老漢高興地笑了。
這一年,六老漢跟土門鄉政府(今土門鎮)簽訂了一份《固沙造林承包合同書》,組建集體林場,承包治理7.5萬畝流沙。
“吃下定心丸,我們更有信心了。”張潤元說。如今,他是六老漢中仍然在世的。
“當時我們就商議,不能前功盡棄,誰老了,病了,干不動了,就讓兒子來干,兒子干不動了,還有孫子,八步沙每家每代都要有人繼續治沙。”張潤元說。
接過這個重擔,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
1982年,郭朝明因病進不了沙漠,讓兒子郭萬剛來接替。郭萬剛當時在土門鄉供銷社上班,一個月工資60多塊錢,比老師還高20塊。
“父親指著林子說,你不來看樹,這樹不就白種了?”郭萬剛被迫辭去公職,帶著情緒進了沙漠,沒想到一干就是38年,成為現在的八步沙林場場長。
郭璽還記得,1995年除夕夜,大伯郭萬剛在林場場部值班,郭璽和哥哥帶著飯菜去跟大伯做伴。
剛到場部,就趕上“老毛黃風”,風沙打在門窗上咔嚓作響,“老毛黃風,就是沙塵暴,白天都黑壓壓的,沙子打在臉上生疼”。
郭璽問大伯,這么大的沙漠,啥時候才能治住。大伯答,我們治不住,還有你們呢。
接力棒要交到第三代手中,難度更大了。
郭璽記得,爺爺在2005年去世那一天還一直拉著他的手不放,“我明白爺爺的意思,他也想讓我治沙種樹”。
大伯勸侄子郭璽,勸了兩年,“你爺爺是第一代人,我是第二代帶頭人,你不帶個好頭,你爺爺種的樹不白種了?”

2016年冬天,大伯郭萬剛又來勸回家幫忙的郭璽留下來,“治沙就像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如果我們停下來,風沙又會卷土重來,兩代人的努力就會白費。大伯老了,干不動了,治沙還得交給你們年輕人,一代接著一代干。”看到大伯老了,郭璽也在糾結到底要不要踐行祖輩們的約定留下來。外面的世界對年輕人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我心里十分糾結和郁悶,同齡的朋友們都嘲笑我一個年輕人待在沙漠里能有啥出息。”2017年5月,幫著林場度過一年中最繁忙的時刻后,幾經思想斗爭的郭璽還是打算到外面繼續打工。臨走前,郭璽想著再看看這些樹,便獨自來到眼窩子沙,這是林場最高的地方。目光所及,開滿了黃色的檸條花。震撼之余,郭璽心里酸酸的,兒時的記憶和長輩的期望在那一刻涌上心頭。“如果不治沙,就沒有這片花海,這是件很偉大的事。”祖輩們通過努力換來的這片檸條花海,讓郭璽下定決心留下來,成為八步沙的第三代治沙人。
繼承遺志治沙精神得接續
進入林場工作后,郭璽跟著大伯、叔輩們從零學起——怎么在沙地種樹,怎么看護苗木,怎么巡護林場。林場最遠的距離有20多公里,郭璽至少每個月就要走一遍。風天一身沙,雨天一身泥,一年四季,晨出暮歸。
這時的郭璽才真正知道,在沙漠里種樹種草,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兒。“在八步沙打草方格、種苗全部靠人工,我們每天天亮就要起來,一直勞作到太陽落山。”郭璽說,“治沙車機械化作業要在平緩的地方,而這里的沙丘一個接一個,是高低起伏的,沒有辦法進行機械化作業。”
沙漠里最缺的就是水。種下去的樹后期還要多操心,即使這樣,有的樹不是被大風拔起,就是不下雨被旱死。郭璽說,直到自己接手,才明白老一輩人是用一生在種樹。“栽下了樹,還要一遍遍澆水,可澆了也不一定成活,付出看不到回報,讓人心灰意冷。”
2019年,天氣比較干旱,年降雨不到100mm,種下去的3萬畝樹的成活率不到10%。“看到那么多樹被曬死,心里特別不好受,我只能自己氣自己,怪自己的工作沒做到位。”郭璽說。
“終于明白老一輩種樹的艱辛,他們也都這么過來了。”沒有成活的樹,來年就要重新補種。郭璽明白了,只有具備不畏艱難困阻、堅持不懈的“愚公”精神,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治沙人。
“綠色的銀行”
“堅持總會有回報。”這是郭璽常用來鼓勵自己的一句話,也是他的人生信條。
如今的八步沙,梭梭、檸條等沙生植物構建的“緩沖帶”,將古浪縣與騰格里沙漠相隔,保護著周邊3個鄉鎮近10萬畝農田,實現了由“沙進人退”到“人進沙退”的歷史性轉變。
“爺爺、大伯他們用一輩子自己開了個銀行,是‘綠色的銀行。”郭璽說,古浪縣先后從南部山區移民6萬多人至沙漠邊緣,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這就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最樸實的寫照。”
現在,郭璽還不斷在琢磨壓沙造林的新方法,嘗試采用“細水滴灌、地膜覆蓋”等技術,提高植樹種草的成活率。同時,他還盤算著向沙漠要效益——在林場養殖“溜達雞”、在梭梭樹下嫁接肉蓯蓉,用實際行動爭取治沙與致富雙贏。
一天,郭璽無意間看到女兒作文中的自己,眼角微微泛紅。
“他們黑了,八步沙綠了。古銅色的皮膚、粗糙結繭的手掌,脾氣倔、韌勁足,這是爸爸給我的第一印象。他從小生長在沙漠中,如同‘大漠胡楊,活得分外堅強。但我更想叫他‘沙漠愚公,一代接著一代繼續治沙守綠,建起了一道堅不可摧的綠色長城。”在《我的爸爸》作文中,郭璽大女兒這樣描寫自己的父親。
這讓郭璽更加堅信自己的選擇是對的。“相信不久的將來,騰格里沙漠一定會在新一代青年人手里徹底改變模樣”。
(摘自《中國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