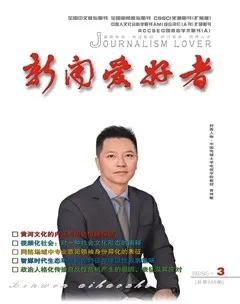華人文字傳播的時間介質研究
付曜輝 王晉
【摘要】文字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唯有詞語才讓一物作為它所是的物顯現出來。古文字的意義在于它們的“歷史性”“時間性”。隨著華人向外擴散,華人所使用的中國古文字在世界范圍內傳播開來,華人走遍了全球,華語也擴散到了全球。研究華人文字文化傳播的時間介質,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如何籌劃未來。“返回”才讓我們前行。向前的道路同時就是返回的道路,返回到人類的本己性使命,聽從語言文字的呼喚,努力掙脫現實功利的糾纏。
【關鍵詞】華人文字;文化傳播;時間介質;源始時間性
傳播以符號為基本介質,文字語言符號是傳播的最基本介質,而語言文字符號傳播的最基本介質是時間。時間是文明傳播的重要維度,這一維度對于華人文字文化傳播體現尤為明顯。本文研究的不是華人語言表達時間的詞語和手段、語言中的時間性,或者是華人對時間的感知,而是從時間性視域來解釋文字符號的發生、對外傳播以及未來籌劃,這便是從文字的深層次存在來理解文字符號。本文采用的時間性概念,不是自然時間或者流俗時間,而是海德格爾發展出的“源始的時間領會”,源始的本真時間被看成是將時間的曾在、當前和將來融為一體的“時間性”。
作為世界上唯一流傳下來的非拼音文字,華人文字傳沿最為久遠。許多古代文字,比如蘇美爾和古埃及文字,早已消亡了兩千多年。造成中華文化核心的是華人文字,而且它已成為中國精神文明的旗幟。[1]受到“重語(言)輕文(字)”的影響,對漢字文化傳播研究較少,研究華人文字傳播更少,大多集中在利用新媒體傳播漢字文化的途徑、某一時間漢字文化(例如唐代漢字文化)的傳播研究,或者是漢字文化蘊含的哲學觀念和文化底蘊,但是少有研究以中國古文字為研究對象,從漢字本體時間性和華人文字文化傳播的源始時間性角度出發,研究漢字對內傳播和包括漢字在內的華人文字的對外傳播的時間性介質。本文首先探索漢字文化本體以及對內流傳與傳播所蘊含的時間性建構,然后分析中華古文字隨種族擴散而對外傳播的時間性,以及反思籌劃華人文字的未來走向。
一、漢字符號與時間性的本體關系
(一)漢字的起源
文字的發生發展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從刻畫符號、圖畫文字,過渡到逐漸發展為成熟、表音的文字體系,成為現代人心目中的基本筆畫,滿足現代人對文字的要求;從繁到簡,從流動到固定,這是個漫長的發展過程。漢字在各個不同文化時代,無論是地位、作用,還是涉及的人群、使用范圍都是有所不同的。文字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唯有詞語才讓一物作為它所是的物顯現出來,半坡陶片上的刻畫符號具有指事符號的性質。“《說文》把‘指事放在六書之首,可能有暗示文字起源的意思。”[2]《周易·系辭》:“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而百官以治,民以察。”《尚書》偽孔傳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古書上的說法也印證了漢字由結繩而刻契而文字的模式正是華夏文字產生的最具理據性的方式。20世紀80年代中期,河南舞陽賈湖裴李崗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甲骨文等物品,距今為7800年到9000年。賈湖遺址出土了二十多個刻符,有些字竟與殷墟商甲骨文一模一樣。這些符號已經具備了原始文字的特征,是原始文字的初創形態。
古漢字以歷史、時間的形態存在著,它們保存、展示著歷史。雖然古漢字應用的時代已經結束,但是作為“歷史”和“時間”因而有了其意義。從這個意義來看,古漢字的意義在于它們的“歷史性”“時間性”。古文字向人類“訴說”它的歷史,人類通過古文字面對過去,與古人交流和溝通,融會古今世界,延續對世界的認知。語言文字是人類與“存在”的對話,這對話“不是工具性的,而是存在性的,是時間、歷史——‘存在得以‘存留的方式,亦即時間、歷史的存在形式”。[3]
(二)漢字書寫形式的發展變化
漢字的流傳與傳播,與漢字書法有很大關系。漢字書法具有獨特的形體特征,作為藝術品所蘊含不同時代和個人的時間性。就書法而言,一個時代,一種書體,一個書家,一個字,都以不同的風格表現出不同的藝術傾向。[4]書法并不只是技巧,而是一個時代美學的集中體現,然而漢字的基本功能在于傳播與溝通,“實用在先,審美在后”[5],最初實用在先,后來發展審美和表現生命調性為重。
秦朝結束東周列國戰亂,一統天下,建立了一種務實、統一的全新書風——隸書。隸書被認為是地位低卑的“徒隸”之人,因為要處理太多的簡牘文件,因此發展出來的方便字體。雖然沒有正體篆書莊重,但是久而久之,方便簡單的字體在社會上流通起來,逐漸取代了舊的字體。三國魏晉是竹簡書寫過渡為紙帛書寫的重要年代,毛筆在“紙”“帛”一類纖細材質上的書寫,增加了線條“行走”“流動”“速度”的表現,漢字在晉代文人手中流動飛揚,瀟灑飄逸,創造了漢字嶄新的行草美學。行草書風發展出獨特美學,甚至超越文字原本傳達信息的功能,使得書法達到與繪畫、音樂和舞蹈同等的審美意義。唐代的張旭、懷素被稱為“顛”張“狂”素。他們通過狂草的書寫形式,表現自己對生命的感悟,體現了大唐美學的時代風格。宋代的書法美學,例如蘇軾的《寒食帖》追求平淡天真,向往個人自我的完成與個性的表現,不再斤斤計較法度結構,而是更強調個人心境的自然流露。
流傳下來的漢字書法作品,作為藝術品保存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中,成為珍貴的文化遺產,以歷史和時間的形態存在著。創作這些作品的人已經成為古人,這些作品所在的時代已然過去。但今人走進博物館,面對這些展現自身歷史和時間的藝術作品,思“前”想“后”,從當下現時世界脫離出來,以眷戀和崇敬的心情體會古人的心境和風格,體會漢字和人生命的力量美學和生生不息,從而讓人由對文字的時間性思考,過渡到對自身有限性的時間性思考。古文字向我們“訴說”它的歷史,我們人類通過古文字,與古人交流和溝通,融會古今世界,延續對世界的認知。
二、華人文字對外傳播的時間性
從遠古以來,不同地區的部族和人民,即有頻繁的接觸。人憑借符號交流,有了語言符號之后,主要的交流方式就是語言文字符號,所以語言文字符號是理解各種文化的鑰匙。華人文字是世界文字大家庭中的成員,這個成員與其他成員在歷史上有何關系呢?華人文字的傳播,不僅限于日本、越南等亞洲周邊國家,更是隨著華人向外擴散而在世界范圍內傳播開來。
著名學者、古文字學家劉志一教授認為,中國古文明是以農耕文明為重心的復合型文明,早在距今一萬年前即已形成。西亞古文明與埃及古文明、印度河谷文明、瑪雅古文明等崛起,實質上是中國古文明外傳后激發的產物。[6]他用古彝文與西方古文字進行對比研究,釋讀出了許多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印度河谷山上的古文字,距今三四千年前的邁錫尼古文,距今四千多年前意大利梵爾卡·史莫尼卡崖畫刻符,距今三千多年的希臘克里特島出土的古文字。西方學者一致認為,現今西方的字母文字,來源于西亞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據劉志一考證,蘇美爾人實際上是一萬年前大洪水時遷入西亞的中國人(古夷人),他們將古夷文字帶到西亞兩河流域,發展成楔形文字和線形文字。由此可見,古夷(彝)文可能與西方文字存在著淵源關系。中國社科院馮時先生認為,不論山東龍山文化,還是所謂的東夷文化,都有早期的夷族文字。[7]李喬先生提出“半坡陶文是古彝文的始祖”這一重要學術觀點。他通過半坡刻畫符號(陶文)與彝族文字的對比研究,論證了半坡刻畫符號與彝族文字一脈相承的親緣關系。[8]西南的彝族學者能釋讀這些文字,是因為古夷人創制的古文字隨著古夷人的遷徙而帶到了亞洲乃至世界各地,如山東的骨刻文字、西亞的楔形文字等。
劉堯漢提出彝族萬物雌雄觀的原始傳統是中國萬物陰陽觀的一部分。[9]彝族十月太陽歷,單月(1-3-5-7-9)為雄,雙月(2-4-6-8-10)為雌,一年分為五季,每季包括雌雄兩個月。老子是楚人,他的“萬物負陰而抱陽”的陰陽思想可能受原始巫術的古道教影響。陰陽兩元,代表一切事物的最基本對立關系。這個二元論是萬物運動變化的本源,自然界的客觀規律,也是人類認識事物的基本法則。陰陽的概念源自古代中國人民的自然觀,古人觀察到自然界中各種對立又相聯的大自然現象,如天地、日月、晝夜、寒暑、男女、上下等,便以哲學的思想方式歸納出“陰陽”這一概念。中華文化中的陰陽觀,在印歐語系中也有體現,這就為中華文化傳播提供了佐證。印歐語系中有些語言的名詞、代詞、形容詞、冠詞的詞形,分陽性masculine、陰性feminine、中性neuter。法語有兩個性,即陰性和陽性。如陽性le livre書,陰性la table桌子。德語有三個性,如陽性der Tisch桌子,陰性die Hand手,中性das Madchen女孩。英語名詞無性,代詞有性區別,如he, she,it等。后綴區別,如actor,actress。
三、華人文字現代發展的時間整體性
海德格爾認為當時間來到現代,就來到了科學技術擴張的時代,也是精神貧困的時代,人性和神性暗淡。在這個詞語荒誕的科學時代,人類精神淪落已經進行得如此之遠,已處于失去其最后精神力量的危險中。[10]科學文化時代起始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這期間漢字經歷了深刻的危機,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嚴重考驗,值得反思。人類比以往更迫切地要追求更高更深和更遠的東西,如何讓人類更偉大而不是相反?海德格爾給出的答案是,返回到人類的本己性使命,聽從語言文字的呼喚,努力掙脫現實功利的糾纏。華人文明對世界作出了巨大貢獻,如何使歷史最悠久的文字煥發出更旺盛的生命力,也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
在對亞里士多德“線性時間”批判的基礎上,海德格爾發展出與前者相對立的“源始的時間領會”。源始時間被看成是將時間的三維(將來、曾在和當前)融為一體的“時間性”。海德格爾對人(此在)的時間性的認識,可以拿來理解漢字的時間性。在此在的生存中,此在本己的是它所曾是,并作為它的所曾是而存在,“此在總是它的過去”,而此在的過去,并不是跟在此在身后,而是總已走到它的前頭。只有當此在如“我是所曾在”那樣存在,此在才能以回來的方式從將來來到自己本身。[11]走向將來,也就是走向最本己的曾在,而當前是有決心走向最本己自己的當前,從而達到將來、當前與過去的整體統一。文字也當如此,走向將來,也就是走向最本己的曾在。人類對于文字的認識亦是如此。在認識到人類和語言沉淪的境況后,為了能得到救贖,人類要走一條返回的道路。對華人來講,探尋華人文字文化傳播和文字文化所代表的精神,在于溫習華人文字的歷史曾在,而意在華人文字和中華民族的當前和未來。人類要返回到原初最充盈的存在狀態,回到自我的精神家園,中國人的精神家園就是華語和華人文字,這是中國文化的命根子。
返回華人文字的精神家園,同時也要返回自身學習華人文字的原點。蔣勛先生說,漢字發展,要回到原點,像初學漢字的兒童,慎重寫下自己的名字,笨拙、緊張,但認真、慎重,一筆一畫,橫平豎直。余光中先生深刻理解漢字文化所蘊含的民族精神,他充滿感情地說:“無論赤縣也好神州也好中國也好,變來變去,只要倉頡的靈感不滅美麗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當必然長在。因為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漢族的心靈,祖先的回憶和希望便有了寄托。”[12]返回自身,理解自身的文化,才能真正自信自強。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心,也是漢字和其他華人文字命運的轉機。
四、結語
只有從時間性著手,才能從現象上通達漢字和中國古文字的本真整體性,也才能通達中華文化傳播的本質所在。只有在時間、歷史的連續性中,我們才能體驗文字的真正意義。語言文字與人的存在跟著時間性一起被遮蔽,也跟著時間性一起被解蔽。人類和華人文字的“時間性”啟示我們,“返回”才讓我們前行,向前的道路同時就是“返回”的道路,回到自我的精神家園,回到中華文字的精神家園,回到中華文明的歷史曾在。做華人語言文字文化的守護者,華人才能找到生命和力量的源泉,自信的華人,才能更好地對世界傳播中華文明。
[基金項目: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此在與語言的時間性同構研究”(2022SJYB1002)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饒宗頤.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174.
[2]周有光.比較文字學初探[M].北京:語文出版社,1998:9.
[3]葉秀山.論時間引入形而上學之意義[J].哲學研究,1998(1):28-37.
[4]何九盈.漢字文化學[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6:75.
[5]蔣勛.漢字書法之美[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108,272.
[6]劉志一.中華人類文明的獨立起源和對外傳播[J].衡陽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1):37-42.
[7]馮時.龍山時代陶文與古夷文[N].光明日報,1993-06-06.
[8]李喬.一個千古難解之謎:半坡刻畫符號與彝文淵源關系試析[J].貴州民族研究,1990(4):41-49.
[9]劉堯漢.中國文明源頭新探:道家與彝族虎宇宙觀[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10]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導論[M].王慶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45.
[11]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29,371.
[12]余光中.余光中散文精選集[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77.
作者簡介:付曜輝,無錫太湖學院副教授(無錫 214064);王晉,無錫太湖學院副教授(無錫 214064)。
編校:張如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