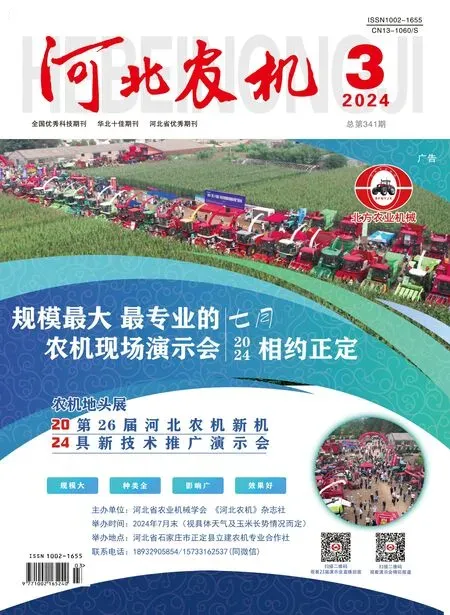共同富裕視角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區域差異研究
重慶三峽學院財經學院 計欣
前言
2016 年《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首次提出要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1]。2017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賦㈣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特別法人”地位。 2022 年國務院印發《鄉村振興責任制實施辦法》強調要“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2023 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提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是引領農民共富的關鍵方式。 農村集體經濟是強調集體所屬的全部資源稟賦歸集體成員所有, 集體成員可利用各類資源要素進行經營活動, 從經濟層面反⒊了農村集體所有制的集體經濟形式。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實現村集體發展的組織載體, 是一種可以利用集體資源資產要素開展各種經濟活動的組織機構[2]。所謂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新在更開放的經營模式、更規范的產權歸屬、更合理的分配制度和更有序的治理架構。 從政策層面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全黨全國重點關注“三農”領域問題的關鍵環節,從經濟層面來說,它對推動農業農村發展,促進農民共同富裕, 助力實現鄉村振興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因此在振興鄉村,發展現代化農業過程中,如何激發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活力促進共同富裕是破題的關鍵[1]。
1 文獻回顧
學術界最早在20 世紀90 年代展開對農村集體經濟的研究, 并提出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滯后會制約農村經濟的全方位發展。21 世紀初,在市場化發展的自然趨勢下,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成為發展現代化農業的基礎[1-3]。近年來,學術界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研究主要從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機制路徑、 困境及對策和產權制度改革等方面展開。首先,有學者從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與障礙及路徑選擇展開研究,思考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局限性問題并分析其成因和對策[4-6]。其次,部分學者重點關注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影響, 認為其作用機理與村集體經濟基礎、治理能力、資源稟賦等密切相關[7]。最后, 一些學者研究表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對于農民和農村共富有賦能效果, 在促進共同富裕發展進程中主要起載體和橋梁作用,對于增加農民收入、提供公共品、提高治理水平等具有重要意義。 綜上所述,本文將基于《中國農村政策與改革統計年報2021》統計數據,探索不同區域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狀況, 分析其與共同富裕之間的邏輯關聯, 同時以此為基礎提出相關建議,力求為促進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均衡發展,助力實現共同富裕提供新視角[2]。
2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情況區域差異分析
2.1 各區域農村基本情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施先富帶動后富發展戰略,在1986-1990 的“七五”計劃中提出,根據地理位置和經濟發達程度劃分出三大經濟帶, 本文以下所有數據分析均以三大經濟帶劃分即東部沿海地帶、中部地帶、西部地帶為基礎,對其農村人口情況、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情況、 土地流轉情況和產權制度改革情況進行研究分析。
從各區域農村基本情況可以看出,東部地帶鄉鎮、村落數與農戶、人口數均位居前列,總體來說東部與中部地帶間差異不大, 但最末的西部地帶的村民數量與農戶數量與東部地帶的差異接近兩倍。(如表1 所示)

表1 各區域農村基本情況統計表
2.2 各區域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狀況
從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收支情況及其對于農戶的收益分配情況可以看出不同區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狀況,其中東部發達地帶領先于中西兩帶。在對農民進行收入分配方面,西部地帶略高于中部地帶,可能的原因是,中西部地帶集體經濟資產本身差距較小,且國家政策往西部地帶傾斜, 相對來說更重視西部地帶農民收益狀況[3]。(如表2 所示)

表2 各區域村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表
2.3 各區域土地確權及流轉情況
全國完成土地確權辦證的份數共計2 億多份。 土地流轉主要包含轉讓、出租、互換、耕地入股等形式,在土地流轉程度方面,中部地帶流轉程度最高。西部地帶土地流轉面積最小, 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帶土地多細碎化,難以形成規模經營,不利于土地流轉經營。(如表3 所示)

表3 各區域土地確權及流轉情況統計表
2.4 各區域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及交易市場情況
2.4.1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狀況
不難看出, 東部地帶在完成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方面,比中部和西部地帶做得更好。這是因為東部發達地帶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起步較早,20 世紀90 年代起便開始探索實施,工作基礎較為扎實。另外全國村級完成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單位數量比起組級和鎮級要多得多,可能的原因是在發展集體經濟過程中,通常是以村集體為單位[4]。(如表4 所示)

表4 各區域完成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單位數
2.4.2 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狀況
農村產權交易市場是提升農村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平臺,為交易雙方提供了流轉交易的平臺、場所和配套服務。東部地帶的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數量最多,中部和西部地帶交易市場數量差距較小。總體來看,全國縣級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數量遠多于地市級和鄉鎮級,省級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數量反而最少。可能的原因是縣級交易市場作為連接下屬鄉鎮和上級省市的中間樞紐,比起鄉鎮級具備更完善的基礎設施、人力物力資源等,與省市級相比又更加了解鄉鎮產權情況,避免了跨級溝通障礙[5]。
3 以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助推共同富裕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確保實現農民共富的重要載體,要做好農村人才隊伍建設、縮小區域發展差異、 鼓勵土地流轉和穩固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成效等工作,創新激活農村各類資金、人口、土地等資源要素,最大限度地在帶動農民共同富裕方面發揮作用。
3.1 加強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人才隊伍建設
在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人才培養方面, 首先要做好人力資源培訓工作,重點關注村支書、村委書記、鄉村能人等帶頭人的綜合素質能力水平提升, 同時培育好用好鄉土人才,全面提升農民素質素養。 其次,在堅持本土人才培養的同時要積極引進外部專業人才,并根據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際發展需求, 充分吸引各類專業領域人才在鄉村振興中建功立業。最后,要創新人才工作體制機制,發展人才共建共享模式,引導區域間人才交流共享,發揮主觀能動性,提升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人力資源水平。
3.2 鼓勵土地流轉形式創新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不能“單打獨斗”,必須抱團聯動。從統計數據來看,目前我國各區域主要的土地流轉形式集中于土地出租、 互換和轉讓等傳統流轉方式。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要因地制宜鼓勵農戶以承包的土地為基礎,通過“以地換地”的方式,發展農牧業、農村服務業等,激發村民的內生動力,以解決承包地的“零散化”問題。同時采取對土地進行資本化、引入信用保證金,建立土地流轉中介服務中心等方式,發展土地規模化、提升土地的利用率,促進農村土地流轉發展,從而增加農民財產性收益[6]。
3.3 鞏固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成效
農村集體資金、 資產、 資源管理事關群眾切身利益,事關農村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各地要充分認識鞏固提升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成果的重要性, 進一步健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領導機構或聯席會議制度, 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監督和運營管理提供支撐保障。 同時探索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新辦法新機制新路徑,真正管住資金、盤活資產、用好資源,不斷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為鄉村振興打牢長遠基礎[7]。
3.4 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
從全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狀況來看,盡管近年來總體發展態勢向好, 集體經濟組織收益有所增加,但是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仍舊突出,存在區域內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總體實力懸殊問題。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發展過程中應結合自身優勢, 因地制宜探索發展路徑,區域優勢明顯的村集體,可通過提供農業生產性服務或勞務輸出等方式帶動欠發達地帶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提升其資源整合和利用效率,帶動農民增收,助推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