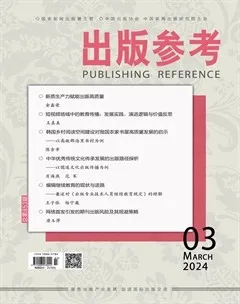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出版路徑探析
肖海燕 范軍
摘 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賡續傳承、創新發展乃至走向世界,都離不開出版的推動。新時代的出版人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覺,擔負起神圣而艱巨的文化使命,重視古籍整理出版,加大傳統文化學術出版,推進傳統文化譯著出版,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薪火相傳、在新時代綻放異彩、更好地走向世界貢獻智慧和力量。儒道文化不僅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精彩華章,而且遠播海外,在世界范圍內產生過廣泛影響。儒道典籍的整理、研究、海外譯介都是傳統文化出版的重要內容。在數字人文背景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整理、出版與傳播尤其要注重現代新技術與文化的深度融合,用媒介融合為新時代儒道文化的弘揚賦能。
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的思想瑰寶,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1],“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2]。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引,繼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筑牢根基。
出版肩負著存續文化火種、傳播科學真理的重要使命,是人類文明歷史的見證者,也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賡續傳承、創新發展乃至走向世界,都離不開出版的推動。本文試以儒道文化出版傳播為例,從三個維度探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出版路徑。
一、重視古籍整理出版,賡續中華歷史文脈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3]。在文化的三層結構(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中,精神文化是其深層內核。古籍作為精神文化的重要載體,蘊含著深邃的哲學思想和豐富的人文精神,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欣欣向榮的表征和見證。古籍整理出版對文化傳承的意義不言自明。
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中,儒、釋、道三足鼎立,共同塑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被奉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三家之中,儒家和道家作為中國本土固有的思想流派,無論是歷史影響,還是現代價值,都更加值得關注。在浩如煙海的傳統文化典籍中,儒道經典是傳統文化出版的重要內容。
儒家典籍整理出版最受矚目的是北京大學資深教授湯一介先生主持修纂的《儒藏》。[4]《儒藏》工程于2003年立項,致力于最大規模地將海內外儒家典籍系統整理、匯編成一個獨立的文獻體系,曾受到習近平總書記的特別關心和肯定。《儒藏》精華編收錄中國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儒學文獻510種(包括傳世文獻458種、出土文獻52種)、282冊,韓國歷史上用漢文著述的儒學文獻89種、37冊,日本歷史上用漢文著述的儒學文獻51種、18冊,越南歷史上用漢文著述的儒學文獻20種、2冊,可謂薈萃傳世文獻、出土文獻、域外文獻于一編,被譽為中國古籍整理編纂史上的一項創舉。目前,《儒藏》精華編的中國部分已全部整理完成,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韓國、日本、越南部分正在推進中。[5]北京大學王博教授指出:“在新時代推進全本《儒藏》編纂與研究,深度契合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精神,將助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6]
道家典籍整理出版以《中華道藏》《老子集成》等為代表。《中華道藏》[7]以明《正統道藏》《萬歷續道藏》為底本,在對原《道藏》所收道書進行校補、標點、重新分類的同時,增補了數十種重要道經,是對道家道教經典的重新結集和系統整理,對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8]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許嘉璐認為,《中華道藏》的出版是中國文化史上一件大事,這部書收錄近百年來發現的敦煌寫本及其他出土文獻(如《老子》郭店楚簡本、馬王堆漢墓帛書本等),并按現代人的閱讀習慣和圖書分類方法進行編修,具有時代特色。[9]
《老子》(又稱《道德經》)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全書八十一章,僅五千多字,卻字字珠璣,義旨玄奧,影響深遠,歷代都有人為之詮解注疏。至元代,“《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10],元以后又涌現出大量注本,形成一個內容極為豐富的老學體系。20世紀六七十年代,嚴靈峰先生先后編纂《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和《續編》,在明正統《道藏》的基礎上,網羅海內外公私庋藏之善本、孤本,影印出版,為保存老學文獻、推動老學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受當時條件所限,該書沒有標點,部分版本不夠清晰,且印數較少,難以滿足新時代學術研究與文化發展的需要。2008年,國家宗教事務局和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啟動“《老子集成》整理與編纂”項目,由華中師范大學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具體承擔,主要對歷代《老子》傳本及注疏本加以標點、校勘,重新整理,形成便于現代人使用的文本。2011年,《老子集成》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該書收錄《老子》戰國楚簡本、馬王堆帛書本、敦煌本、道藏本等重要傳本,以及保留至今的戰國至1949年中國學者關于《老子》的各種注疏文獻265種,在嚴靈峰先生所編《老子集成》的基礎上增加了87種,包括50多種非常珍貴的孤本、善本,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出版意義。誠如該書副主編劉固盛教授所言,“《老子集成》的出版,對道家學術研究的深入推進、對道家道教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以及對整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大力弘揚,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1]。
傳統文化典籍的匯編整理出版,體現了盛世修典的中國文化傳統。盛世修典,旨在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光大。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22年4月印發的《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對古籍編輯出版提出了明確要求,包括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編輯出版能力(加強傳世文獻系統性整理出版、推進基礎古籍深度整理出版、加快出土文獻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利用)、加快古籍資源轉化利用(挖掘古籍的時代價值、推進古籍的數字化、做好古籍的普及傳播)等。回望歷史,很多具有文化自覺的出版人、出版社都特別重視古籍的整理與刊刻。近代著名出版家張元濟先生即為古籍出版奉獻了畢生心血。他在商務印書館開辦涵芬樓,專門搜集古籍珍本,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叢刊》《道藏》《涵芬樓秘笈》等多套大型古籍,澤被后世,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早期中華書局的陸費逵處處與商務印書館競爭,包括古籍整理與刊刻,自成特點,成就不俗。新時代的出版人更應以高度的文化自覺,擔負起神圣而艱巨的文化使命,做好古籍的編輯出版、數字化應用、普及傳播等工作,讓古籍里的文字“穿越時空”,成為溝通傳統與現代的橋梁,讓更多讀者通過古籍感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
二、加大傳統文化學術出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發展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中華文明是革故鼎新、輝光日新的文明,靜水深流與波瀾壯闊交織”[12],“中華文明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要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13]。如何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的時代重新煥發生命活力,需要學術界與出版界攜手并肩,共同推動學術創新。
學術研究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要途徑。古往今來,真正的大學問總是飽含深沉的歷史使命感和深切的現實關懷精神。研究者回溯歷史長河,探尋遙遠歷史中動人的微光,并用生花妙筆闡幽抉微,拂去掩蓋在古籍上的塵埃,讓傳統文化在新時代重新綻放光芒。因此,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往往需要兼具燭照幽微的眼光和貫通古今的視野,緊扣時代脈搏的學術研究才能傳之久遠。前述儒道典籍匯編整理出版的意義不僅在于古籍的保存和文化的傳承,更在于返本開新,為充分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提供思想資源,因此其學術影響的廣度與深度超越了一般學術項目,體現了編纂者、出版人高度的文化自覺和學術擔當。
儒家和道家產生于春秋時期。德國哲學家雅思貝爾斯提出,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古希臘、古印度、古代中國等歐亞大陸文明古國幾乎同時發生思想突破,塑造了人類文明傳統,并對人類精神世界產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直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期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燃火焰。”[14]中國發生的這次思想突破以先秦諸子百家為代表,“而對秦、漢以降兩千年的中國文化具有定型作用,并對中國文化各領域都產生廣泛而又深遠影響的,只有儒、道二家”[15]。儒家奠定了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基礎,倡導剛健有為、自強不息;道家以自然哲學為核心,主張自然無為、貴柔守靜,二者互為補充、相互激蕩。歷代思想家立足各自的時代,對先秦儒道經典進行闡發,傳統文化精神在批判中不斷更新。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傳統文化研究熱潮的興起,學術界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儒道文化研究成果。
如何讓優秀學術成果走出書齋,發揚中國古代學術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如何讓優秀傳統文化鮮活起來,融入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離不開學術出版傳播的推動。學術出版既是學術研究成果呈現的重要形式,也是知識生產的重要平臺和思想傳播的重要載體,具有特殊的價值和意義。筆者曾撰文指出,“出版本質上是一種知識生產”,具體到傳統文化相關的出版,無論是古籍的匯編整理出版,還是傳統文化研究叢書的出版,都離不開出版人的“知識整合”,“這種知識整合本質上就是新的知識生產和價值創新”。[16]縱觀古今中外出版史,學術創新與出版繁榮往往是相輔相成的。一些學術積淀深厚、享譽海內外的老牌出版社,國外如牛津大學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公司、蘭登書屋、哈佛大學出版社,國內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三聯書店等,均以其獨特的文化品格,堅守文化本位,堅持與時俱進,出版了大量優秀的學術著作,在傳承思想文明精華、推動現代知識出版、引領學術文化創新等方面發揮過極其重要的作用。
最能體現出版人文化品格和學術引領的是大型叢書、套書和系列圖書的策劃編輯出版。[17]鐘叔河先生20世紀80年代編輯出版的《走向世界叢書》即出版人用思想點亮古籍的典范。該叢書主要收錄1840年到1911年間中國人到歐美和日本出使、考察、留學、游歷留下的日記、隨感、回憶錄等。這些近代國人睜眼看世界的雜記舊聞,從內容上看不算新奇,然而一旦集腋成裘,近代知識分子面對西潮沖擊時的反思與覺醒,給改革開放伊始正經歷又一次思想啟蒙的中國知識界帶來了強烈的思想震撼。叢書的編纂無疑是一種知識整合,而思想讓這種知識整合變得更有價值、更有力量。[18]
很多儒道文化研究成果也是以套書或叢書的形式出版并產生影響的。湯一介、李中華主編的九卷本《中國儒學史》,全面論述了2500年來儒學產生、發展、演變的全過程,被譽為“迄今內涵最為豐富、資料最為詳備、脈絡最為系統、思想最為新穎的一部中國儒學通史”[19]。在總序中,湯一介先生站在全球的高度和時代的前沿,用分析的眼光重新審視歷史上的儒學,深刻闡明了現代儒學創新發展的偉大意義,強調儒學的創新要關注其入世精神、憂患意識、和諧思想,揭示中國儒學特殊價值中的普遍價值并貢獻于世界,等等,對推動儒學研究的創新發展有極大的啟發意義。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叢書“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書系”,旨在揭示道家文化傳統的歷史內涵和現代價值,對推動道家文化創新性發展有積極意義。該書系由華中師范大學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茅山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聯合主辦,注重幾個結合:經典重刊與原創新作結合、高水平專著與優秀論文集結合、海內成果與海外研究結合、道家研究與道教研究結合等。經典重刊,如詹劍峰先生的《老子其人其書及其道論》曾于1982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獨創性、論辯性受到很高的評價。原創新作,如《明清時期武當山朝山進香研究》《道教老學史》《道家思潮與晚周秦漢文學形態》《宋代莊學思想研究》《漢魏六朝老學研究》《清代老學研究》《英語世界老學研究》等,內容豐富,視角多元,體現了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以老莊學研究為主、兼及道家道教文化其他方面研究的特色;在研究方法上,既強調理論研究,又注重田野調查,具有較高的學術文化價值。“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書系”推出后產生了很好的社會影響和不俗的市場反響。在2006年8月日本京都的中日韓三國大學出版社學術交流期間,日韓學者就對該書系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老子其人其書及其道論》等書首印3000冊,很快售罄;韓國李順連的《道論》列入政府采購書目,多次重印。[20]熊鐵基先生倡導并主持的中國老學史、中國莊學史研究具有開創性意義,在福建人民出版社等單位大力推動下,得到國家出版基金強力支持,出版了一系列成果。新近刊行的五卷六冊《中國老學通史》(劉固盛主編)先后被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2022年度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是第一部系統、全面反映中國老學發展歷史,深入分析并提煉出不同歷史時期老學的理論創建和思想特點,揭示老學與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深刻聯系,闡明中國老學的思想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的通史性著作。這一大型項目無論是從學術史,還是從出版史來看,都是富有集成與創新價值的。我們講中華優秀文化的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學術研究和學術出版理當攜手前行。
儒道文化有很多具有時代價值的內容值得深入挖掘,如儒家的民本思想、道家的生態智慧等,對今天治國理政的理論與實踐均有借鑒意義。加大傳統文化學術出版,不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和精髓,而且能更好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新時代“重燃火焰”。新時代的出版人要秉持文化使命、聚焦時代精神、追蹤學術前沿,主動“出題”,精心策劃,發揮學術引領作用,與學術界一起將傳統文化研究推向新的境界。
三、推進傳統文化譯著出版,助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21]“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造就了中華文明的博大氣象。
譯著出版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橋梁。湯一介先生曾說:“世界學術文化發展的總趨勢應是在全球意識觀照下的文化多元化發展……如果我們要想對人類文明做出重大貢獻,就不僅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且還要‘會東西之學。”[22]這句話雖然是對學術的要求,對出版也同樣適用。具有高度文化自覺的出版人既要做異域文化的“盜火人”[23],也要做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推動者。
中國近現代出版人中不乏全球意識和世界眼光的“盜火人”。張元濟、王云五在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期間都十分重視中西文化的溝通。從“嚴譯八種名著”“林譯小說”“萬有文庫”到“漢譯世界名著”,再到“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系統譯介西方學術經典一直是商務印書館堅持的出版傳統。這些世界學術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典著作,凝聚了幾千年來積累的人類思想文化精華,在促進古老中國社會轉型和歷史進步方面曾發揮過難以估量的作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的重大學術翻譯出版工程,亦為我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與“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可謂異曲同工。前者以“借鑒海外漢學,促進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為出版宗旨,在研究方法、研究領域、學術范式等方面為中國學人打開了一扇窗,被譽為“學術界與出版界良性互動的典范”。
文明需要互鑒,文化理當交流。我國在注重吸納世界文明優秀成果的同時,近些年來也高度重視中國文化、中國出版走出去。其中重要的政策舉措包括設立和實施“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絲路書香工程”“中國當代作品翻譯工程”“中華學術外譯項目”,以及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中外圖書互譯計劃等,有力地推動了出版業的海外影響力和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提升。這中間,很多工程和項目都涉及儒道典籍。
在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方面,儒道文化出版傳播有獨特優勢。儒道文化不僅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精彩華章,而且遠播海外,在世界范圍內產生過廣泛影響。《儒藏》精華編所收韓國、日本、越南歷史上用漢文著述的儒學文獻,即儒家文化在東亞傳播的有力見證。儒學傳入歐美后亦受到廣泛關注。歐洲最早的儒家經典譯本是1594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用拉丁文翻譯的“四書”。1626年,法國傳教士金尼閣又將“五經”翻譯成拉丁文出版。“東海西海,心理攸同。”隨著越來越多的儒家經典被譯成西方文字,儒家思想中具有普遍價值意義的理念在歐美引起強烈共鳴。在19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會議通過的《走向全球倫理宣言》中,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定為全球倫理的道德黃金律(又稱“道德金律”或“金規則”)。[24]在儒學復興、現代化轉型及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現代新儒家的貢獻不容忽視。以杜維明、成中英等人為代表的海外新儒家強調在全球“文明對話”視域下對傳統儒學進行“現代轉化”,郝大維、安樂哲等人亦致力于全球視域下當代儒學的重構,是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的典范。因此,傳統文化譯著出版要重點關注海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
《老子》(《道德經》)是《圣經》之外譯本最多的一部經典。據統計,截至2022年,世界上共有2052種《老子》譯本,涉及97種語言[25],堪稱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典型。最早的《老子》譯本是17世紀末比利時傳教士衛方濟的拉丁文譯本。1842年,儒蓮的《老子》法文譯本在巴黎出版。1868年,《老子》首個英譯本——英籍傳教士湛約翰的《老子玄學、政治與道德的思辨》由倫敦圖伯納出版社出版。1870年,維克多·施特勞斯的《老子》德文譯本問世。[26]隨著譯本數量和語種的不斷增加,《老子》在海外的傳播越來越廣,影響也越來越大。世界對《老子》的關注,從最初的宗教領域拓展至哲學、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科學等多個領域。20世紀以來,面對戰爭、災難、生態危機以及伴隨工業化、科技高速發展而來的道德困境等現代文明弊病,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將目光轉向道家,希望在《老子》中尋找救世良方。德國哲學家尼采將《道德經》喻為一個滿載寶藏、永不枯竭的井泉。[27]海德格爾稱老子的“道”中隱藏著“思想者的道說”或語言的“全部秘密之所在”,其含義比西方人講的理性、精神、意義等更原本。[28]日本首位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湯川秀樹這樣評價老子:“早在兩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經預見到了今天人類文明的狀況,甚至已經預見到了未來人類文明所將達到的狀況。”[29]美國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卡普拉推崇道家的生態智慧:“在偉大的諸傳統中,據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態智慧。”[30]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經典跨越時空,成為全人類共有的精神文化遺產。海外的《老子》翻譯與研究成果,對現代化視域下的道家文化研究尤其是當代“新道家”的建構有啟示意義,因此也是傳統文化譯著出版應關注的重要內容。
《儒藏》《老子集成》收錄的典籍,除儒道經典的傳本之外,還包括歷代的注疏本,體現了秦、漢以降中國思想文化的更新發展,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推進古籍數字化,以這些典籍為基礎開展儒道學術研究及其外譯出版,搭建國際學術交流的綜合平臺,可以為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提供中國智慧。因此,推進儒道文化相關的譯著出版,對助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有重要意義。
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賡續傳承、創新發展及走向世界,是新時代賦予當代出版人的文化使命。我們應主動扛起文化這面大旗,以媒介融合、數字人文的興起和發展為契機,以大數據、新型人工智能等為手段,以儒道文化為重點,重視古籍整理出版,加大傳統文化學術出版,推進傳統文化譯著出版,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薪火相傳、在新時代綻放異彩、更好地走向世界貢獻智慧和力量。
(作者單位系:肖海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范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