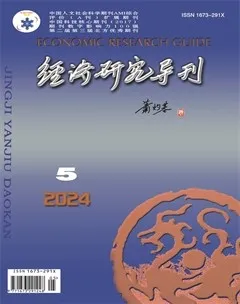鄉村振興背景下新鄉賢角色分析:一個文獻綜述
李慶真 朱志君
摘? ?要:鄉賢作為鄉村社會發展的重要精英群體,一直根植于村落共同體變遷與城鄉關聯的歷史進程中。深處當下時代發展變革中,區別于傳統鄉賢,時代賦予當代鄉賢新的內涵,作為農村發展的重要引導力量,深入農村發展當中。結合時代變遷背景論述新鄉賢的角色變化,以及在地區經濟發展差異、鄉村內生權威弱化等困境中,如何明確新鄉賢的時代角色,更好地發揮其功能。
關鍵詞:新鄉賢;鄉村振興;角色變遷
中圖分類號:D616?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4)05-0035-03
一、問題提出
2016年8月,《人民日報》刊發一篇名為《人民日報縱橫:尋找今天的“鄉賢”》的文章,讓人們日漸淡忘的鄉賢角色再一次走入視野。封建時期,鄉紳、鄉賢、鄉村精英、地方權威就在傳統農村社會扮演不同角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在政策導引、經濟吸引等綜合因素的推動下,導致農村人口外流,使得原本的農村生產經營模式瓦解,傳統地方內生權威日益萎縮。黨的十九大以來,為促進農村地區的發展,落實鄉村振興戰略,2014—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在政策層面確立鄉賢的角色定位及功能。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明確強調在深化村民自治實踐中要“積極發揮鄉賢作用”。
鄉賢作為傳統農村社會的地方權威,是鄉村治理的中間階層,在彌補國家與農民間聯系的斷裂空間上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鄉賢回歸鄉村參與基層治理被認為是解決鄉村發展難題、克服現代化鄉村治理困境的重要依托。也正因此,鄉賢群體成為越來越多專家、學者的重點關注對象,他們強調新時代要注重發揮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作用。梳理文獻,本文旨在從鄉賢參與基層治理的維度,面臨農村發展困境、內生權威弱化、時代變遷等背景下,如何明確新鄉賢的時代角色,更好發揮其功能。
二、鄉賢角色的歷史變革
受皇權至尊思想影響,形成“國權不下縣”[1]的治理結構,這就使得傳統鄉賢成為縣下鄉村治理的內生權威。原始社會時期,氏族部落的首領擔任族群的管理角色,教化族人、維護部落安定。商代村落分為兩級,一級是承擔祭祀功能的大型村邑,由宗族長掌權管理;另一級則是小型村落,只具備基本生產和生活功能的貧困地區。這種簡單的村邑組合是早期農村社會結構的基礎單元,宗族長是治理結構的核心,扮演早期鄉賢的角色。春秋戰國以后,皇權逐漸下移,基層確立郡縣制,加強對地方的掌控。基層單位的“雙軌制”[2]不僅削弱了鄉賢職能,還細化分工,輔助地方官員收繳賦稅、調解矛盾、禮儀教化、公益救助。漢朝時期,《百官公卿表》記載:“縣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盜賊……”[3]此中職能明晰的“三老”“嗇夫”“游徼”便是由地方正直、剛克、柔克三種德行的長者擔任。東漢末年,孔融首創鄉賢祭祀活動。范曄《后漢書》記載:“孔融為北海相,郡人甄士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辭源》稱此為祭祀鄉賢之始[4]。漢代以后,鄉賢文化越發豐富,祭祀鄉賢被視為教化百姓,提升鄉賢社會地位的重要手段。隋唐時期開創科舉制度以選賢任能,愈來愈多的文人志士通過科舉考試實現階層跨越,希望可以實現“出則為仕,退則為紳”的人生追求[5]。宋朝時期,國家經濟發展迅速,百姓有相對穩定的生活保障,國家人口增至1億左右。和諧社會的治理自然也要借助德治手段,如同國法、家規,在民間出現成文的鄉約規范人們行為。北宋陜西地區呂氏兄弟創作的《呂氏鄉約》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成文鄉約,它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為基準,教化一方百姓、改良地方風氣。宋元時期為先賢設立專祠祭祀,后來為了解決前朝鄉賢祠多且祭祀繁雜的問題,明朝時期祭祀先賢的方式發生變化。一是設立鄉賢總祠將已故賢人一并供奉其中;二是將祭祀鄉賢活動與學生教育結合起來,傳遞鄉賢文化。明代洪武年間,中央政權授予地方及第生員部分特權,由此成為生員變成階層蛻變的第一步。但是生員晉升的名額有限,以至于許多生員不得不困于鄉村之中,使得一些人出現了群體異化傾向,劣變為劣紳、惡霸、無賴等。清朝以后,科舉制度被廢除,不僅阻斷學生階層晉升渠道,也使得地方失去官方認證鄉賢的依據,地方鄉賢群體力量逐漸萎縮。
三、新鄉賢的內涵
何為新鄉賢?本文通過以下幾個維度進行分析。一是新的時代背景。不同的時期,社會導向及治理需求是不同的。傳統鄉賢作為政府與村民的中介,協助地方官員尋求一方穩定。而現代鄉賢正處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各地力求變革以實現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高萬芹從精英理論角度分析新時代背景下鄉賢的內涵,認為新時代的鄉賢應該是各行各業的成功精英,他們有現代化的發展理念和前瞻的視野,以及創業經商的成功經驗,才是新鄉賢應該具備的時代品格[6]。二是農村發展格局不同。隨著時代的變遷,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變化,與傳統人口集聚的農村社會不同,當前農村面臨勞動力短缺、資金不足、人才匱乏、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發展理念保守等一系列問題,這也是新鄉賢回歸鄉村參與治理面臨的挑戰。三是鄉賢的群體構成不同。相較于傳統鄉賢,對新鄉賢的群體認知產生平民化、泛化趨勢,既不要求其地域性,也不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