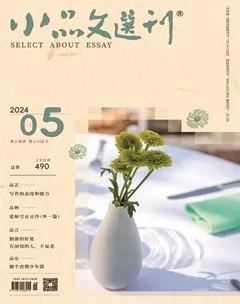聰明的“鈍感”
游宇明
人生無疑需要心靈的敏感,不悖內在的個性,并與環境適度和解,可以少走彎路。
不過,生命不僅要有敏感,還得有鈍感。所謂“鈍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遲鈍”。
我有一個朋友是畫畫的,他有良好的出身,父親是文學教授,母親是舞蹈演員,從小受到藝術的熏陶,對色彩、線條、意境、韻味之間的東西很熟悉。朋友在事業上走得很順,20多歲入省展、國展,并在京城舉辦了個展,30來歲加入省美協、中國美協。朋友事業上的風生水起引起一些人的嫉妒,每次聚會,總有人問他:“入美展需要花錢吧?”“你進省美協和中國美協,找了誰?”每逢這種時候,朋友都只是淺笑一下,不予回應。說什么好呢?講入展沒花錢、加入美協未找人,這些人未必愛聽;說自己入展花了錢、加入美協找了人,又不符合事實,且涉嫌誣蔑別人。有一點朋友做得很到位:無論別人怎樣懷疑他的“少年得志”,他都沒當回事,該干什么干什么。后來,朋友的名望越來越高,畫也賣得越來越貴,那些嘰嘰喳喳的聲音反而沒有了。
說到這里,我們可以聊聊“鈍感”的好處了。人不是鈔票,不可能人人喜歡;我們花紅柳綠的事業也不是紅燒豬蹄,想啃,就有機會咬上一口,因此,一個人的為人處世遭受五花八門的諷刺、嘲笑,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增廣賢文》有言:“誰人背后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不是鼓勵人嚼舌根,而是教導我們要有一定的鈍感,面對流言八風不動,不必像山羊一樣一觸即跳。
在人際關系上,我們要有鈍感,遇到各種挫折時,同樣應該如此。世間有一種人非常精明,時刻考慮的是如何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收益,他們只想走順途不愿遭逆境,只要掉入逆境立即會怨聲載道、逃之夭夭。還有一種人盯住一個目標便永不放松,碰到河流一定會架橋,逢上石頭一定會炮劈,生活給他們再多的風雨,他們也會癡情地守望下一次遠行。有段時間,大家都在談陳寅恪,可是少有人知道陳寅恪一生經受了許多磨難,比如眼疾,比如特殊時期遭逢的人格侮辱。可是,即使晚年雙目失明、沒有公開發言的機會,他依然對學術癡心不改:經常口授學術著作,讓家人記錄下來,以等出版的時機。正是這種面對艱難的“鈍感”,使他成了社科研究“三百年來第一人”“教授的教授”(傅斯年語)。
鈍感并不意味著愚蠢,也不代表卑微,更多的時候,它是源于一種眼光、一種格局,一種超越普通人悲歡的情懷。一個人不僅能看到眼前的茍且,還能看到詩和遠方;不僅能看到卑劣的人性,也能看到社會整體上的光亮;在反常的時候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只是個短暫的過程,生活從來不曾脫離“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行事邏輯,你的時間、精力便可集中,內心也就有了分辨力,該生鈍感的時候會長出足夠的鈍感,該有敏感的地方會像指南針一樣靈動。
哲人說:“寧靜致遠。”聰明的鈍感永遠是寧靜的基礎。
選自《聯誼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