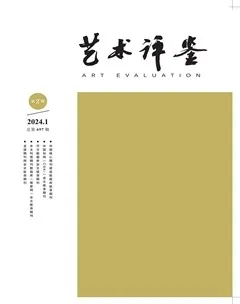守正與創新:劉三姐歌謠藝術的重構與發展
【摘? ?要】傳統是一條流動的河。歌謠隨時代與地方為轉移,并非永遠不變之一物。劉三姐歌謠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劉三姐歌謠從田間地頭傳唱到戲劇與歌劇舞臺,再到銀屏的展演、傳播過程,其實就是一個從傳播方式到藝術本體不斷重構發展的過程。這些重構發展主要集中于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彩調劇、歌舞劇和電影等藝術載體中完成,由此奠定了劉三姐歌謠的巨大影響力,并一直延續至今,還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成為廣西代表性的文化品牌。劉三姐歌謠守正創新、重構發展的過程其實就是守正創新精神的集中體現,而這一過程又引發大家對于當下非遺保護的一些思考。
【關鍵詞】劉三姐歌謠? 守正創新? 重構發展
中圖分類號:J6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4)02-0007-06
傳統音樂理論家黃翔鵬先生曾說,傳統是一條流動的河。這句話是說傳統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要順應時代的需求與發展與時俱進,不斷地創新發展,從而延續自己的生命力。同樣,劉三姐歌謠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就其本源而言,劉三姐歌謠文化的創造與傳承主體首先是壯族和壯侗語民族創作的歌謠文化積淀和升華,同時又在漢、瑤、苗等民族雜居的地區流傳并衍生演化,最終形成豐富多彩的劉三姐歌謠文化。①因此,劉三姐歌謠發展過程其實就是一個不斷守正創新的重構發展過程。劉三姐歌謠正是通過一次次守正創新的重構發展,一直延續著自己的生命活力。劉三姐歌謠重構發展的內容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傳播方式從現實生活中的歌圩等場合到戲劇、歌劇藝術舞臺,以及銀屏的創新重構發展,參與的對象主要是被直接采用的劉三姐歌謠;二是劉三姐歌謠藝術本體如歌詞與曲調被改編后所完成的創新重構。本文僅是對后者的相關論述。
一、戲曲《劉三姐》及其劉三姐歌謠藝術的重構
劉三姐從作為民間傳說移植到戲曲劇本創作到搬上舞臺表演,經歷了較為漫長的過程。曾經涉及《劉三姐》劇本創作與演出的劇種非常多,但最后只有彩調劇《劉三姐》脫穎而出,并在廣西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究其原因,與其對劉三姐歌謠的成功使用有至關重要的關系,劉三姐歌謠在彩調劇《劉三姐》中完成了它的第一次重構發展,開始在廣西家喻戶曉。
(一)戲曲《劉三姐》的劇本創作及演出
戲曲《劉三姐》劇本最早出現于清乾隆年間蔣士銓撰寫的昆劇《雪中人》的第十三出中。20世紀30年代,廣東海陸豐正字戲中也有《劉三妹割草》。②1953年4月,彩調劇《劉三姐》為獻禮劇目匯演,受邀到南寧參加全自治區演出,演出后對社會各界產生了深遠影響。緊接著,關于《劉三姐》的創作組在柳州成立,將許多精彩的民歌經選擇、改造、提煉、融化到劇本的修改稿中,經柳州彩調劇團再次排練,在柳州首演,進而到南寧及全區各地演出,反響更為強烈。
后經倡導,廣西各縣、公社、大隊、廠礦、學校紛紛排演《劉三姐》,形成《劉三姐》演出高潮。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廣西有1209個專業和業余文藝單位演出《劉三姐》,參加演出人員有58000多人,觀眾多達1200萬人次。1960年4月21日—4月27日,《劉三姐》文藝會演在南寧舉行,演出中有彩調、粵劇、邕劇、采茶戲等11個劇種,共演出23場。各地來的參演代表共1400多人,其中,業余演員占57%,飾演劉三姐的45人中,業余演員有31人。這種盛況空前的演出景象在廣西戲劇發展史上可謂前所未有。在這次大會演中,柳州彩調劇《劉三姐》獲得前所未有的推崇。這一劇經過不斷演出、修改后,創作組后來進行了仔細思考,曾多次組織成員深入民間進行采風,在采風過程中拜訪了各種不同的民間歌手,并整理和搜集民歌近萬首。經過多次召開座談會進行探討,后來寫了七個稿本的《劉三姐》,其中以第三稿本最受歡迎。③之后的進京演出并引起巨大轟動的歌舞劇《劉三姐》就是在彩調劇《劉三姐》第三稿本基礎上汲取其他劇種優勢,博采眾長改編而成。1980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給予高度評價,并授予柳州市劉三姐創作組劇本創作一等獎。
(二)歌謠劉三姐在彩調劇《劉三姐》中的重構
彩調劇《劉三姐》首次將壯族歌仙劉三姐的形象進行藝術化呈現,成功將劉三姐從傳說到舞臺藝術的第一次突破,也使劉三姐歌謠從田間地頭的草根民歌藝術實現向專業舞臺藝術的第一次重構發展。正如彩調劇《劉三姐》的主創人員之一曾昭文先生在談到該劇創作時所言:“不懂山歌,根本談不上創作《劉三姐》。《劉三姐》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把山歌融進戲劇之中,這是歷史上所沒有的。”④以下擇例進行分析。
1.歌詞的重構
當年彩調劇《劉三姐》的創作人員之一龔邦榕說:“為創作《劉三姐》,我們搜集了25萬字的山歌,形成了厚厚一本山歌集,《劉三姐》一百多首山歌,就是從中提煉出來的。”彩調劇《劉三姐》對山歌的使用并不是隨隨便便,拿來就用。正如該劇主創人員曾昭文先生所言:“我們的經驗是,山歌不可隨直接收到就用上,必須進行修改。”⑤例如:“唱山歌,這邊唱來那邊和,山歌好似春江水,哪怕灘險彎又多。”其中的“春江水”,原來是“紅河水”。紅河是廣西的母親河,放在歌詞里本來也非常合適,但創作組的專家之一江波認為“紅河水太過具體、缺乏詩意”。大家經過討論,最后改成意境很美的“春江水”。這一改動便極大地擴展了歌曲含義的外延,已經不再單指紅河流域,而是可以概括有山歌傳唱的所有地方。經過這一創新,這首歌曲最終也成了劉三姐歌謠中流傳最廣泛的一首經典歌曲。
2.曲調的重構
1960年,歌舞劇《劉三姐》的總導演鄭天健在《關于〈劉三姐〉的創作》一文中介紹道:“彩調劇《劉三姐》第三方案在音樂上除采用彩調的傳統唱腔外,還用了很多民歌,并由專業音樂工作者對原始民歌進行改編。”⑥例如劇中的曲十五、曲二十六等均由柳州山歌改編而成。其中最為典型與成功的當屬主題曲《山歌好比春江水》曲調的編創。
關于彩調劇《劉三姐》的曲調,最初是將柳州民歌《石榴青》以口傳的方式進行改編而成,因為在當時對于簡譜掌握不熟悉,所以采用的是口傳的方式。后來彩調劇團根據需要成立專門的音樂設計組,設計組成員精心思考后,又根據《劉三姐》的音樂重新設計改編,到該劇目正式上演時,才正式把《石榴青》的音樂重新設計成《山歌好比春江水》這一嶄新的音樂曲調,但是音樂元素基本是建立在《石榴青》的基礎之上。⑦改編后的旋律得到大眾的認可,這樣的處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正如當時音樂創作人員之一黃友琴所說:“采調劇《劉三姐》的演出實踐證明,改編的柳州山歌(現又稱柳州民歌)曲調作為采調劇《劉三姐》主題音樂曲調,不僅保留了原山歌曲調的色彩與風格,且比原山歌曲調更集中和完整,更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唱。”⑧“將山歌變成了唱腔,將山歌的唱腔加入彩調劇中,這在當時是一種新的創造。”⑨這無疑是對劉三姐歌謠很好的重構發展。
二、歌舞劇《劉三姐》及其劉三姐歌謠藝術的重構
早在1929年的《戲劇》雜志第4—6卷就刊載有歐陽予倩創作的歌劇《劉三妹》。⑩但作為藝術舶來品的歌劇,以本土內容為題材的作品上演在當時的中國還比較少見,以戲曲內容為題材的歌劇上演更是鳳毛麟角。所以,《劉三姐》以歌舞劇形式的演出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得以實現。劉三姐歌謠在這一藝術載體中完成了它的第二次重構發展,影響力走出廣西,遠播至全國大部分地區。
(一)歌舞劇《劉三姐》的演出及其影響
1960年4月,在廣西南寧舉行了關于《劉三姐》的劇種會演大會,演出就包含彩調、采茶戲、桂劇等11種和《劉三姐》相關的劇目。通過這一次大會演后,集中籠絡了南寧眾多優秀的文藝創作者,充分發揮了廣大文藝創作者的智慧,大家根據原彩調劇《劉三姐》的版本,最后綜合各自劇團的演出版本,重新整理改編,最終形成全新的歌舞劇《劉三姐》,然后通過廣西民間歌舞劇團重新進行編排,劇目編排完成后在當地成功進行多場演練,影響頗大。緊接著在同年7月,受到黨中央的邀請,全體劇組奔赴北京開展為期兩個多月的匯報演出,可以說意義非凡。后來相繼收到各兄弟省市的邀請,全體劇種又分別到吉林、天津、遼寧等13個省、市、自治區進行巡演,演出足跡遍及全國24個城市,巡演近一年的時間,所到之處都引起很大的轟動,由此可見,該劇深受各地百姓喜愛。尤其是該劇在北京演出后,影響力與日俱增。后來在1982年8月《散文》發表的李潤新《壯家三姐擅斯文》一文中進行過這樣的描述:“1960年6月,《劉三姐》在首都公演了,一時轟動北京城。許多觀眾百看不厭,《劉三姐》唱段到處傳唱,真是京城無處不飛歌。萬眾齊贊《劉三姐》,一致認為《劉三姐》是繼《白毛女》之后歌劇發展的第二個里程碑。是戲劇民族化、大眾化的典范,是中國風格、為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范例,是我國藝術寶庫的珍品。這一年十月間,四進懷仁堂演出,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贊揚。”
(二)劉三姐歌謠在歌舞劇《劉三姐》中的重構
歌舞劇《劉三姐》在整體的藝術處理及歌詞與音樂等創新方面都受到了文藝界的好評。如《從“劉三姐”談唱詞》一文談道:歌舞劇《劉三姐》貫穿始終的絕大部分唱詞,都是準確、生動、優美、樸素、真摯的詩句,民歌和彩調的相互結合、相互熔化的結晶。對于劇中人物來說,這些富于民歌化、詩歌化的唱詞,既發揮了抒情的力量,又具有表現人物性格的特色。
1.歌詞的重構
歌舞劇《劉三姐》對劉三姐歌謠歌詞的重構發展主要采用翻譯點化、漢語改編的方式,或者是對原詞做畫龍點睛式的改動。例如:“莫夸財主家豪富,財主心腸比蛇毒,塘邊洗手魚也死,路過青山樹也枯。”這首歌謠前身是流傳于廣西右江—帶的一首舊情歌,意思是責罵一個變心婦女,說她在右江岸邊洗手,被毒死的魚像浮云鋪滿江面;她路過村寨,幾百個村的黃牛就會瘟死;她走過山邊,右江兩岸的樹林就枯死。劇作者則根據劇作主題需要,經過翻譯點化,用漢語改編成上述形式,既保留了濃郁的壯歌韻味,又大幅增強了歌詞意蘊的表現力,入木三分地刻畫出這位變心婦女的狠毒。
“連就連,我倆結交訂百年,哪個九十七歲死,奈何橋上等三年。”對于這首山歌,著名詞作家、編劇喬羽先生認為:“這是劇本中最有特色,最能表現劉三姐式的愛情,被公認為是最好的一首情歌。”這首山歌把原來的“結交六十年”改成“結交訂百年”,于是后面便自然可以改為“九十七歲死”,而不是“六十七歲死”。雖然只是區區幾個字的改動,但可謂畫龍點睛,字字千金,使那種執著而奔放的愛情口吻脫穎而出。“這使人很自然地聯想到我國人民形容愛情堅貞不渝的那句成語‘百年偕老,更覺得意味深長。”
2.曲調的重構
歌舞劇“劉三姐”中采用的民歌曲調絕大多數是經過較大的改編和發展的。1959年,在彩調劇《劉三姐》的創作中,創作者們開始有新的認識,也在思考如何將民歌曲調引入并進行改編和發展,經過不斷琢磨后,將柳州山歌“石榴青”確定為《劉三姐》的主題音樂,并將其展開發展。柳州山歌“石榴青”及其他廣西地方山歌被改編成歌舞劇中唱段,改編后的山歌對于劉三姐的形象塑造更加鮮明。
另一方面,歌舞劇《劉三姐》在演唱形式方面有很大創新。獨唱和對唱是民歌的兩種主要演唱形式,在彩調劇《劉三姐》中均有運用。為了進一步展現劇情沖突,歌舞劇《劉三姐》除了增加對唱唱段的數量外,還在第六場《陰謀》和尾聲《傳歌》等部分進行深化,將合唱形式引進去,增強了戲劇的表現力。
三、電影《劉三姐》及其劉三姐歌謠藝術的重構
歌舞劇《劉三姐》公演后,立即在全國各界具有重要影響,其中在電影界影響迅速,很多電影界專業人士由此獲得創作靈感。其中在1961年,由喬羽改編、雷振邦作曲、蘇里導演、黃婉秋主演的電影《劉三姐》由長春電影制片廠攝制完成。在電影中,劉三姐歌謠完成了它的第三次重構發展。影片于1962年4月先后在全國及東南亞一帶上映,借助現代媒介的巨大傳播效應,劉三姐歌謠與電影一樣,影響力走出中國,波及世界范圍。
(一)電影《劉三姐》的上映及其影響
電影《劉三姐》在全國公映后,除了在全國掀起一股浪潮,而且很快風靡國外,首當其沖是影響整個東南亞。其中,在1962年,拍攝成功的電影《劉三姐》在香港首次公映。在影片公映期間,香港各地涌現出一股唱山歌的浪潮,大街小巷都能感受到這樣一種非凡景象。由于影片的影響力巨大,后來分別于1964與1978年,影片《劉三姐》又再次登上香港復映,這兩次的復映同樣掀起一股關于劉三姐唱山歌的熱潮,同時也帶動了《劉三姐》的唱片和錄音帶暢銷全香港。“劉三姐”成了廣西的代名詞,看過《劉三姐》的人多年以后都還會對影片中動聽的山歌、美麗的山水和機智的劉三姐形象記憶猶新。正如著名導演張藝謀在執導大型山水實景劇《印象·劉三姐》時說:“電影《劉三姐》讓我影響至深。我小時候對劉三姐的印象,那就是人漂亮、歌好聽,劉三姐是我兒時最美麗的回憶。”1980年,劉三姐的扮演者黃婉秋隨團前往新加坡演出時,難以置信地親歷了當地一位馬來西亞華僑時隔觀影十余年仍能成段唱出《劉三姐》中山歌的一幕。
(二)劉三姐歌謠在電影《劉三姐》中的重構
電影《劉三姐》的故事內容源自歌舞劇《劉三姐》,甚至影片中歌詞的內容和風格及音樂元素等都源自歌舞劇《劉三姐》,尤其是山歌的數量、歌詞內容和風格。電影里出現的山歌一共111首,屬于原樣移植或稍作改動的就有78首,而至今廣為傳唱的《多謝了》《不是命》《虧了虧》《藤纏樹》《什么水面打跟斗》《什么結果抱娘頸》《什么有嘴不講話》《州官出門打大鑼》《天崩地裂我不怕》等多首山歌也都悉數包括其中。以下擇例進行分析。
1.歌詞的重構
電影《劉三姐》把所有山歌歌詞的語言載體都改為漢語普通話,并根據人物性格與劇情安排需要對部分歌詞內容稍作改動。例如,山歌《藤纏樹》在歌唱語言載體上先后經歷壯話、客家話,以及電影中使用的漢語普通話等轉變。其原來的歌詞是:“入山看見藤纏樹,出山看見樹纏藤;藤生樹死纏到死,樹生藤死死也纏。”在電影里則改成:“山中只見藤纏樹,世上哪見樹纏藤,青藤要是不纏樹,枉過一春又一春。”這一改動既使歌詞增加了一些人生哲理內涵,又更加適合于口頭傳唱。而漢語普通話的使用無疑極大地擴展了電影《劉三姐》的受眾面。
2.曲調的重構
電影《劉三姐》的音樂均由滿族音樂家雷振邦完成。在電影《劉三姐》中,許多歌曲都采用平調山歌,如《山頂有花山腳香》,歌曲旋律較為簡單流暢、婉轉、朗朗上口。這首曲子也是整部電影的主題旋律。作曲家雷振邦共為影片編創了十四首歌曲作品,這些作品中,有《采茶姐妹上茶山》《山歌好比春江水》《只有山歌敬親人》等,均可以稱為經典作品,影片中賽歌會上那些幽默詼諧的經典唱段,把以劉三姐為代表的形象刻畫得惟妙惟肖。而現在,這些歌曲都已成為廣西民歌的代表符號。
另一方面,為完美塑造劉三姐這一山歌經典人物形象,導演蘇里煞費苦心,除了故事情節和外在形象的設計外,在人物聲音及歌唱表演方面也精益求精,特地邀請配音張桂蘭和藝術家傅錦華為影片配唱,傅錦華是原歌舞劇《劉三姐》的表演者,也是一名著名的彩調劇表演藝術家。有她們為影片進行配音和配唱后,為影片人物形象的塑造錦上添花。也是由于在這部影片的精彩表演,傅錦華于2005年獲得“當代中國電影歌曲《劉三姐》優秀演唱獎”殊榮。原本由民間歌手傳唱的劉三姐歌謠在電影中都由專業的歌唱家配唱,自然會為歌曲大大增色。因此,這也算是劉三姐歌謠在聲音載體或演繹上的重構發展,即由草根歌手升華為專業歌手演繹。
四、結語
劉三姐歌謠從彩調劇《劉三姐》,到歌舞劇《劉三姐》,再到電影《劉三姐》,其藝術本體和傳播形式經歷了三次重構發展,從而使其影響力走出廣西,走向全國,乃至世界范圍。劉三姐歌謠由此從草根藝術重構發展為經典藝術,并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成為廣西民歌的代表性符號,成為廣西代表性的文化品牌,這引發大家的一些思考。
一方面,正如文中引言部分所提到的那樣,傳統藝術只有不斷地創新,才能發展,延續生命活力。但這個創新無疑不能脫離傳統根基,即守“正”。回顧劉三姐歌謠的三次重構發展,不難發現,它的每一次創新、每一次發展都是緊緊圍繞其傳統根基的。所以,守正是創新的前提和基礎,這無疑也是彩調劇《劉三姐》可以從眾多戲曲劇種中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可以說,三次集中性守正創新的重構發展逐步奠定劉三姐歌謠的巨大影響力。也就是說,創新其實也是守正的目的和路徑。
另一方面,在文化全球化及社會現代化快速發展的當下,傳承發展陷入困境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無疑可以借鑒劉三姐歌謠的發展模式,即以該項非遺發展過程中某一(些)感人的事情或某位(些)感人的傳承者故事,連同該項非遺一起改編成戲劇舞臺或影視作品,借助戲劇舞臺尤其是影視作品的巨大傳播效應,激發非遺流傳地民眾的文化自豪與文化自信,喚起他們非遺保護的文化自覺意識。當然,在文化娛樂樣態異彩紛呈、文化娛樂發展日新月異的當下,這些與非遺相關的戲劇影視作品所引發的效應是無法與半個世紀之前的《劉三姐》相比的,但至少也可以產生“死水微瀾”的效果,一如2016年5月在全國公映的嗩吶非遺題材電影《百鳥朝鳳》。或者,還可以像劉三姐歌謠一樣,之所以一直保持它全國性的影響力,是因為圍繞著它的重構發展與展演傳播的舉措一直沒有停止過,即一直沒有停止過對它的守正創新。因此,非遺保護無疑也必須秉持守正創新的精神。
參考文獻:
[1]趙德光.民族文化重構的三重交奏理論初探——兼論石林阿詩瑪文化的重構問題[J].云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04):156-159.
[2]黎學銳.劉三姐歌謠[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11.
[3]黃桂秋,曹俏萍.廣西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叢書——劉三姐歌謠[M].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
[4]梁庭望.中國壯族[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2.
[5]覃德清.詩性的思維——壯侗民族民歌文化傳承與發展的調查和研究[M].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
作者簡介:胡小東(1975—),男,貴州民族大學音樂舞蹈學院教授,博士,主要從事民族民間音樂研究。
基金項目:本文為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課題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名稱:侗族大歌腔詞關系研究,項目編號:21GZYB32。
①廖明君、韋麗忠:《劉三姐歌謠·古歌卷》,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5年。
②鄧凡平:《劉三姐劇本集》,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
③中國戲劇家協會廣西分會:《歌舞劇〈劉三姐〉評論集》,南寧: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9—21頁。
④胡椒粉、鐵戈:《電影〈劉三姐〉,創作還是抄襲?》,《法律與生活》,1996年,第3期,第2—6頁。
⑤黃勇剎:《壯族歌謠概論》,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65、76頁。
⑥李林:《三首〈劉三姐〉歌曲的歷史原貌》,《中國音樂學》,2011年,第3期,第49—54+74頁。
⑦黃友琴:《關于采調劇〈劉三姐〉的主題音樂》,《人民音樂》,1978年,第5期。
⑧羅崗生、李蓮芳:《劉三姐研究資料集》,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6、279頁。
⑨劉一寧:《重寫〈劉三姐〉》,《南方文壇》,2008年,第1期。
⑩蒙雄強:《電影〈劉三姐〉拍攝的臺前幕后》,《文史春秋》,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