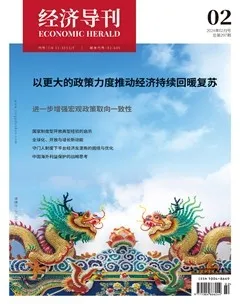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學科化的核心要件
2023年10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強調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華民族共同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等理念,鮮明提出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作為民族地區各項工作的主線,進一步拓展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形成了黨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構建科學完備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要優化學科設置,加強學科建設,把準研究方向,深化中華民族共同體重大基礎性問題研究。”①
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催生了中華民族共同體
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基于不同的理念有不同的解釋。基督教對于人類社會的解釋,就是上帝締造社會并推動其前進;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則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根本力量,一定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與馬克思處于同一時代的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在對美洲印第安部落進行數十年觀察的基礎上,寫了《古代社會》一書,其中提供了印第安人原始部落生活的生動素材。馬克思認真閱讀了《古代社會》,并作了翔實的讀書筆記。恩格斯接手了馬克思積累的素材,寫出了唯物史觀開創性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按照恩格斯的研究,人類社會群體的認同是沿著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聯盟、民族、國家這樣的脈絡發展起來的,群體的認同方式也是從血緣認同到地緣認同、文化認同的演進,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在氏族認同時代,就像恩格斯所說:“勞動越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越受限制,社會制度就越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系的支配。”到了階級社會,“這種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權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確實被打破了。”① 此時“相鄰的各部落的單純聯盟,已經由這些部落融合為單一的民族所替代了,產生了凌駕于各個部落和氏族的法的習慣之上的雅典普遍適用的民族法。”② 人類進入了階級社會,出現了私有制,出現了剝削,人類的群體劃分的依據不再主要是血緣氏族,而是依財產多少來劃分階級。統治階級為了抹殺階級剝削,開始推動地緣認同和文化認同,通過向不同地域和異文化的擴張,來緩解階級矛盾,此時民族便走上了歷史的舞臺。在存在私有制的社會里,國家就是有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工具。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③恩格斯的研究表明,待到人類消滅了私有制和剝削制度,國家將隨即消亡,人類認同將進入無群體差異的狀態,也就是世界實現了大同。
中國文化起源與西方發展環境的不同,中國的人類認同方式比歐洲模式多出了一個環節——民族共同體認同。正如錢穆所說:“希臘有民族,無國家;羅馬有帝國,而帝國之內不能摶成一民族。近代西方依然還不能走上理想的民族國家之正路。依然是希臘市府與羅馬帝國之拼湊。整個西方,還是民族與國家之四分五裂,支離破碎。只有中國及早完成了‘民族國家之體制,即由一個民族來創建一個國家,由一個國家來摶成一個民族之體制。”④ 這一民族,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也稱作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發端于農耕文化,是一種包容性的文化,與發源于游牧、商業的西方排他性文化存在著明顯的分野,西方文化認同最高只能達到民族層面,而中國文化的包容性認同則可以超越民族,達到民族共同體的層面,進而建立中華民族共同體。
馬克思生產力理論構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學科理論
西方共同體研究中的國家維度
霍布斯的國家理論認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趨利避害即自我保存是支配人類行為的基本法則,善惡并無固定標準,全然是以是否符合人的自我保存為前提。在國家出現以前,那時的人處在一種“自然狀態”,而這種狀態的特點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為了擺脫這種惡劣的局面,人類需要一個大于一切人的權力的公共權力做自然法的后盾,這樣才能震懾住人們無限的欲望,使人們的安全得到保障。而這個公共權力就是國家。① 盧梭的國家理論認為,人類曾處在自然狀態之中,那里人人都是平等和自由的,那時人們都具有原始的、高尚的德行,并不存在什么“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只是由于私有制,才出現了人們的種種紛爭,為了避免紛爭,才產生了國家。而國家是人民自愿戴上的枷鎖。他還說出了一句振聾發聵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要尋找出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個人的共同力量來維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并且由于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體與全體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樣自由。”② 盧梭發現了私有制對既有人類共同體的解構與重建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又是他的局限性。
黑格爾的國家理論認為:人生來就已經是國家的公民,任何人不得任意脫離國家。“生活于國家中,乃為人的理性所規定,縱使國家尚未存在,建立國家的理性要求卻已存在……所以國家絕非建立在契約之上,生存于國家之中,對每個人來說是絕對必要的。”國家存在的理由,是人們可以實現實體性的自由。他認為: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是作為顯示出來的、自知的實體性意志的倫理精神,這種倫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所知道的,而且只是完成它所知道的;③ 國家是一個“行走在陸地上的神”。這是一種典型的唯心史觀。
總之,西方觀察人類共同體演進的視角脫離了唯物史觀,體現為唯心式的發展指導思想,也就徹底放棄了對人類群體發展真正動力的研究。
中國的民族共同體理論
用歷史唯物主義縱觀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史,我們會發現,影響人類經濟發展的核心因素大體有三:分工、規模與范圍、創新,它們在不同維度上影響經濟的發展。④ 作為經濟發展的人類共同體支撐,我國的民族共同體也在生產力的進步中不斷發展出來。
分工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費孝通教授認為:“把游牧民族看成可以單獨靠牧業生產的觀點是不全面的”,“他們所要的糧食、紡織品、金屬工具和茶及酒等飲料,除了他們在大小綠洲里建立一些農業基地和手工業據點外,主要是取自于農區”,“因而后來把農牧區之間的貿易稱為‘馬絹互市和‘茶馬互市”。① 正是這種分工促成了中國農耕部分與游牧部分的統一,共同建立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規模和范圍加速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歷史學家許倬云認為:“中國內部沒有分裂為若干獨立國,其緣故一則在文化的凝聚力,一則在全國性經濟交換網繼續的擴展,不斷將全國吸入一個整合的經濟結構。然而各地區域的地理特色及其在全國政治與經濟體系上的相對地位,終究會造成若干區域性的分歧,從而影響若干歷史事件的發生及發展過程”,“在空間平面上,中國的各個部分,由于若干中心地區,放射為樹枝形的連線,樹枝的枝柯,又因接觸日益頻繁,編織成一個有綱有目的網絡體系。幾個地區的網絡體系,逐漸因體系的擴大,終于連接重疊,成為更龐大的體系。”② 從文化維度來分析,需要超越民族的人類共同體,形成了規模范圍更大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中華民族共同體之所以能夠形成與鞏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華民族的創新基因。錢穆認為,世界主要是游牧文明、商業文明和農耕文明三種文明形態,前兩種文明都崇尚戰爭,依靠武力奪得自己的生產生活資料,后一種文明不具有掠奪土地的條件,只有依靠自身對土地的持續投入才能發展農業經濟,進而形成了農耕民族的創新基因。歷史經驗也證明了我們的判斷,比如建于公元前3世紀的都江堰,就是很好的佐證。在都江堰工程建設以前,成都平原是一個經常發生洪澇災害的地區,為了爭奪良好的生存環境,平原各部落間經常發生沖突;都江堰工程建成以后,成都平原變成了一個水旱由人的區域,部落間的關系也由競爭關系變成了合作關系,久而久之就結成統一的人類共同體,并最終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
我們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研究發現,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鑄成,都是生產力進步的結果,只有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高度,才要求人類共同體也必須發展出一個新的方式并與發展了的生產力相匹配,才能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我們研究中華民族共同體,就是要研究人類共同體與生產力發展的匹配問題。按照馬克思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的論述,作為生產關系集中反映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也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影響,并將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而不斷發展壯大。除此以外,生產方式又是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人與自然界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體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斷密切,人與人的關系越來越緊密,表現為人類共同體規模越來越大,為了實現生產力最大限度的發展,就一定會發展到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階段。
中華民族共同體學的研究對象和分支學科
歷史學家許倬云認為:“‘中國這個共同體之內,最主要的互應變量,至少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四個方向。政治范圍內,包括政權的性質和行政的結構;經濟范圍內,包括生產方式、生產力和資源分配;文化范圍內,包括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宗教組織;社會范圍內,包括社會階層、社會結構,尤其注重精英階層的作用。”①
為踐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學科化要求,我們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學的概念,它是研究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完善規律的科學,研究對象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各組成部分及其內在認同機理,研究方法是對已經存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進行歷史回顧與總結,并使之沿著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路線繼續發展。為此,建議下設經濟共同體學、政治共同體學、文化共同體學、社會共同體學等二級學科。
經濟共同體學
在歷史上,中華民族形成發展過程中,華夷秩序和朝貢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華夷秩序推動中華大地上各民族相互認同,形成了一體認同的中華民族。在華夷秩序中,有“南蠻、北狄、東夷、西戎(羌)”之說。南方蚊蟲多的地方的民族稱為“蠻”,北方帶著獵犬烤火的民族為“狄”,東方背著大弓漁獵的民族為“夷”,西方牧羊的民族為“戎(羌)”。“南蠻”為農耕民族,生產方式與華夏民族一致,經過世代交往與生產合作,較早就融為一個民族;“北狄”、“西戎”是游牧民族,雖與華夏民族采用不一樣的生產方式,但由于生產力發展要求經濟活動的規模范圍越來越大,于是兩者間產生了分工,加之不斷應對其他民族帶來的競爭與挑戰,久而久之就融為了一個民族;“東夷”為漁獵民族,遠洋時代為漁獵民族帶來了機遇,其生產力水平實現了大發展,為了容納日益發展的生產力,漁獵民族需要巨大的經濟發展腹地,進而出現了東夷與華夏民族的融合。由于經濟力量的推動,中華大地各民族實現了一體融合,中華民族共同體也就順理成章地誕生了。
政治共同體學
在政治范疇內,政權的性質和行政結構都會對人類共同體產生影響。自文明時代開始,中國的政治就一直有利于人類共同體的形成,塑造中華民族共同體就成為題中應有之意。“古代的貴族階級和封建制度,雖然在統一政府下,常不免趨向分割,必待平民社會逐漸覺醒,逐漸抬頭,始有進一步統一之需要。由春秋中葉,直到戰國末期,四百年間,平民社會各方面勢力,繼長增高,進一步的統一要求,愈來愈盛,秦始皇帝的統一,即承應此中要求而產生。”那時的政治特點是:“一、皇位世襲,象征天下一統。二、丞相輔助皇帝,為政府領袖,擔負實際行政責任,選賢與能。三、全國官吏皆由公開標準考選,最要條件是受過國家指定教育,有下級行政實際經驗。四、入仕員額,依各地戶口數平均分配。五、全國民眾,在國家法律下一律平等,納賦稅,服兵役,均由法律規定。六、國內取消貴族特殊權利,國外同化蠻夷低級文化,期求全世界更平等更和平之結合。”①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中華政治生態很早就體現出人民性、包容性的特征,能夠容納各民族進入中華民族的政治舞臺,共同締造出中華民族共同體。
文化共同體學
中國有句古話:英雄不問出處。中國人的共同體認同與西方不一樣,我們只要認同中華文化,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其他成員絕不會因為你的不同民族出身而歧視你。歷史學家陳寅恪說過:“漢人胡人之分別,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② 這樣一種包容的文化,其中一個重要的支點,就是建立越來越廣泛的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大家認同同一文化理念,在同一村社、街區、區域內和諧相處、形成社會認同。
社會共同體學
社會領域的核心問題,大體包括社會階層、社會結構和精英階層的作用。和西方不同,中國古代學者早已有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念,有了仕、工、農、商的社會排序,使社會的物質、政治、精神世界相統一,實現社會的平穩有序。這樣的社會既具有包容性,也擁有吸引性,能夠吸引各民族加入其中,共同締造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
結語
中華民族共同體學是一門源于中華大地的學科。因此,我們要提出具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底蘊的學科范式,不能照搬西方民族學理論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唯物史觀,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機結合,培育出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學,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編輯 宋斌斌 尚鳴)
① 習近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推進新時代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求是》,2024年第3期。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106-107頁。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2頁。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3頁。
④ 錢穆:《文化學大義》,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44頁。
① 參見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3頁。
② 參見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8頁。
③ 參見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62頁。
④ 參見李曦輝:《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經濟學體系構建》,《經濟研究》,2023年第7期。
① 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
② 許倬云:《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序言第7-8頁、第136-137頁。
① 許倬云:《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復雜共同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06-207頁。
①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95、104-105、107頁。
②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第2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