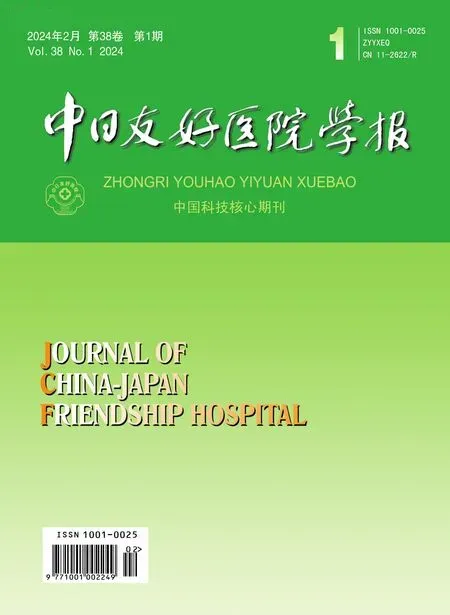腸造口患者社會疏離狀況評估及干預研究進展
喬 楠,張 也,張少華
(1.中日友好醫院 普外科,北京 100029;2.中日友好醫院 日間病房,北京100029)
腸造口是治療結直腸癌、炎性腸病、腸梗阻、腸外傷等疾病的常見術式[1]。由于腫瘤病情與腸造口的特殊性,一半以上的造口患者遇到心理社會問題,如自卑感、病恥感和社交焦慮,出現自我封閉,拒絕社交等社會疏離行為[2,3]。社會疏離是指個體因各種原因對社會行為的潛在影響而產生一種自我疏遠和疏離的心理和行為表現,包含主觀感受(孤獨、無助等負性情緒體驗)和客觀行為(社交回避、社交范圍減少等)[4]。而逐漸剝奪社會化是一種強大的慢性應激源,不僅會產生心理、精神異常,損害認知功能,出現社會認知缺陷[5],也會影響癌癥的復發和長期生存率,增加家庭及社會負擔[6]。本文對腸造口患者社會疏離感動態變化軌跡、影響因素、預防和干預措施等方面進行綜述。
1 腸造口患者社會疏離評估工具
1.1 主觀社會疏離量表
目前臨床上多采用Jessor 等[7]研制的一般社會疏離量表測量個體的孤立感及參與活動的不確定感。量表包含懷疑感、無意義感、自我疏離感、他人疏離感4 個維度,共15 個條目,采用Likert4 分計分法,總分越高提示社會疏離水平越高。2022年王文等[8]根據理論模型針對結直腸癌幸存者編制結直腸癌幸存者社會疏離測評量表,包含社會性疏離及情感性疏離2個維度,共16個條目。
1.2 客觀社會疏離量表
Lubben 社會網絡量表是根據Berkman 社會網絡指數為臨床評估而研發的,目前包含原始版本LSNS-10、修訂版本LSNS-R、擴展版本LSNS-18 和簡化版本LSNS-6[9]。LSNS-6 應用最為廣泛,包含家庭網絡和朋友網絡2 個維度,共6 個條目,每個項目采用Likert5 分計分法,每個分量表低于6分則代表家庭或朋友隔離[10]。
1.3 間接量化社會疏離感量表
1.3.1 社會影響量表
社會影響量表(social impact scale,SIS)由Fife 在2000 年研制,Pan 等[11]于2007 年進行漢化。中文版SIS 在評估社會疏離方面具有出色的應用,包括4 個維度,即社會排斥(9 個條目)、經濟歧視(3 個條目)、內在羞恥感(5 個條目)和社會隔離(7個條目)[12]。
1.3.2 孤獨量表
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孤獨量表(UCLA)[13]、癌癥孤獨量表[14]、De Jong Gierveld 孤獨量表[15]等經漢化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能間接反映患者社會疏離情況。
2 腸造口患者社會疏離現狀及動態變化軌跡分析
2.1 腸造口患者社會疏離現狀
目前尚無直接評估腸造口患者社會疏離水平的研究,多數通過社會支持、社會影響、社會心理適應間接測量。有研究表明結直腸癌腸造口患者社會疏離感明顯高于結直腸癌未留置造口患者[16]和其他癌癥幸存者[17],并處在較高水平。腸造口患者由于癌癥及造口的雙重打擊多呈現自我主動社會疏離行為[18],其中在負性情緒增加、社交焦慮、重返工作困難方面表現最為明顯,王玉平等[19]研究表明36.59%的患者減少跟其他家庭成員及社會接觸,很少參加集體活動,12.80%的患者則從來不進行家庭以外的活動。另一項研究指出44%造口患者產生病恥感、孤獨、屈服等負性情緒,受到來自他人的不理解甚至是排斥而出現社會回避和社交恐懼[20]。有報道顯示雖有2/3 患者重返工作崗位[21],但國內外研究顯示腸造口患者工作適應性情況普遍較差[22,23]。
2.2 腸造口患者社會疏離感變化軌跡分析
腸造口患者的心理變化是復雜的,動態的。一項多中心研究發現術后早期社會疏離感較高,社會心理適應能力較差[24]。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疏離感逐漸下降,變化規律基本上呈“緩梯式”下降趨勢,這與造口患者對生活質量變化趨勢[25]及對造口接受度軌跡及角色功能轉變軌跡基本相符[26,27],并呈現動態化。有研究顯示在術后3 個月內疏離感達到最高水平[28,18],另有研究表明疏離水平最高峰在術后6個月[29],此差異可能與研究對象所在地域、樣本量及研究對象年齡差異有關。在出院過渡期甚至術后1 年內社會疏離感最強這項結果國內外研究具有一致性[30]。研究發現癌癥幸存者的孤獨感隨著時間而遞增[31],原因可能為治療早期患者的社會支持有所增加,這種支持會隨著治療的結束而逐漸瓦解,導致患者孤獨感增加。在術后6個月內若社會參與下降,不能重返工作和社會活動,社會融合幾率將渺茫。
3 腸造口患者社會疏離影響因素
3.1 人口學因素
人口學因素包括年齡、性別、文化程度、主要照顧者等。與其他癌癥幸存者社會疏離研究[32]不同的是,腸造口患者社會疏離在以父母為主要照顧者的青壯年患者和獨居患者中較為常見,其次是照顧者為配偶的中年人群,再次是照顧者為子女的老年群體[33,34]。女性患者社會疏離感高于男性。文化程度高的患者能夠利用相關資源參與社會活動[28],因此社會疏離感低于文化程度低的患者。
3.2 造口類型
不同類型造口對患者社會疏離的影響研究結果存在著明顯差異。王芬等[35]研究發現臨時性造口患者的社會疏離感評分高于永久性造口患者。而另一項橫斷面研究則表明[36]永久性造口患者社會疏離、社會排斥和內在羞恥感是高于預防性造口患者的。
3.3 負性心理特征的中介作用
腸造口患者負性心理在社會疏離之間起著重要的鏈式中介作用[37],即包含對社會疏離的直接作用,也包含間接影響作用。負性思維在患者腦海中閃現頻次越多,患者感知到的負性心理,如反芻思維、自我隱瞞、逃避、病恥感、屈服心理則越大。研究顯示[38]反芻心理對孤獨感具有間接的負效應,長此以往,自我封閉,脫離社會。自我隱瞞心理在病恥感和社交回避間起中介作用[39],自我隱瞞與他們試圖忘記并對抗應激源有著內在的聯系,患者內在的羞恥希望隱瞞自己的疾病,逃避不必要的傷害,社交減少使社會疏離更加明顯[24]。
3.4 社會因素
經濟負擔、社會歧視、社會支持不足等會導致造口患者社會疏離的發生。造口患者面臨著較重的經濟壓力,經濟結構差距必然會導致社會排斥,產生社會疏離[40]。由于對癌癥的錯誤認知使患者容易產生被歧視感而社交退縮,加之造口的存在,被歧視感知更為強烈,患者孤獨感愈加強烈,難以融入社會。社會支持指來自社會或家庭等方面的情感和物質的支持和鼓勵。研究表明[2]造口患者對身體的感知是與同伴相平行的,良好的社會支持使患者相信他們受到關愛、尊重并屬于一個社交網絡,與社會疏離呈負相關[33]。因此健全家庭、社會支持方案對減少造口患者社會疏離、提升生活質量具有重要意義[4]。
4 預防和干預措施
4.1 完善出院準備,加強社交意愿
造口患者良好的出院準備對預防術后社會疏離具有重要作用[41]。入院時需評估患者需求、教育程度、認知水平;圍術期充分宣教;預出院至出院期間準確預測回歸社會生理、心理,制訂造口護理及康復計劃;同時加強出院患者延續護理,包括電話隨訪、家庭訪視、造口門診、移動社交平臺等形式,提高造口患者自我效能[42],進而減少造口對自身的限制,做好重返工作的準備,增加重返社會的意愿和信心,降低社會疏離感。
4.2 及時心理干預,再建社交信心
患者在治療及攜帶造口生活過程中會產生一系列負性心理。針對患者不同程度的心理變化,制訂心理指導方案,提高社會心理適應水平,幫助患者回歸社會十分重要。護理人員可采用漸進式訪談與患者共情[43],術后1 星期內建立訪談關系,術后第2 個星期了解其社交煩惱,對缺乏自信者,采用敘事療法幫助患者建立社交自信感,改善其社會關系[44]。對存在無助感、自尊心下降者,采用尊嚴療法減輕患者心理負擔,提升尊嚴水平[45]。術后1個月,根據改善情況制訂個體化疏導方案,提高心理韌性,改變負性情緒,最終提高社會心理適應水平。
4.3 構建支持網絡,鼓勵主動社交
改善公眾認知,構建社會環境支持體系。呼吁社會關愛和幫助造口病人,營建支持性社會工作環境[46],促進其早日回歸社會工作。出院后加強家庭成員及同伴造口知識教育,使病人更容易接受造口,緩解壓力,對回歸社會有積極作用[47]。構建醫院-社區-家庭三聯支持網絡,該體系能有效提高患者健康信息獲得效果[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