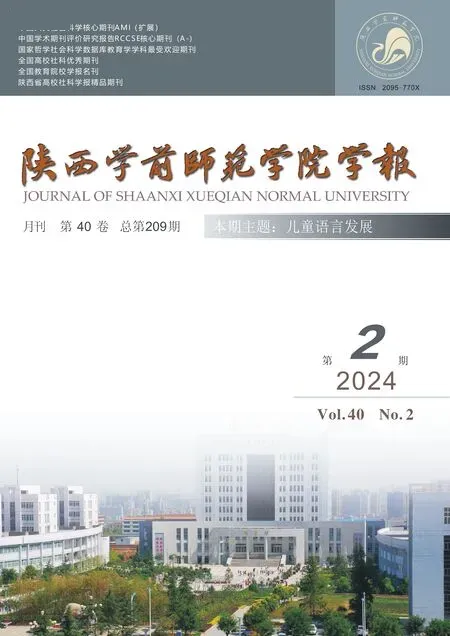“制造”傳統:早期中國胎教起源考
李鵬舉
(陜西學前師范學院幼兒教育學院,陜西西安 710100)
一、問題提出:中國古代胎教傳統真的起源于周王室嗎?
根據《辭海》的解釋:古人認為,胎兒在母體中,能夠受孕婦的言行的感化,所以孕婦必須謹守禮儀,給胎兒以良好的影響,叫做胎教①。與現代胎教觀念不同的是,中國古代胎教實施的對象不是胎兒,而是懷孕的母親,通過從視聽言動、飲食起居等日常禮儀方面對孕婦施教,以生育形容端正、秉性良善的嬰孩,故又稱之為“母教”。有賢母則有賢子,母子之間這種相應關系使得胎教自西漢伊始一直作為兒童教育的起點,為歷代儒生所重,是傳統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一歷史傳統的形成,則要追溯至早期中國的商周之際,根據劉向《列女傳》中的記載,早在太任(周文王之母)時期,周王室中就有了胎教的實踐傳統②。
近代教育史學科建設以來,學者們普遍接受這一觀點,并在各類教材中將之知識化。在教育史上最先明確這一點的,是清末的黃紹箕(1854—1908)。他在《中國教育史》③中寫道:“周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為妃。太任之性,敦一誠莊,唯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能胎教……武王后曰邑姜,太公之女也。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獨而不倨,雖怒而不訾,胎教之謂也。言教育者,以周為盛;言周之教育,以胎教為盛。”[1]黃紹箕首次將西周的胎教之法作為學科知識納入《中國教育史》的教材之中,使得“胎教起源于西周王室”成為了教育史中的經典知識,后來者皆循此說。民國時期,陳青之在撰寫《中國教育史》時,就采信了黃紹箕的說法④。新中國成立后,教育史的分支學科,比如家庭教育史、幼兒教育史以及學前教育史等學科的教材亦沿襲此說。如,馬鏞所著的《中國家庭教育史》就曾寫道:“我國的胎教始于西周,至漢代,思想家賈誼、劉向、王充等開始總結前代胎教經驗,逐漸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胎教理論。”[2]再如,金林祥主編的《簡明中外學前教育史》也明確指出:“我國胎教歷史悠久,早在距今3000 多年前的西周時期的宮廷中就有胎教實踐。”[3]而學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杜成憲和王倫信合著的《中國幼兒教育史》:“中國古代的胎教實踐開始得很早。據史籍記載,早在3000 多年前,周文王的母親太任在妊娠文王期間,‘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列女傳》卷一)”[4]36除教材外,近四十年來凡是涉及胎教起源的研究,“理重事復,遞相模效”,也都一致地追溯到周太任時期,毫無新意⑤。比如,在最近的研究中,劉秀霞在其博士論文中指出:“文王之母太任為生母的典范,她端一誠莊,日常生活中極為注重提升自我德行,懷孕進行胎教時,‘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母儀傳》)。”[5]蔡晴認為:“(西周)太任的胎教實踐已具備‘正禮’的雛形,并已成為后世的范本。”[6]
綜合來看,中國古代的胎教研究涉及到歷史學、文學、教育史、兒童史等多個領域,已有研究普遍把胎教的起源追溯至西周王室,而支撐性史料主要集中在賈誼的《新書·胎教》,戴德的《大戴禮記·保傅篇》和劉向的《列女傳·周室三母傳》。這三份文獻中記載了周文王母親和成王母親胎教的事例,常常作為典范性知識,被已有研究頻繁地征引。但這些文獻的記載是否真實?學界至今并沒有學者提出過質疑。縱觀這些史籍成書的年代,皆為西漢時期,由此,“胎教源于周王室”的說法最早源于漢代。但奇怪的是,漢代所言周室胎教之情形并不能夠在先秦文獻(包括傳世文獻、出土簡帛、甲骨文以及青銅器銘文)中找到相同性質的證據支持。如果周王室確如漢儒所言實施過胎教,那么漢代的儒生又是如何知曉這一歷史的?換言之,西漢文獻中關于周王室胎教的記載到底是歷史真實抑或是人為杜撰?為了解答這一問題,則需要借助歷史文獻學的方法對這些史料的真偽進行考證。
早在民國時,馮友蘭先生就提出古史研究三類趨勢,即“信古”“疑古”和“釋古”,馮先生的立場是放棄信古,重視史料的審查,多做疑古和釋古的工作[7]。而古史辨派歷史學者楊寬(1914-2005)又在此基礎上把我國古史研究歸納為四個派別:信古、疑古、考古和釋古,他認為除信古一派外,其余都持之有故,言之有理,主張上溯史料來源真偽乃治史最先必經之步驟[8]1-2。古史辨派提出對古代的傳說、故事以及相關史料必須抱有懷疑的態度,不可盲目采信,須認真細密考辨其來源真偽,并將其作為治史的前提和基本方法,古史辨派的這一主張有著深厚的歷史傳統,也得到了當今史學界的普遍認可。即便是作為其對立的學派,主張“走出疑古時代”的李學勤,雖然對“古”的態度與之不同,但在疑古思維和方法論上同樣主張要利用考古發現及出土簡帛等實物證據對清代以來的“疑古”成果做第二次的反思,這本身就是另一個層面疑古精神的體現,并不是簡單的“信古”[9]。日本學者谷中信一詳細考察了中日兩國疑古主義的歷史,也總結道:“那種僅僅因為傳承古老就堅信不疑是愚昧的,必須辨析真偽,甄別傳承的內容。”[10]可見,抱著基本的懷疑態度而對史料的真偽進行嚴密細致的考辨,早已成為國內外研究中國古史的廣泛共識。
具體到胎教起源這一微觀領域,一方面由于自身的視角和研究對象的限制,胎教問題一直未曾走入歷史研究者的視野之中,歷史學家并未對胎教起源的古史進行過考證。另一方面,教育史、兒童史的研究雖然一直重視胎教在童蒙教育中的突出地位,胎教問題作為兒童早期教育中的經典問題也不乏有學者發文探討,但他們卻普遍缺乏歷史研究的疑古精神和文獻考證方法。因此,近百年來胎教溯源問題一直處于停滯的狀態,長期以來陷入盲信古人的窠臼之中,不能跳脫出來對案造舊說做科學的批判。故,亟需歷史研究與兒童史研究相結合,以突破該問題的瓶頸,為新知識的建立打下堅實的文獻基礎。
基于此,作為一項跨學科的研究,本研究秉持歷史研究的疑古精神,借由文獻考證的傳統方法,對胎教起源的相關史料進行考證⑥。通過對漢代記載西周王室胎教的古史材料的真偽進行考辨,從而揭示中國古代胎教起源的真相,重建胎教起源的知識基礎。研究的具體思路分為以下兩步:第一步先通過胎教內容的異同進行系統性比較,對言“西周王室胎教”的三份漢代文獻的關系進行考察,辨析它們內在的因襲關系,進而找出源頭性文獻;第二步,從文獻出處和內容等方面對該源頭性史料的真偽進行考證,從而解開中國古代胎教起源的謎團。
二、早期中國胎教起源的相關史料間關系考
在已有的研究中,凡是主張“胎教始于西周王室”的,其所引征的史料概有三份:《新書·胎教》《大戴禮記·保傅篇》以及《列女傳·周室三母傳》。但已有研究皆未曾關注到這三份史料之間的因循關系,而是全部將其視為平行關系不加區分地予以引用,對史料之間的內在關系缺乏細致深入的辨析是制約理清胎教起源問題的關鍵步驟,也是已有研究普遍存在的根本性問題。從內容上看,這三份漢代史料共同的核心在于“正禮胎教”,部分文獻間甚至在用詞上都存在大量雷同的情況,其因循關系是顯而易見的。那這三份史料的源頭性材料是什么?記載“西周王室胎教”這一“史實”最早出自哪個文獻?對這一問題的考證將有助于我們理清“胎教源于周王室”的史料基礎,進而確立胎教起源的史實原型。茲下將對這三份史料從內容方面進行兩兩比照,以文獻互證的方式理清胎教起源相關史料之間的因循關系。
(一)《大戴禮記·保傅》與《新書·胎教》關系考
《大戴禮記·保傅篇》和《新書·胎教》在內容上極為相似,都記載了周成王之母胎教的情形,且表述也基本相同。既然二者內容雷同,則必然存在因襲關系,究竟是誰“抄襲”了誰呢?目前為止,教育史的研究皆未關涉到這一問題,在教育史的研究領域中這仍然是一個亟需指出的新問題。但是,中國傳統學術中版本、校勘、訓詁,乃至近代思想史等諸多領域對此有過長期且系統的考證,并形成了統一的認識,以下茲引試對該問題作一徹底的澄清。
近代儒學大家徐復觀先生(1903—1982)在《兩漢思想史》中就曾指出:“在南梁時劉昭注司馬彪《續漢書》中之《百官志》中就已明確《大戴禮記·保傅篇》系取自《新書·胎教》,在‘太傅上公一人’條下引自‘賈生日,天子不逾于先圣之德’起,至‘此少保之責也’止,皆見于《傅職》篇,僅文字稍有裁省。由此可以證知《大戴記》系取自《新書》,而非《大戴記》取自《新書》。”[11從徐復觀先生的引征可知,早在南梁時期就有學者辨明二者的因循關系了。清代著名經學家孔廣森(1751-1786)在其版本、校勘及訓詁的集大成著作《大戴禮記補注》中同樣明確指出過該問題:“《保傅第四十八》取賈子書《保傅》《傅職》《容經》《胎教》四篇。”[12]清末的經學研究進一步明確指出,《大戴禮記·保傅篇》就是將賈誼《新書》中《保傅》《傅職》《容經》《胎教》四篇合而為一。建國后,專門研究賈誼思想的學者也多指出過這一問題,其中有代表性當屬王興國的《賈誼評傳》,該書談到此問題也明確說過:“《大戴禮記·保傅篇》中有關胎教的內容,不過是賈誼此文之移植。”[13]這里的“此文”,書中指的就是賈誼的《新書·胎教》。
由上可知,《大戴禮記·保傅》與《新書·胎教》的關系在傳統經學和近代思想史中早已明確,諸多的歷史研究相互印證,二者的因襲關系是清楚無疑的,《大戴禮記·保傅》中的成王之母的胎教事例完全是從《新書·胎教》抄錄而來的,因此,中國古代胎教溯源的研究就再無引用《大戴禮記·保傅》的必要了。但由于對二者之間的關系缺乏基本的認識,在當前教育史中引用《大戴禮記·保傅》的研究仍然大量存在,很多現行的學前(幼兒)教育史的教材中亦是如此。
(二)《新書·胎教》與《列女傳·周室三母傳》關系考
從上面學術史追溯已經明了,《大戴禮記·保傅篇》中的胎教內容全部抄自《新書·胎教》,因此,胎教的史料溯源便沒有考慮《大戴禮記·保傅篇》的必要了,只需考證《列女傳·周室三母傳》和《新書·胎教》之間的關系即可確定源頭性史料了。這兩篇文獻分別記載了周文王、成王之母胎教的事例,從“事件”發生的歷史來看,文王之母實施胎教的時間自然是早于成王之母的,但吊詭的是,從著作發生的年代看,賈誼的《新書》卻是早于劉向的《列女傳》的。這里就隱藏著一個矛盾:文王、成王之母胎教“故事”發生的時間先后與記載這些“故事”著作的先后是不一致的,即,時間線上在前的文王之母胎教的“故事”,相比于成王之母的胎教“故事”來說,其實是后出的。這種“后來居上”的古史現象該如何理解?又該如何考證它們之間的關系?
古史辨派歷史學家顧頡剛(1893-1980)創造性地提出了“層累的造成的古史說”這一理論框架可以很好地解釋這種“時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的現象[14]。他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提出這一理論,并提出“歷史演進的方法”來考證、還原古史傳說層累演變的真相。胡澠(1994)準確地將“層累的造成的古史”放入史料學范疇,也即是文獻學范疇,把史料辨偽作為歷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礎[15]。顧頡剛將這種方法表述為:“凡是一件史事,應當看它最先是怎樣的,以后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的。”[16]59后來,胡適(1891—1962)又把這種考辨古史傳說演變的方法具體分為四個步驟:“(1)把每一事之種種傳說,依先后出現次序排比;(2)研究此一事在每個時代有如何之傳說;(3)探索此一事漸次演變之跡象;(4)遇可能時,解釋其每次演變之原因。”[8]34顧頡剛先生提出的理論框架與方法論對于中國古史考證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下文將沿著這一學術理路對后出現的文王之母胎教古史傳說的演變進行分析與解構,深入剖析劉向創作這一歷史“故事”的演變軌跡,并與賈誼所記的成王之母的胎教事例進行比對考察,從而揭示二者隱含的內在因循關系。《列女傳·周室三母傳》中胎教內容茲引于下:
“①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②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③溲于豕牢而生文王。④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16]14
《列女傳》中的故事,總體上是在《詩經》《尚書》等先秦典籍中所記載賢妃貞婦的事跡的基礎上,進行一定藝術加工創作而成的。這一點《漢書·楚元王傳》已經點明:“(向)故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17]403《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序也可為證:“又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可見,劉向的《列女傳》是二次創作而成的,在傳統學術中并不被視為“正史”。
文王之母的胎教事例完全體現了《列女傳》創作的基本理路。首先,材料①點明了文王和太任的母子關系,而這段話就取自于《詩經·大雅·思齊》:“思齊大任,文王之母。”和《詩經·大雅·文王》:“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18]通過比對發現,二者文義相等,部分文辭相同,比如“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摯仲氏任”“維德之行”等語句基本相同。可見,劉向文王之母胎教的故事正是圍繞《文王》《思齊》為基礎展開的。《詩經》中雖明確說了太任生育文王這一事實,但卻沒有提及生產過程中的細節,而材料③說溲于豕牢而生文王,即太任在上廁所小便的時候生下了文王,這是不見于《詩經》整書的。那劉向的這一說法又來自哪里?查閱史料發現,此細節系取材于《國語·晉語四》中的記載:“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19]428二者對比可見,“溲于豕牢”的細節是晉文公時期晉國大夫胥臣聽聞而來的,至于從何而聞,則無從考證。從胥臣的表述中,這一細節并無任何史料的支持,僅僅是“聽說”,因此,也就初步具備了故事的傳奇色彩了。從《詩經》到《國語》的過程中,太任嫁于王季并在廁所誕下文王的“歷史”就被建構出來了。但是,《詩經》《國語》非但沒有提及太任胎教的任何情況,《國語》中胥臣舉太任生文王的例子反而是意在闡明外在教化的無用⑦。胥臣認為,一個人的德行取決于先天的“質”,而非后天的“教育”,“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19]429胥臣明確說到,文王“在母不憂”這樣賢良的德行是天命使然,而非后天的教誨之力所致。而劉向卻說“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這豈不是與《國語》中胥臣的教育觀念相悖嗎?那劉向的這種胎教觀念又源于哪里?綜合②④的內容可知,劉向所說的“胎教”是要求孕婦在坐、立、視、聽、言談、飲食等方面符合禮的要求,核心在于“正”,即“正禮”,也即是遵循儒家禮儀,這與賈誼提出的“正禮胎教”是完全一致的。除了胎教思想相同外,從文辭內容來看,②④材料中的胎教表述與賈誼的“立而不蹕,坐而不差,雖怒不罵、所聽聲音要合于禮樂,所求飲食符合正味,”[20]329-332對比可見,二者文字表述也基本一致。可見,劉向談文王之母胎教的內容是來自賈誼的,他把賈誼所述成王之母胎教的做法隱蔽地移植到文王之母的身上,創作了文王之母胎教的“史實”。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揭示文王之母胎教“古史”的歷史演變軌跡:首先,西周時期為該故事的原型時期,《詩經》《尚書》《逸周書》等史料中多次提及太任與文王的關系以及太任的賢德,各類文獻表述一致,這一時期所顯示的太任和文王的母子關系是確定的史實。但西周的史料中普遍沒有任何具體生產過程細節的記載,這一點也是確定的;其次,到了春秋時期,從《國語》中“臣聞昔者”(聽說古時候)的表述中,史實出現第一次變化,開始走向傳奇化、故事化。胥臣加入“溲于豕牢”“在母不憂”等情節,不但進一步充實了既有史實,還使得其開始帶有一定的傳奇色彩。但胥臣講述這些細節的本意是闡明一個人賢良與否根本上取決于先天的“質”,外在的“教”只能增益其質。很明顯,這與漢代的正禮胎教觀念,即通過對孕婦正禮教化就能生育賢良資質的嬰孩,是相矛盾的,換句話說,在春秋時期這種胎教觀念并未形成;最后,到了漢代,劉向在西周到春秋時期層累的文王之母生產的故事基礎上,加入賈誼“正禮胎教”的觀念,形成了完整的文王之母胎教的故事。因此,《列女傳·周室三母傳》中文王之母胎教內容其實是基于《新書·胎教》改編而成的。
綜上,通過漢代有關“胎教”起源三份文獻關系的考證可知,言“周王室胎教”的源頭性文獻實為賈誼的《新書·胎教》,最早的“史實”則是周成王之母胎教的事例。那西漢的賈誼是如何知悉西周王室胎教細節的?賈誼所憑據的史料又是什么?這些史料又是否真實可信?圍繞這些問題,以下茲將進一步考證。
三、早期中國胎教原型考
上文證知,成王之母的胎教事例最早出自賈誼的《新書·胎教》,共有兩段文字,茲下全引: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
“此正禮胎教也。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獨處不倨,雖怒不罵,胎教之謂也。”[20]329-332
綜合兩段材料的內容來看,周妃后妊成王時的胎教事例來自于“青史子之《記》”,漢書中稱“青史子”。杜成憲等人已經指出:“賈誼的《胎教》……通過古代文獻所記載的周代后妃和有關官員進行胎教的具體事例,說明胎教的實施。”[4]37這里,杜成憲等學者談到的“古代文獻”,無疑就是《青史子》了,而“有關官員”就是《青史子》中提到的“太史”“太卜”和“太宰”。那《青史子》中的記載又是否可信?下文將綜合使用目錄、辨偽等文獻學的已有研究成果和方法對《青史子》一書的寫作年代與真偽進行考辨,從而厘清成王之母胎教的真相。
(一)《青史子》的著作年代及真實性考辨
《青史子》原書五十七篇最早見于《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位列諸子略中的小說家這個門類之下,該書于隋朝亡佚⑧。目前,最為可信的仍是《漢志》本身。由于《青史子》屬于小說家,班固對其出處以及性質有過簡短的說明: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17]
班固認為小說家皆出于“稗官”,顏師古注“稗官,小官”。從現有研究看,“稗官”身份混雜,主要包括兩類人:一類是“秦漢時縣、都官之屬吏,具體秩次在百六十石以下,是所謂的“少吏”階層,處于整個官僚系統的最基層”[21];另一類是秦漢時期的方士待詔或侍郎[22]。但不管是哪一類人,這些小說的性質總體上是淺薄荒誕的,班固對其評語多是“其語淺薄,似依托也”“其言非殷時,皆依托也”“迂誕依托”等。小說所記載的內容“為街談巷語,道聽涂說者造也。”即來自于街談巷尾普通人的閑言碎語,即“普通的民間議論和傳說”[22]。郭麗的研究顯示,這些小說反映了“依附于道家而又雜糅儒、道、方士文化,應是漢代黃老之學和新儒學影響下的產物,是漢代大規模制度、文化建設催生的不合經藝之作。”[23]因此,整體可信度不高,用在班固在大序中的話說就是“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而第十家小說家則為閭里的“狂夫之議”,不可做信史視之,這顯然代表了漢儒的共識。今人的研究大多支持這一看法,比如盧世華的研究就認為,“小說家對統治者及其臣工的參考價值很小,卻受野民、市井喜愛。所以,就理論意義和治國參考來說,當然是不可觀的。”[24]
另一方面,具體到《青史子》而言,班固注“古史官記事也”,由于講的比較模糊,再加上原著早已佚失,作者真實姓名及生平均不可考。后世對青史子的身份猜測很多,但基本難有實證。比如,南宋鄭樵《通志·氏族略》、清周壽昌《漢書注校補》皆引東晉賈執《姓氏英賢錄》云:“晉太史董狐之子受封青史之田,因氏焉。”[25]據此猜測青史子是春秋時晉國太史董狐之子,今人李零亦持此說⑨。但此說并無確鑿史證,今人對其批判良多。比如王濟州的研究就指出:“然遍查先秦典籍,并無相關記載。漢應劭《風俗通義姓氏篇》、南朝何承天《姓苑》、王僧孺《百家譜》亦不見記載,不知賈執何據。”[26]再比如章太炎猜測青史子是春秋時期的左丘明:“疑《青史子》即左氏所著書,左氏故稱青史也。史之所記,大者為《春秋》,細者為小說,故青史子本古史官記事也。”[27]章太炎的懷疑同樣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因為《漢志》開篇說“昔仲尼沒而微言絕”,已明告讀者:“九流十家,皆起于孔子之后。”[28]而《論語》中孔子多次提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說明左丘明應該在孔子之前,至少是同時代的長者,孔子才可能會以其標準來標榜自己,那青史子顯然就不可能是左丘明了。目前,絕大多數研究認為《青史子》是秦漢之間的托古偽作。比如今人盧世華就認為青史子為漢代方士附會黃老之學而偽作,假托古人以自重其說[24]。而王齊洲更是對前人的考證逐一梳理,就僅存的三則內容結合南北朝時期的《青帝云門舞》提出青史子是五帝之一的青帝之史,實際上是個壓根就不存在的傳說人物[26]。王說與當前對小說的普遍認識,即小說是秦漢之間托古偽造的觀念相吻合,可備為一說。
總之,結合漢儒共識和已有關于稗官、小說家和青史子等多方面的研究,可以證知,《青史子》應該是秦漢之間的小吏(或方士)采集民間議論或傳說附會于歷史傳說人物身上而偽造的,并非出自于周王室的史官,可信度極低。
(二)職官功能視角下《青史子》真偽再辨
由于《青史子》中的胎教內容在先秦史料中并未出現過,因此,目前教育史學界尚沒有研究通過其內容進行直接考辨,下文首次嘗試從其內容中提及的“太宰”這一職官的職能在歷史中演變的角度對其成書年代進行考辨。
近日,IMF發布《財政透明度、借貸成本與外國持有主權債券》報告,以33個新興經濟體為對象,從預算過程的公開度、財政數據透明度和財政問責制三個維度,分析財政透明度對借貸成本以及國外對其主權債券需求的影響。結果顯示,財政透明度降低了各主權債券利差,提高了投資者對新興經濟體債券的配置意愿。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推動預算過程公開可以降低主權借貸成本,而財政數據的透明度則有助于提高投資者對其主權債券的需求。報告還指出,統一標準的財政數據和較高的對比便利度(尤其是資產負債表),可以便利國外投資者進行決策,增加其對新興經濟體主權債務的配置意愿。
《青史子》中有兩處提到“太宰”這一官職:“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根據北周盧辨的注解:太宰,膳夫也。再結合文義可見,《青史子》中的太宰是負責宮廷膳食的官員。這與周代太宰的職能是不相符合的。周代的太宰又稱大宰或冢宰,“《周禮》題稱為‘天官冢宰’,楊天宇題解,太宰即冢宰。”[29]據《周禮》記載:“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30]2“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30]27從《周禮》⑩來看,太宰是西周的六官之首,輔佐君王治理諸侯邦國的各類事務,地位崇高,類似后世“掌承天子,助理萬機”的丞相。到了春秋時期,太宰的職權地位有所下降,逐漸變成一般性官職。劉光的研究顯示:“春秋時期,太宰都非各國所重之職官。除少數小國之外,列國之太宰或為一般的職官,或是執政卿的泛稱。”[29]春秋時期,在少數小國中,太宰一職仍至關重要,在多數列國中太宰變成一般的卿大夫,比如劉光的研究揭示春秋時期楚人伍子胥在吳國的官職應該就是太宰。但縱使職權下降,無一例外,“太宰”一詞在先秦文獻中都沒有“膳夫”的含義,比如太宰見《春秋》經傳凡11 次,春秋金文6 次,在這17 次記載中太宰都不具備“膳夫”的含義[29]。直到秦朝建立,“太宰”才成為秦制中負責膳食的官員。據《漢書·百官公卿表第七上》記載:“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又均官、都水兩長丞,又諸廟寢園食宮令長丞,有雍太宰、太祝令丞,五畤各一尉。”[17]103這里“太宰”隸屬于九卿之一的“奉常”,根據唐顏師古的注解:太宰即是具食之官。可見,“太宰”一職只有到了秦朝時,才變成負責天子飲食及祭祀用食物供奉的官員。因此,《青史子》的寫作年代就只能在秦以后了。
通過上述“太宰”這一職官從西周到秦漢的變遷可知,《青史子》中出現的“太宰”一詞意指“膳夫”,這一職能最早出現在秦朝的官制中。由此可證,《青史子》的寫作年代只能在秦朝建立以后。這一結論和上述小說家和《青史子》的相關研究是一致的,三方可以互相印證。
綜上所述,《青史子》應當是秦漢間小說家托古擬造之作,而非西周信史,不足憑信。由此,《青史子》中所載成王之母周妃胎教的事例同樣是托古臆造的故事,“胎教源于周王室”這一經典知識自然也就沒有文獻基礎了。胎教一說本源于秦漢之間的稗官小吏收集的街談巷議,屬于下層庶人間流行的口頭傳說,荒誕不經,本不為當時正統學術所重(不可觀)。正是賈誼敏銳地發現胎教學說背后潛藏的“禮儀”價值,并做了上層階級的路徑建設,將胎教回溯至西周王室,在“三代”歷史中建立其天然的合法性,才使得胎教傳統在以儒家思想為尊的漢代社會中確立起來。
四、結語
“胎教源于周王室”在教育史、兒童史、家庭教育史、幼兒教育史、學前教育史等多個領域中早已成為確定無疑的“常識”,既有研究亦將之視為不證自明的“史實”,這就造成了長達百年的知識錯誤。這些錯誤長期以來非但沒有被察覺到,反而在各學科教材中不斷被“知識化”,形成強大的話語力量,讓后來的研究者再進入到這一領域時先入為主地將其視為定論,以至于在諸多學科內部已經完全喪失了質疑與反思的精神。事實證明,僅僅因為傳承古老就深信不疑,違背學術理性和科學精神。
從以上考證可以看出,一方面,早期中國童蒙教育文獻由于歷史悠久,傳世過程中訛謬不免增多,且造作虛偽層出,真假參半,顯示出獨特的歷史復雜性。因此,在當前蒙學或兒童史的研究時,應首重史料的真偽,綜合利用傳統學術中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訓詁學等已有理論、成果及方法,認真甄別史料的真偽,“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以確保所使用的史料的真實性。正如章太炎所言,不能辨偽,遑論求真?離開了史料真實這一前提條件,那么任何在此基礎上生發的教育論述都將變得毫無意義。“窺一斑而知全豹”,從胎教溯源這一“個案”可以看到,當今蒙學研究,乃至教育史研究中不加質疑、望“文獻”而生義,乃至按自己需要隨意解釋歷史文獻的情況仍然是廣泛存在的問題,這反映了當前學界浮躁空疏、急功近利的學風,值得所有同仁警惕。另一方面,童蒙教育與其背后的歷史思想之間表現出強烈的內在關聯性,賈誼“制造”胎教傳統的文化實踐正是基于儒家“正禮”的思想背景之上的。因此,當前童蒙教育研究在范式上應該超越以現代教育學,尤其是學校教育為基本框架解釋歷史文獻的局限。正是這種教育與歷史思想之間不可分割的內在關系,使得我們在研究古代兒童教育,乃至教育史問題時,應該摒棄現代教育學所提供的概念框架,回到特定時代的思想史背景中重新發現中國式教育的文化特質,即在思想史視角下理解中國古代兒童教育問題應該成為當前童蒙教育的基本范式。這些都為當今蒙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也對現代學前教育基本理論的建構提供了助力[31]。
[注釋]
①該定義出自舒新城等編著的《辭海》,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576 頁,它抓住古代胎教中“感應轉化”以及“禮儀”等關鍵特征,切合漢代陰陽五行氣本論的思想背景,避免使用諸如“生長發育”“科學”等現代性的概念,突出了古今胎教概念的本質性區別,是比較準確和中肯的。
②據《列女傳·周室三母傳》記載:“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溲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③1904年癸卯學制在全國實行,經學科大學和師范學堂章程中都開列有教育史課程高等學堂設有教育史課程,但當時尚無中國教育史教材,于是便有黃紹萁草創,柳詒徵輯補了《中國教育史》一書,該書是中國學者最早撰寫的中國教育史著作。據杜成憲《關于第一部<中國教育史>的幾個問題》一文考證,該書綱目是由黃紹箕制定,在其1908 年1 月死后,柳詒徵受命補其書,約在1910年完稿,而于1925年出版。
⑤張新生(1982)《略談中國古代的胎教學說》,傅榮(1987)《中國——世界最早的胎教策源地》,于貞干(1988)《胎教古說略考》,趙國權(1994)《淺析中國古代的胎教思想》,韋石(1995)《我國最早提出和實踐胎教》,賀云俠(1995)《略論我國古代胎教學說的起源和發展》,胡幸福(1997)《中國古代平民胎教略論》,柏建華(2000)《我國古代的胎教思想》,劉炎隆(2002)《中國古代胎教學說是中國教育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劉寧(2010)碩士論文《漢代母教研究》,潘帥(2014)《“正”與“氣”—中國古代胎教思想史發展史的理論追溯》,郭芳(2014)碩士論文《漢代生育禮俗研究》,殷苗苗(2014)碩士論文《漢代胎教思想的基本內容及特征》,朱慈恩(2015)《論傳統中國胎教觀念的近代嬗變》,張世萍(2018)《中國古代胎教理論的發展與經驗借鑒》,郭晶晶(2018)碩士論文《性別視角下先秦至兩漢時代的生育禮俗探究》》,韓笑(2021)碩士論文《周代育兒問題研究》等諸多研究都持中國古代胎教源于西周王室的觀點。
⑥文獻考證方法多樣,大體上可歸為兩類:一類是顧頡剛、楊寬等人采用的是傳統文獻之間綜合比對互證的方法以考證古說之真偽,這種方法是傳統考據學與近代以來的科學精神相融合的新的嘗試;另一類是王國維、李學勤等學者使用的二重證據法,即,將傳統文獻與出土文獻交互比對以進行古史重建工作。這種方法雖然更注重出土文獻在驗證古史上的重要性,但并不拒斥傳統文獻間的互證。參見李學勤《談“信古、疑古、釋古”》,《孔學堂》,2014年第1期。本研究的文獻考證工作仍以傳統文獻間的互證為主,未使用出土文獻。
⑦關于教育功用有限性的觀念在春秋時期是普遍存在的,據《國語·楚語上》記載,除晉國外,連地處中原文化之外的楚國也能看到類似的觀念:“(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日:‘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日:‘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日:‘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
⑧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西漢時期《青史子》有五十七篇,但到了南北朝時期僅剩一卷了,《隋書·經籍志》記載,梁有青史子一卷,至隋已佚。清代馬國翰依據《大戴禮記·保傅篇》等古書典籍所引的片段輯錄,為《玉函山房輯佚書》本《青史子》一卷,置于子編小說家類之下。民國時,魯迅先生也從各種舊籍的引注中也僅輯出三個片段,其中“胎教”內容也是從《大戴記》抄得,輯為《古小說鉤沉》。
⑨見李零《蘭臺萬卷:讀<漢書·藝文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116頁。
⑩《周禮》,又稱《周官》,成書年代于漢以來備受爭論,至今仍無定論。顧頡剛《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一文認為周官大部分內容成書于戰國時期,楊寬《古史微探》卷七《月令考》一文也贊同這一觀點。徐復觀《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一書則認為周官成書復雜,經歷多個歷史時期的史官編撰,并非成書于一人,可能系晉國史官系統所承編纂。盡管成書年代不確定,但研究西周歷史的學者都傾向于把它視為可信的材料,比如楊寬《西周史》、許倬云《西周史》、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