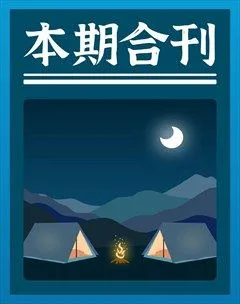朱伯丞:撥云見霧




路人、海鷗、大教堂……朱伯丞的微博中,罕見地出現了與比賽、工作無關的旅行碎片。原因無他—一今年亞運會與明年和平精英春季聯賽之間,橫亙著一條小小的時間裂縫。盡管這位職業電競選手天生“戀戰”,渴望比賽,卻也得面對近半年的空白,學會在追逐下一個職業目標之前,享受生活本身的樂趣。
自16歲起,朱伯丞便習慣將全部時間投入訓練和比賽之中。比起自己的名字,人們更熟悉他在和平精英中使用的用戶名——Paraboy傘兵。稍稍檢索,一長列的戰績緊隨其后,好像—堆漂亮的行李:18歲時取得PEL(和平精英職業聯賽)、PEC(和平精英國際冠軍杯)、PMCC(和平精英全球總決賽)冠軍大滿貫;19歲獲得電子競技獎(EsportsAwards)最佳手游選手;20歲蟬聯世界冠軍;21歲,也就是電子競技進入亞運會的這一年,他帶領隊伍為中國拿下金牌……客觀來說,朱伯丞已抵達難以逾越的職業高度,電競評論人稱他為“GOAT”,也就是人人都渴望拿下的那個“歷史最佳”。
行李雖漂亮,卻總歸是承重之物。名譽的另一面,則是“高處不勝寒”的壓力。朱伯丞承認,“之前拿了那么多成績,肯定不想因為個人狀態不好,就導致比賽成績的下滑”。
采訪恰逢亞運后恢復訓練的首日,在兩場訓練賽的間隙進行,他同我們分享首戰的成果,自我評價“還行,六局打了十個人”,緊接著輕聲滑過一句,“我其實不太能接受這個狀態”。或者說,他其實不太安心。成為職業電競選手,意味著平日嚴格的訓練,朱伯丞常年保持每天14個小時的訓練量,練習至凌晨兩三點。亞運會過后,出席活動、拍攝雜志、接受采訪,一個月五次往返成都與北京,諸多訓練外的工作襲來,這些電競領域外更廣闊的世界,他也喜歡,卻總有種不在軌道上的不踏實。
如今的電競行業中流傳著一句話:想要成為電競職業選手,天賦與努力缺—不—可。大家甚至會用“百萬里挑一的天才”來形容成為頂級職業選手的難度。
事實證明,人們對于這種“努力”的想象淺薄而貧瘠,以5月亞運會準備的集訓為例,所有人都必須遵守一套嚴苛的訓練流程,7點鐘起床,晚上11點結束訓練,一日三餐固定且統一。因為亞運版本的和平精英與常規版本存異,難度驟升,技術、戰術或思維,教練和運動員都要從頭開始學習。
十月發布的亞運會紀錄片中有這樣一幕,因為發現自己在新版本中的技術短板,以及落后于他人的可能性,朱伯丞—聲不吭地延長了訓練時間——直到其他選手晾異地發現,他的手機屏幕因大量、快速的點擊,被磨出了一塊清晰的凹陷。
是否對自己過于嚴苛?朱伯丞記得‘傷仲永的故事,那個有天賦的孩子最終反被天賦誤,“我以此警醒自己,不希望自己在哪方面落后特別多。某個部分可能并不是我的強項,但我也不希望它成為我致命的短板,我必須訓練到它相對我的長處而言并不突出,卻不會拖我后腿的程度”。亞運會選拔期間,“卷”(意為競爭)如同選手們心照不宣的暗號,早起只是最基本的一條,很多選手自覺加訓,發展到后期,教練甚至下了不允許熬夜的規定。
究其根本,這才是“電競入亞”的原因。盡管是年輕的競技門類,電子競技其實與傳統競技項目共享著同樣的內核:選手需要付出大量的訓練時間,以保持穩定的技術發揮,最終追逐勝利。
這一點,朱伯丞是在亞運村才明白的。也是在10月1日,朱伯丞帶領隊伍以44分36秒943的總成績奪得亞運會電子經濟頃目金牌的時刻,強烈的榮譽感升騰起來,他說,站上領獎臺不同于以往拿到任何聯賽的冠軍,“我確信自己在做一件很正確的事。也就是,感受到了強烈的個人價值”。
亞運的記憶像是懸浮飄渺的煙霧——亞運版本不會延續到未來聯賽,因亞運集結的隊友也相聚后離散——但它確實對朱伯丞發生著作用,就比如,之前打比賽,朱伯丞多半采用自己的一套“方法”,賽前不吃生冷辛辣食物,盡量不感冒,以防腸胃或身體不舒服導致比賽狀態不佳。亞運集訓強制的早睡早起,讓他看到身體在競技中的重要訓,如今,為了保持靈敏的技術和反應能力,他盡可能規律作息,并在長期訓練后貼肌肉貼,定期對手部肌肉做按摩。
或者說,備戰亞運的五個月,對朱伯丞而言,是一次撥云見霧的經歷。亞運會前的大半年,他所在的上海NONA戰隊表現欠佳,外界紛紛質疑這支隊伍未來的發展,身為領軍人物,朱伯丞自然也倍感壓力。“不知道該怎么凋整,也根本沒有辦法改變現狀”,他如此描述這段迷霧中的行走。
外界看來,朱伯丞的職業生涯似乎—直高歌猛進,但其實,2020年PMGC(和平精英全球總決賽)拿下職業大滿貫后的一段時間,便遭遇了第一個低谷。從那之后,“找到自己的問題,然后付出更多的訓練”,就成了朱伯丞走出低谷的訣竅。



“能知道什么東西好,什么東西不好,這種狀態算不錯,因為你已經知道問題所在,去解決和調整就好。當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時候,才是最艱難的。”話雖如此,即使因未知的迷惑障目,朱伯丞“以不變應萬變”的應對之策也是沉著的,繼續訓練,繼續下功夫,因為他堅信,物極必反,否極泰來。“一件事糟糕到了谷底,就不可能繼續糟糕下去,能做的就是等待春天到來。當然,是努力保持自己的狀態,同時等待春天,不是擺爛和放棄,那樣只會—點機會都沒有。”
他的回答,讓人想起德國新電影運動的導演之一,赫爾佐格作品中慣常塑造的人物。這些主角,面對看似難以克服的處境,以及無因的不可抗力,往往展現出強壯的意志,如若能在“陸上行舟”。
因此,朱伯丞也不忌諱談論這些經歷,“電子競技,失敗才是主旋律,不可能有人—直拿冠軍。大家看到的冠軍是積分獲勝,也許我們只會在幾個小場里獲得第一名——從另—種層面上看,其實—直都在失敗”。在他看來,電.子競技最終比拼的是失誤的多少,即技術的穩定性,而長時間的訓練,就是為了把不確定性降到最低。“不要忘記自己本身需要什么,或者是平時的基本功,越到大賽,越不需要超常發揮,只需要做自己平時在做的事,打出平時的水平。”
話頭最終還是回到了訓練。朱伯丞說,亞運后有過一陣失去目標的短暫的眩暈。他于是去學吉他,爬格子每天練,發現演奏的短板,就跟短板“死磕”——與電競訓練時如出一轍。“當然著急,但始終都想著,把自己要做的給做好,如果沒進步,就繼續做。”不過,上個月發布的吉他演奏視頻里.他已經明顯感覺,自己進步了。
土耳其旅行數日歸來,飛機落地,朱伯丞最終在微博寫下:明年要鼓起百分百的勁……我還是對自己和隊伍有信心的。輕飄飄的散漫,終究不適合這位腳踏實地的年輕人。很顯然,他對春天的來臨已迫不及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