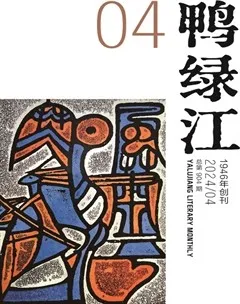獨手聯(lián)彈(短篇)
汪泉
文明路可真文明。甫一入住,便聽到鄰居家琴聲流淌,不絕于耳,還是鋼琴。畢竟是廣州的核心地帶,還有免費的鋼琴曲欣賞,整日沉浸于藝術(shù)氛圍,真是享受。我是樂盲,難為知音,但莫名喜歡。因為這種東西可有可無,聽,它起伏有致,優(yōu)雅悅?cè)耍徊宦牐簿褪莻€響動。作為一個“單身狗”,有點響動,總比沒有好,盡管我是一個極其喜歡安靜的人。有時候,我也挺煩這琴聲,偶或半夜三更,琴聲大作,將我從夢中驚醒;繼而琴曲舒緩悠揚,誘人入睡。看來這次是遇上真的藝術(shù)家了。
不久,我在一場朗誦會上邂逅了一位鋼琴教授,她叫佟琴。她是音樂學院的教授,身材窈窕,談吐雅致,舉止得當,正如一架高貴的鋼琴。我喜歡她,我們相處了很久,我們總是待在她的房間,她彈琴,我朗誦,很多時候都是即興。再后來,我們就拉上了厚厚的窗簾,不管是黑夜還是白晝,我們總是喜歡在黑暗中,我的聲音在房間走動,她的琴聲攀緣著我的朗誦,聲音彼此相擁共舞。一段時間的激情過后,再沒有找到新的相處之道。有一段時間,我們?nèi)艏慈綦x,不知道彼此關(guān)系將何去何從。我苦于這種僵持的關(guān)系。終于,我想到請她來我的寓舍,聽聽鄰家的琴聲。
佟琴進門后,我們寒暄了幾句,正當一段小小的空白檔,尷尬在即,我正想朗誦點兒什么給她,鄰居家的琴聲適時響起。我甚為得意,說:“這是我家的背景音樂,鄰居在彈鋼琴,知道你來了,演奏迎賓曲呢。”佟琴毫無表情地說:“這不是迎賓曲,是德彪西與拉威爾四手聯(lián)彈雙鋼琴作品,《六首古代墓志銘》的第二曲,《為一位無名氏的墓志銘而作》。”我驚訝于她對樂曲有如此敏銳的識別能力。
接著她問:“你鄰居夫妻都是搞音樂的嗎?”我說應(yīng)該不是,我從來未見他家里有女人,好像也是單身,至少70歲。琴說,那就是播放的樂曲,不是彈奏的。我心想,也許吧,但至少說明我的鄰居是一位音樂鑒賞水平極高的人。
我本來要說出一件事,但面對這個教授女友,沒好意思出口。那是一個夏日的傍晚,氣溫高達38℃,我下班進門,脫了上衣,光著膀子,進了廚房。正巧,鄰居也在廚房做飯,盡管他頭發(fā)幾乎全白,但他面色白皙,身材瘦削,絲毫也不顯老。我們相距不到五米,只隔著空空的天井和窗紗,讓人覺得這段距離既遠又近。他說:“你好,鄰居,我這邊有好多女人,知道嗎?”這是鄰居先生第一次跟我說話。我一聽這話,心跳加速,不知如何接話茬,裝作沒聽懂。他說的是粵語。我繼續(xù)做飯,他又說:“鄰居,聽到我說話了嗎?”我用普通話說:“您好!您是在跟我說話嗎?”我聽到他家客廳傳來鋼琴聲,清脆悅耳,聲聲將溽熱驅(qū)走不少。他說:“是的,我是在跟您說話呢!我家里有個女鋼琴師,她一絲不掛,在彈琴,你想見見她嗎?”令人驚懼的鄰居。他穿著整齊,絲毫不像在家里的樣子,似乎是在演出現(xiàn)場,我看到他的襯衣領(lǐng)口系著黑色的領(lǐng)結(jié)。我頓了頓,笑著說:“免了吧,鄰居,還是你自己受用吧!”他說:“你的穿著,有礙觀瞻!”我這才意識到自己是裸著上身的,急忙紅著臉說對不起,轉(zhuǎn)身溜出廚房,穿上背心,許久沒敢出現(xiàn)在廚房。
佟琴在我家里沒有待多長時間,只是很客套地給我解說了《古代墓志銘》表達的意境,什么幽思,什么冥界,天人對話,什么《神曲》,等等。在我聽來,這曲子和標題毫無關(guān)聯(lián),好像是一個老人在回憶,一會兒洶涌澎湃,一會兒孤獨寂寞,一會兒在傾訴內(nèi)心的私密,一會兒在評說對外界的觀感,凌亂不堪,不知所云。總之,這種東西,在你走神的時候,會引導你更走神,忽而想到一些美景,忽而回想起一些美事,還會讓人想起一些浪漫的細節(jié)和令人恐慌不安的往事。
佟琴走了,沒有沿著我設(shè)想的意圖談婚論嫁,也沒有發(fā)生什么意外。琴聲還在,不絕如縷,低回纏綿,似乎是在替我傾訴雜陳的心事。我沉浸其中,一時心緒紛雜,恍然出門,從文明路左轉(zhuǎn)50米,即入北京路。在這千年古道上,人潮涌動,我卻獨自如在荒野。那塊透明的玻璃下面,是北宋的路面,路面的青磚上長著青苔,似乎還散發(fā)著宋代的味道,再下面是元代的路面,我看見和我一樣的北方人在這路面上走過去,牛皮鞋底釘著鐵掌,走在磚砌的路面上,敲打出叮當悅耳之聲,正如那《古代墓志銘》的琴聲;明代、清代、民國和當下的聲音,四重疊加一處,正如那四重奏一般,四只手時而急促,時而舒緩,在這磚塊般的琴鍵上,彈奏出了兩千年之間多少無名死者的跫然足音。
一段時間,我被佟琴和鄰居家的琴聲感染成了一個多愁善感的人。兩個模糊而美好的所在,遙遠而近切,近在眼前,遠在天邊。我的孤獨如同秦朝一統(tǒng)百越的50萬大軍中的一員,猛然來到這異鄉(xiāng)的街巷,越是熱鬧,越顯得另類,格格不入。語言不通,習慣迥異,飲食相悖,思維有別。鄰居的教訓就是最現(xiàn)實的例證。
鄰居在五米之外,一墻之隔,我對他的印象實在談不上深刻,一段時間,被他那一番訓導弄得羞愧難當。時常進了家門,馬上警惕起來,看看對面鄰居先生在不在家,否則不敢貿(mào)然脫衣服;即便脫了,也要拉上窗簾;進了廚房,想起他的提醒,急忙退避三舍,穿點什么,再進去。我的廚房似乎成了禮堂一般。甚至有幾次,我看見他在廚房里,著裝整潔,在做飯,此刻,我盡量避免面對他,盡量拖延時間,或者拿出面板,在客廳操作。很多時候,見他在廚房,我都要等他操作完畢,錯峰下廚。究竟我是從鄉(xiāng)下來的,雖然也自詡為一個文化人,但遇上這位極端文明的人,我難免滋生不少的羞怯和自卑。
有一次,他看見我進了廚房,急忙喊:“鄰居,你是不是也姓董。”我笑了笑,不置可否,便匆匆出了廚房。我才知道,鄰居姓董。說實話,我內(nèi)心里是怕他的,可是在自己家里怕別人,卻又無計可施,這就更令人難堪。
意外的事終于發(fā)生了。一天早晨起床遲了點,我選擇從小區(qū)后門外的迎恩里出去,如此可以避免與大量的人群相撞,會快點到達地鐵站。出了后門,前行不到100米,眼前的一幕勾住了我的目光:一位穿著西服,扎著黑色領(lǐng)結(jié)的男子在垃圾桶里專注地尋找什么。我的好奇和意外可想而知,這文明路,還真是文明,撿垃圾竟然如此講究?正要走過去,轉(zhuǎn)而想,那黑色的領(lǐng)結(jié)似乎有點眼熟,我鼓足勇氣,偏過頭,正面看過去,令人吃驚的事就在眼前:這位撿垃圾的竟然是我的鄰居董先生。
是他那黑色的領(lǐng)結(jié)出賣了他,確定無疑。他就是我的鄰居——董先生。我內(nèi)心的傲慢升騰而起,對他的鄙夷盎然如嶺南的花草,一時葳蕤。我昂首繼續(xù)走路,腳步端直,身端周正,雙目不屑的余光斜睨在他的身上,無法抽拔出來,恨不得看見他手里撿到的是什么骯臟的東西,也許是一個避孕套吧。我狠狠地望著他,擦肩而過,繼而,我竟然停下腳步,悠閑無比地從衣兜里掏出一支煙,惡意地站在原地,點燃。一縷煙從我的嘴里飄出來,愜意無比,我惡作劇地希望他轉(zhuǎn)身注意到我,對,讓他看清楚,就是我,你的鄰居,正在看你撿垃圾呢。
他的左手優(yōu)雅地背在身后,右手空空奓在垃圾箱口,似乎指揮著一場演出,一個微妙而細小的音符正被他的右手提拉起來。我此刻對他真的是鄙夷之極,究竟是一個拾荒者,還拿捏得如此雅致,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感到十分好笑,又無比好奇:住在一線城市核心區(qū)繁華之地,這里可是文明路。北宋時,連續(xù)多年不見有學子中舉,先生們急了,上書官府,在學宮對面開了城門,叫步云門,顯然是想讓學子們平步青云。到了清代,改為文明門,路就叫文明路,沒想到時至今日,這文明路上出了這樣一位落魄的拾荒者!他竟然真的是我的鄰居,真是無奇不有,還裝什么鋼琴師。
我想,其中必有故事,我好奇心愈甚。但上班時間在即,我不能如此邪惡地觀望下去,只好離開我的紳士鄰居,趕往地鐵站。
我上班在東湖,離文明路的寓所只有兩站路,寓所是單位提供的,免費使用,連同物業(yè)費都由單位負責,我感激我的老板。此前上下班,我都是從文明路西行200米,左轉(zhuǎn)進入北京路,直行400米,再左拐,便是北京路地鐵站B口,下了電梯,右轉(zhuǎn)直行100米,等待地鐵;上了這節(jié)車廂,到東湖地鐵站B2下車,正好就在上行的扶梯口,不用擠巴,絕對第一個上扶梯,不耽誤一點時間,出了地鐵站,前行300米,就是單位。整個行程是我反復修改、反復斟酌過的,恰如一段流暢的圓舞曲,疾緩有致,恰到好處。這是我擠地鐵的高效攻略。
自從那一次在迎恩里碰到董先生,好奇心作怪,我徹底改變了上下班線路,每次都從窄窄的迎恩里出去,看看是否能再一次在垃圾箱旁邊遇到鄰居。
還真奏效,每天早晨,我都能碰到他。那時刻,他總是在迎恩里綠色的垃圾桶邊徘徊,專注地撿尋,我想,這位可憐的鄰居,他是在找早餐吧!我裝作毫不在意,仰著頭,不疾不徐,緩緩走過去,像個紳士。其實,多少次,他根本就沒有在意路人,由于太過專注,甚至渾然不覺行人通過。他總是在晨光里背著左手,謹慎地伸出右手,高高抬起,修長的手指向下,正如一只正在探向河水的鶴頭,尋找魚蝦蟲草;很奇怪,我發(fā)現(xiàn)他總是用右手翻檢,有時候,左手或者放在前胸,動作甚是優(yōu)雅,完全不像拾荒者那般伏在垃圾箱口,大手大腳,臟亂不堪。他手指輕柔,似乎在琴鍵上尋找一個難覓的音符,又似在捉筆書寫,正在描繪一幅精妙的山水畫;那白皙的手指細長優(yōu)雅,在陽光里像幾束溫柔的光柱,忽而交叉,忽而分離。他的身材筆直,西裝革履,在晨光的迎恩里堪稱一道風景。
用翻檢這個詞來描摹倒不是十分精準,應(yīng)該用搜尋,對,搜尋更加貼切,因為搜尋有從心而覓的意味,而翻檢的動作太大了,像抄家。他不是在翻檢什么,因為我從未看見他翻檢出什么東西拿在手上,譬如摞起來的紙箱、舊的衣物、過期食品等等,什么都沒有。
一日清晨,我七點起床,單位當天有活動,要趕早集體乘車。迎恩里滿樹的蔭翳中,鳥兒早就婉轉(zhuǎn)啼鳴,我看見他已經(jīng)站在一棵樹下,潔白的雞蛋花次第綻放,樹下是一個垃圾桶,他站在垃圾桶邊,嘴里叨咕著:哪里去了呢?哪里去了呢!我悄無聲息地從他身邊走過,我的惡意有所收斂,他的專注也從未被外界任何東西所干擾。
黃昏,北京路口,那棟橘黃色的轉(zhuǎn)角樓,燈光漸次亮起來,燈光的黃暈,紛紛下披的綠色藤蔓,糾纏在一起,映著夕陽,煞是迷人。向后轉(zhuǎn),就是迎恩里,我不斷回頭欣賞那景致,并未在意前方。及至迎恩里最西頭的垃圾箱邊,鄰居董先生已經(jīng)在我身邊。夏日的垃圾箱散發(fā)出非同一般的臭味兒,他筆直地站著,在黃昏的陽光中,我看見他的左手背著,右手五指有節(jié)律地伸屈著。我沒敢多看他,一時忘了身后的美景,繼續(xù)前行。一個蹣跚學步的嬰兒從右前方的樓口向我跑來,那孩子的身后是一個老婦人,踉蹌追來。我夸張地張開雙臂,迎上那小孩兒;小孩兒見我攔著他,歪歪扭扭回了頭,又向那婦人跑去,我在他身后笑著。那婦人在前面張開雙臂,接住了那小孩兒,一邊看著我,友善地說:“就怕他。”那婦人揚起下巴,示意了一下我身后的董先生,“他有病,很長時間了,怕孩子嚇著。”
“哦,見他總是在垃圾箱邊,什么病?”我問那婦人。
那婦人指了指樓口的椅子,示意我坐下。我坐下來。一縷金色的斜陽正從北京路口的黃樓頂上灑過來。那婦人剛要開口講故事,卻示意著遠處高張著臂膀的鄰居,驚恐地說:“看看,又犯病了,快走,快走——”那婦人還沒有開始講故事,便抱著孩子進了樓門。
我回頭望,董先生站在灑滿金色的巷口,恍若站在巨大的舞臺中央。他面對黃昏的殘陽,揮舞著雙臂。
秋日的一個周末,佟琴再次來到我的住所。她長時間對我若即若離,一方面她對我的詩歌近乎癡狂地欣賞,只要我在微信朋友圈發(fā)出一首詩歌,她幾乎在瞬間點贊;另一方面,對于我本人,她卻顯得有點冷淡,甚至漠視。我對她一往情深,她應(yīng)該最為清楚,人卻恍若隔世。這次,她來了,除了詩歌,就談我的鄰居。我說:“我的鄰居是個優(yōu)雅的拾荒者、行乞者。”她吃驚地說:“不可能,在北京路有房子住,不可能是拾荒者,你知道你這房子值多少錢嗎?”“我不知道,這是單位的房子,給我過渡,在這地段,肯定很高了。”她說:“起碼六萬過了。”我想,這地段的房子價格定然不菲,北京路是廣州文明發(fā)源地,這房子正好在文明路,可想而知。我迅速搜索文明路房產(chǎn),正好有一套精彩大廈的房子,內(nèi)部轉(zhuǎn)讓價是九萬五一平米。我驚奇地說:“按照這個價格,他也是一個千萬富翁了,還撿垃圾。”琴的臉色沉郁,她走到客廳窗口向?qū)γ驵従蛹铱矗戳税胩欤龥]有搭腔。她打開手機,似乎是在拍照。我說:“你小心,他是好像精神有問題,這是他的私人空間,這樣不好。”我走近她,才發(fā)現(xiàn)她使用手機拉近了鏡頭,看鄰居家客廳里的那架鋼琴。她說:“天哪,他是鋼琴師,好鋼琴。”
她回頭坐在沙發(fā)上,我坐在她身邊,她興奮異常地打開那張照片,說:“你看,那是一架很貴的鋼琴,看這些字母:J.&J.HOPKINSON,知道什么意思嗎?”我陌然搖搖頭。我的心思全在她的身上,而她的心思卻在別人家的鋼琴上。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和她接觸,看她手機里的照片,是幾個不知哪國的字母。她散發(fā)著若即若離的體香,對我說:“這架鋼琴誕生于1835年的英國,是世界上最早的鋼琴品牌,是全球數(shù)一數(shù)二的奢侈鋼琴品牌,是高端鋼琴鼻祖。這架鋼琴,音色優(yōu)美,高中低音過渡流暢,是琴中極品。”
她說:“你說他是一個拾荒者,是對他的羞辱,也是對一個音樂人的羞辱。”我很慚愧,補充說:“我親眼見他每天都在垃圾箱翻檢,他不是拾荒者?”她說:“他不是乞討者,也不是一個被人憐憫的人。”我迎合道:“哦,不是不是,他當然有尊嚴;不說他了,我們還是說說我們自己吧!”她站起身來,說:“我們?”她笑著說:“我還要去‘拾荒呢,失陪了。”完了完了,我看著佟琴向門口走去,我想挽留她,卻說不出任何的挽留之詞。我知道,我在對待鄰居的事情上是有點卑鄙。
正在此時,琴聲響起。佟琴停下已至門口的腳步,接著扭轉(zhuǎn)即將出門的身子,興奮向客廳窗口走去,正如登上舞臺一般,她裙袂飛揚,在音樂聲中,像邁開了舞步。
她像渾然忘了前一秒的不快,來到窗口。我看到董先生正坐在鋼琴前,背對著我們,演奏的還是那首曲子,正是佟琴所說的《為一位無名氏的墓志銘而作》。琴聲如流水行云,時而激越慷慨,時而悲憤難抑。佟琴突然依著我,淚流滿面,灼熱的頭臉貼上了我的右頸窩。我站在天井五米之外——正如藏在董先生的背后。隔著空谷,她沉浸在鋼琴聲中,我不得要領(lǐng)。
琴聲在一陣激越之后,嗒然單調(diào)下來,像塌陷了一根柱子的屋子。佟琴從我的頸部抬起頭來,迷茫地看著鄰居家,似乎是在尋找剛剛消失的琴聲。我也聽出來了:原本好幾層的琴聲,如今顯然少了那位老者的彈奏,只剩下了錄音,成為背景音樂一般。
我說:“這是假的。”她驚訝地看著我,充滿憤怒,似乎要以這目光打我一個耳光。我怯怯說:“他是一個瘋子,怎么彈琴!”她站起身來,目光憂傷而憤恨,轉(zhuǎn)身摔門而去,關(guān)門聲如鋼刀一般“嚓——”切斷了我倆!金屬門拍上的聲音勝過一記耳光,驚得我張口結(jié)舌。
等我恍然醒悟,跑出門,見佟琴站在電梯口,背對著我,肩頭在劇烈顫抖。正好電梯上來,電梯顫抖了一下,停下,是上行的電梯,她卻鉆進去了。我呆呆站在電梯口,一片茫然。
正在此時,鄰居家的門嘩然打開,董先生竟然也神情恍惚地站在門口,他的左手覆在右手上,似乎剛從琴鍵上取下來;他渾身戰(zhàn)栗地看著我,胡髭凌亂,他猛然跑到電梯口,嘴里喊:“別啊,我彈的是經(jīng)典曲目,不是靡靡之音!不是——”
電梯停下,門開了,我看見佟琴不在里面。董先生進了電梯,電梯一顫,門關(guān)上,無聲下去了。我回頭拉上自家的門,又疾步走回,按下電梯。大概是在董先生下去的同時,另一部電梯上來,我跨進電梯,來到樓頂,不見佟琴;朝下看,也不見佟琴。我惶恐難安,心仿佛能撞擊到胸肋,咚咚顫動。我打電話,她也不接。
俯身巴望著樓下,我看見董先生向迎恩里跑去,慌慌張張。我猛然發(fā)現(xiàn)佟琴緩緩行走在他的前面,如在夢中。我惶惶再乘電梯下樓,向迎恩里跑去。出了小區(qū),聽到迎恩里有人激烈爭吵,到巷口,我看見一個人和清潔工扭打在一起,細看,是董先生!我跑過去,我看見他渾身沾滿了垃圾,渾濁的顏色染滿了他潔白的襯衣,他渾然不顧這些,一次次撲向垃圾桶,那名強壯的清潔工一次次將他甩向一邊,他被摔倒在地,爬起來,再次向垃圾桶跑過去,撲向垃圾桶內(nèi)。前面幾個垃圾桶都倒在路邊,垃圾傾撒在地面,這肯定是董先生做的。我快速跑過去,那名清潔工正拉著他的腿,將他從垃圾桶內(nèi)拽出來,他用右手死死拽著垃圾桶,拉住清潔工的時候,我突然發(fā)現(xiàn),他的左手除了拇指之外,其余只是四個禿禿的肉瘤!他那沒有四根指頭的左手,在堅硬的水泥地上摩擦著,無助地扣著地面,他和垃圾桶一起被那名清潔工后拽,艱澀地滑行。
我拽住清潔工喊:“松手——松手——”那名清潔工身體壯實,毫不理會我的呼喚,繼續(xù)拽著他,同時用腳踢著他的后腿。
“停下——別傷害他——停下——他的手——”一個女人的聲音。我仰起頭,正是佟琴。
佟琴定然看見董先生那肉瘤般的禿手指了。
我一拳砸向那清潔工的后腦勺,那名清潔工晃了一下,松開了手,又撲向我。我俯身將董先生拉起來的瞬間,被清潔工一腳踩倒在地,我的身體正好壓在董先生的身上,我弓著身子,護著他說:“你別怕,我是你的鄰居。”
“停下——停下——”佟琴已經(jīng)撲到了我們身邊,她死死拽著清潔工的衣襟喊。
“不是靡靡之音……”董先生突然高喊。
這一聲喊,清潔工松手起身了,我也被驚得從他身上爬起來。我拉他的手,正好是左手,已經(jīng)血肉模糊。我抓著那團沒有指頭的血肉,將他拉起身。
“別怕,我是你的鄰居,這是怎么啦?”我問。
“我找我的指頭!他打我!”董先生的眼神飄忽,處于極端的驚懼當中,他花白的頭發(fā)和蒼白的臉頰上沾滿了污穢;他用右手下意識地捂住流著血的左手。
“你的手指?”女友問。
“他們剁了我的手指——不讓我彈琴……剛才,一刀下去,我的四個指頭……”董先生聲音顫抖,用血淋淋的左手指著那個清潔工。
“神經(jīng)病,誰剁你指頭!你看看,把垃圾箱都掀翻了,每過幾天就這樣,還說他瘋了,他一點兒也沒病,就是誠心欺負我這個清潔工——我的勞動也要人尊重……”那清潔工喘著氣,極力辯解。
“別說他神經(jīng)病!”我怒斥。
旁邊有人用粵語說:“嘿呀嘿呀,他是精神有點小小的問題的啦。”
我恍然大悟,小心翼翼地說:“董先生,你沒事吧?好了好了,走吧,咱們回家。”
“他們用砍刀剁了我的手指,扔進了垃圾桶,你看看——”他伸出血淋淋的左手,讓我看。
我突然想起剛才女友在樓上摔門的那一聲,利斧剁下一般的聲音。佟琴站在一邊,淚眼婆娑。她正在打電話,我走過去,輕柔地撫著她的肩頭,她渾身顫抖著,我說:“沒事,琴,沒事,別怕!”
她顫抖著右手里的手機,說:“警察,這里有人被人打了,都流血了,快點兒,迎恩里和北京路交叉處!”
她走到董先生的身邊,掏出一張濕巾,顫抖著擦拭董先生那只有拇指的左手。
警察還沒到來。旁邊有人說:“他有病,好久沒犯了,咋又犯了?”有人說:“肯定又受了什么刺激,否則是不會的。”
不到十分鐘,來了兩位警察,一老一少。他倆溫和地向清潔工詢問了情況,然后又詢問我和董先生的關(guān)系。再后來,年長一些的警察將我拉到一邊說:“你是什么時候住這里的?”我說:“不到一年。”“你和他是什么關(guān)系?”我說:“是隔壁鄰居。”我轉(zhuǎn)而憤怒地詰責老警察:“你們不盤問打人者,反而盤問起我了,什么意思!”老警察說:“莫急莫急,難怪,你可能不知道,他的精神有問題,幾十年了。謝謝你。這個女士你認識嗎?”我說:“我朋友。”老警察說:“你們?yōu)槭裁匆u擊清潔工?”我說:“是因為他襲擊我的鄰居,我正好碰上了,我才阻止他,他不聽,我去拉他,他將我打倒在地上。”
警察教訓清潔工襲擊一個精神病患者是不應(yīng)該的,襲擊一個路人更不應(yīng)該。接著,讓我和清潔工陪同小警察將董先生送到醫(yī)院。在醫(yī)院,醫(yī)生對他的左手傷口清洗包扎,費用40元,由我和清潔工五五分擔,清潔工不愿意,說自己沒錢。正在我們爭執(zhí)不下的時候,佟琴已經(jīng)付了錢,此事算是了結(jié)了。
此后,老少兩警察將我和鄰居送回樓上,當然包括佟琴。將董先生送進房間,我和佟琴也隨同進去,才發(fā)現(xiàn)這房間格局和我的住所一模一樣,干凈整潔,客廳里除了一張飯桌和沙發(fā),就是那架鋼琴。佟琴癡癡看著那架鋼琴,轉(zhuǎn)而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神無疑印證了此前她的發(fā)現(xiàn)。
老警察使了個眼色,似乎也看著那鋼琴,又看著縮在臥室的董先生,對我說:“你剛來這里,可能有所不知,當年,他可是歐洲有名的鋼琴王子,僅次于傅聰啊,傅聰知道嗎?”我說:“我不知道。”老警察笑了,接著說:“不說傅聰了,這位董先生的父親是十三行之后,廣府有名的董老板,有錢有勢,就將小小的他送到了維也納學習鋼琴。后來,董老板被投進了監(jiān)獄,他偷偷回來探望父親,也被抓起來,要他演奏一場音樂會。音樂會就在前面拐角處,現(xiàn)在叫永漢電影院,演奏完之后,正趕上一位香港大佬來廣州,要他單獨為他演奏,董不肯,左手四個手指被一刀剁掉,他瘋狂地揮舞著血淋淋的手,撲在地上,要撿他的四根手指。一個馬仔將他的左手踩在腳下,命令手下把手指扔進樓下的垃圾桶。他當即發(fā)瘋,掙脫那雙腳,要從窗戶跳下去,被攔住;想要沖出劇院,被死死捆綁……大概十年后,他爸爸死了,他就在這一帶拾荒,再后來他家房屋拆遷,補償了他一套房子,就是這一套,還補償了他一筆錢,他就住這里了。他精神時好時壞,平時看不出來有什么問題,就是受了刺激,才會犯病,我們對他很熟悉。”
小警察在一邊說:“有人說是他勾引了香港大佬的小妾,才被剁掉了四根手指……”
老警察瞪了一眼小警察,說:“就你知道得多。他啊,就現(xiàn)在,單手彈琴也是無人能及的。”
我摸了摸我自己的手指頭,手心有點微汗。我想起那脆厲的防盜門關(guān)閉聲——嚓!我說:“街坊大媽說,是他偷東西被剁了手指……”
那警官說:“說法不少,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自從他的手指頭被剁,他就瘋了。據(jù)說,他女兒在意大利,曾經(jīng)來看過他,但是他早就不認識她了。女兒給他買了一架世界頂級鋼琴,放在家里,喏——”老警察向那臺鋼琴努了努嘴巴,接著說:“也雇了鐘點工……但他一直不忘他的手指頭被扔進垃圾箱,所以他只要見著垃圾箱,就要倒騰,總是翻檢。”
我說:“不是翻檢,是搜尋。”
小警官用奇怪的眼神盯了我一眼,說:“你說什么就是什么……”接著那位老警官說:“他已經(jīng)七十多歲了……”一老一少兩警官看了看我,走了。走前,老警官似乎還沒講完鄰居的故事。
佟琴走過去,坐在那架鋼琴前,端坐良久,突然,用左手彈出了幾個音符,那琴像突然驚醒了一般,伸長了胳膊腿,舒展了周身,又似乎呼叫了一聲。
我回頭,董先生已經(jīng)站在臥室門口,繼而輕輕走過來,坐在佟琴的身邊。
琴聲響起,是那首《為一位無名氏的墓志銘而作》,靜水深流,如泣如訴。
佟琴的眼眸閃耀著傾慕,目光灼灼地看著我。我目光癡迷地看著她,低沉地朗誦曾經(jīng)的那首詩歌:
孤獨的時刻突然明亮,
美好和悲傷無可逆轉(zhu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