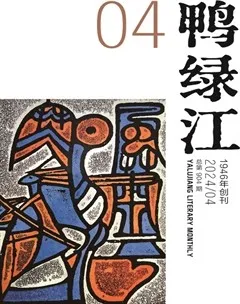方冰:歌唱二小放牛郎
陸天
“牛兒還在河邊吃草,放牛的卻不知哪兒去了。莫非他貪玩耍丟了牛,放牛的孩子王二小……”悠揚的旋律一響起,大家紛紛跟唱。這樣的場面見多了,我就問了許多次,問了許多人為什么跟唱。聽到最多的答案是好聽。再問詞作者是誰,人們往往語焉不詳。這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的詞作者是我尊敬的長輩方冰。說起方冰,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了,可他的大女兒、著名演員方青卓卻是家喻戶曉。其實當年方冰在延安家喻戶曉時,方青卓還沒出生呢。這一首抗戰時期流行于全國的《歌喝二小放牛郎》,被傳唱了八十余年,至今依然廣為流傳。毫無疑問,這首歌已經融入中華兒女的血脈中,感動激勵了我們民族幾代人。
方冰出生于1914年,安徽淮南人,原名張世方,年輕時到延安參加革命,進陜北公學學習創作,取筆名為方冰。“方”是要求自己做人要方方正正;“冰”來源于“一片冰心在玉壺”,寓意心性高潔。許多年過去了,我還記得方冰用安徽普通話吟誦的情景:“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緩慢的語速、莊重的神態,讓人肅然起敬。
方冰在遼寧作協工作,是我父親的老領導。遼寧作協辦公地點在今張學良舊居,所以我小時候也住在那里。方冰喜歡孩子,尤其對我偏愛有加,每次遠遠一看見我就喊:“二嘎子過來扛木頭。”我有姐姐,在家里排行老二 ,二嘎子就是方老當年給我取的外號。在他的故鄉,二嘎子是對小男孩兒的愛稱。我也喜歡這位沒有架子、沒有脾氣的大人。小時候我把人分成小孩兒和大人兩類,那時候我不知道方冰不僅僅是大人,還是一位大人物。“扛木頭”是我們倆的專屬游戲,他兩條大長腿一叉穩穩站立,右胳膊向前一伸,小臂向上一收,擺好了架勢。我就趕緊跳起來,用雙手環抱,掛在他粗壯的大臂上打提溜。悠來蕩去,累得不行時,游戲才在我倆的笑聲中結束。笑聲中經常還伴有糖果獎勵。方冰有三個女兒,她們都沒有這樣的待遇。方冰在我的記憶中永遠是笑聲爽朗、目光慈愛、帶給我童年歡樂的長者。
方冰于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冬天到晉察冀邊區打游擊,同時擔任宣傳工作并開始寫作。曾與田間等人發起街頭詩運動,負責編輯《詩建設》。1945年創作了長篇敘事詩《柴堡》,反映抗日敵后根據地人民的艱苦斗爭生活。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大連市文化局長,1956年在中國作家協會沈陽分會從事創作,后來擔任副主席兼《鴨綠江》雜志主編,著有《戰斗的鄉村》《大海的心》等詩集,1997年因病去世。老人家去了天堂,他把《歌唱二小放牛郎》留在了人間,永遠訴說著那段歷史,永遠為英雄的孩子歌唱。
抗戰期間,中華大地涌現出了不少抗日小英雄,他們只有十二三歲,和平年代本應該上學,或者還在父母身邊貪玩,可是日本侵華戰爭卻改變了他們的命運。孩子們也被卷入戰爭,他們整天吃不飽,穿不暖,餓著肚子給部隊和鄉親們送信、帶路,做了許多工作,有的甚至犧牲了年輕的生命。當年也有小英雄,為了打鬼子,不顧個人安危,把日本鬼子引入了我軍的包圍圈,被敵人識破后殘忍殺害,這類故事在當時的晉察冀邊區廣為流傳。
當時方冰和著名作曲家李劫夫一起在華北打游擊,兩人睡在一鋪炕上,吃在一個鍋里,一個作詞,一個譜曲,配合得十分默契。身為記者的方冰敏銳地捕捉到這些信息,他想為孩子們寫一首歌,讓人們記住那些可愛的孩子,記住那些民族的小英雄。方冰和劫夫商量,兩人一拍即合。可是方冰那時連一支筆也沒有,不過這也難不倒方冰,他就地撿起一根草棍,在草棍一頭綁上一個鋼筆尖。沒有鋼筆水,就去醫療隊要了一點紅藥水。草棍綁鋼筆尖蘸著紅藥水,詩人滿懷的激情化作了《歌唱二小放牛郎》。
因為形象栩栩如生,以至于我少年時代一直以為王二小真有其人,就問方冰,是不是真有一個王二小?方冰并不拿我當小孩兒看待,他認認真真回憶說:“在我的腦子中,確實有一個真名實姓叫王二小的小英雄,但是在我歌中所寫的王二小是眾多小英雄故事的再創作。我的王二小和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不一樣,是我創作出來的典型藝術形象,是無數少年英雄的化身。我要歌唱的不僅僅是某一個人,而是廣大少年英雄的抗日精神。”
我小時候就喜歡纏著大人問東問西,可惜那時候父母忙于運動,忙于工作,其他大人們也都疲憊不堪,沒有人會認真回答一個孩子的問題。方冰不同,我的每一個問題都被他視為“答記者問”,認真詳細回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從來不敷衍了事。受到激勵,我繼續發問:“那么‘九月十六日那天早上,敵人向一片山溝掃蕩是真的嗎?為什么是九月十六日呢?”方冰身材高大,他蹲下來摸摸我的頭,緩緩回答道:“不是真實的日期,九月十六日是我的生日。”很多小時候的記憶如今都荒蕪了,唯有方冰這個九月十六日被我牢牢記住了。2023年9月16日,我在朋友聚會上唱了一遍《歌唱二小放牛郎》,可惜天人永隔,方冰已經聽不到了。把自己生日設定為小英雄為國捐軀之日,這是怎樣的情感投入!這是怎樣的一腔孤勇!
方冰這首敘事詩形式的歌詞非常具有畫面感,語言樸實無華,娓娓道來,就像一位講故事的老人在講述一位小英雄從為東家放牛,到被鬼子抓走帶路,最后把鬼子騙到八路軍的埋伏圈,自己犧牲寶貴生命的全過程。著名作曲家李劫夫看了一遍歌詞后非常激動,通宵達旦一氣呵成,為這首詩譜了曲。歌曲拿到軍區文工團去試唱,很快就唱響了根據地。從此,這首《歌唱二小放牛郎》宛如插上了翅膀,迅速唱遍晉察冀,唱響全中國。藝術家對孩子滿腔的愛,對侵略者的憤恨,激勵著大眾的愛國精神,極大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名如其人,方冰為人方正不阿,他自己也承認“嘴敞”,就是心里藏不住話,有什么說什么,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他對那些年過度政治斗爭不滿,就曾經公開講道:“回想一下這些年,都干了什么了?自己人殺過來,殺過去,一個也沒剩下。”方冰有點口吃,講到“殺過來,殺過去”時往往情緒激動,口中拖著長音“殺,殺,殺過來……”手上還打著手勢,從左邊劃拉到右邊,又從右邊劃拉到左邊,好像滿懷的殺氣快要溢出來似的。
20世紀50年代中期,別有用心的人添油加醋,舉報了方冰。有一天,時任旅大市委書胡明召開會議,通知方冰也參加,當時方冰還在旅大文化局局長任上。旅大的很多人都知道,胡明是方冰的老戰友、老首長,兩人個人關系非常要好,誰也沒想到的是,胡明在會上突然發怒,拍著桌子指責方冰胡言亂語,講了不該講的錯話。不等方冰接話茬,余怒未消的胡明就代表旅大市委決定把方冰下派到熊岳印染廠負責宣傳工作。這一決定著實讓許多人震驚,他們覺得胡明不近人情,就為幾句話處理這么重,等于把老戰友一棍子打死,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說不過去。其實,大家都不知道,隨后到來的“反右運動”對說錯話人的處理力度遠遠不止于此。胡明是用這種方式把方冰保護了起來,不然方冰很可能被定為“右派分子”。“文革”后期,我母親與胡明之女胡小紅成為同事,方冰知道后,特意請我母親轉達對胡小紅的問候。方冰內心一直對胡明充滿了感激。
方冰有個愛好,就是收藏古玩。20世紀50年代末,他經常與著名書法家沈延毅先生交流,一起品鑒藏品。賞心悅目之后,兩位大咖經常愉快地共同進餐。有一次沈老請他吃飯,方冰突然像有了考古新發現似的說:“沈老,你太奢侈了,你用這盤子是道光年間的。”沈老說:“不可能呀,這是新買的景德鎮青花瓷,就是普通日用品,怎么可能是道光年間的呢?”方冰端起盤子,把盤里面的剩菜都倒進了自己面前飯碗中,然后邊笑邊說:“你看,這不是倒光是啥?”沈老這才恍然大悟。沈老一貫不茍言笑,一想到景德鎮變身“道光”,禁不住也跟著哈哈大笑起來。
1965年,為了彰顯工農兵作家的重要性,方冰積極落實“走出去請進來”的方針。“走出去”是指作家們到基層體驗生活,“請進來”是指把基層作家請到作協大院里來。方冰決定把一位名叫霍滿生的農民詩人請到作協大院來,與專業作家詩人們交流。方冰主抓詩歌創作,交流會自然由方冰主持。霍滿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農民,平時愛說順口溜,很有生活,有一些還挺有趣。比如他寫的一首:“扒著門縫往里瞧,我兒我孫吃火勺。我兒吃火勺不給我,我孫還照我兒學(方言,讀音同“淆”)。”把一位農村老人對兒子不孝順的無奈和憤怒表達得非常幽默,同時老人對美食的渴望也鮮活生動。霍滿生還有一些歌頌人民公社的詩歌,其實并沒有太高藝術價值。不過當時霍滿生走進作協大院開詩會,確實像一股叮咚作響的山泉,給大院留下了不少歡樂的話題,以至于我從小就認為詩歌應該帶給人歡樂,詩人也如是。方冰對霍滿生也很感興趣,經常帶頭朗誦霍滿生鄉土詩歌,笑聲最為爽朗,富有感染力,現場也常常滿是歡聲笑語。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作協首當其沖。作協內部分成三派,開始對老干部老作家進行批判。幸運的是作協的領導和普通干部都比較溫和,斗爭的形式僅限于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批斗會等,沒有人身傷害,也沒有人員傷亡。然而天有不測風云,1967年1月,院外的造反派來到作協,他們領頭的是大東區一個工廠的工人,業余作者,愛好寫詩,但多次投稿《鴨綠江》,編輯部也沒有采用。此君對作協的專業作家及編輯非常痛恨,認為這些“文霸”把持《鴨綠江》才造成工農兵的作品不能發表。他們進到作協后強行把大灰樓的地下室作為造反派總部,經常花樣翻新地整治這些專業作家。不過作協內部的造反派并不買這幫人的賬,一時間,作協內部造反派和作協外部造反派沖突不斷,雙方經常因為一些觀點發生矛盾,唇槍舌劍。有一天院外造反派小頭目把老作家、老編輯召集到一起訓話,小頭目說:“你們這些人過去為什么壓制工農兵作家?方冰你先交代。”方冰本來有點口吃,又見院外造反派頭目來勢洶洶,方冰口吻鄭重,回答說:“我……我……我沒有壓制工農兵作家,《鴨綠江》有規定,每期都用十頁版面發表工農兵作品。”小頭目瞪了一眼方冰說:“你還敢抵賴?”說著就把厚厚的一沓手稿摔到方冰面前說:“你看看,這都是我的詩稿,全部被你們退回了,鐵證如山,你還敢抵賴?”方冰就勢把手稿拿過來,蹲在地上認認真真讀了起來,就像平時坐在辦公室里翻閱作者來稿一樣。造反派本來想批判“文霸”,看到“文霸”認真審稿,希望發表的小火苗再次升騰起來。批斗會好像就地變成了詩歌創作交流會。全場鴉雀無聲,在場被批斗的其他作協領導、“文霸”如韶華等人不知結局如何,只好忐忑等待。時間靜靜流逝,方冰翻閱半天,抬起頭來說:“現在……看,還是……不能發表。”方冰一絲不茍的回答,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把在場的人們全都逗樂了。誰也沒見過這么歡樂的批斗會。小頭目又心虛又不甘,氣急敗壞地問:“為什么?”方冰答:“概念化,盡是口……口號。”方冰的回答當然換來又一場疾風暴雨般的批判,好在個小頭目好歹也算是個文化人,并沒有動粗,只是實施語言暴力而已,這才使作協的老干部老作家們免受皮肉之苦。
有一天,院外造反派小頭目手下的女紅衛兵在地下室里唱起了歌曲《美麗的哈瓦那》:“美麗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陽光照新屋,門前開紅花。”歌聲悠揚動聽,傳出很遠。這是一首贊美古巴的歌曲。當時古巴已經被定義為修正主義。作協內部的造反派在樓上聽到地下室傳來的歌聲后,立即組織人力跑到地下室展開批判。作協造反派早就看著這幾個外來的造反派不順眼,這回抓住把柄,豈能放過他們。院外造反派小頭目自知理虧,也不敢再戀戰,怕引火燒身,遂決定撤退,于是這伙院外造反派就這樣狼狽逃竄了。作協大院的管控權又回到了內部造反派的手中。
“文革”期間,方冰被下放到內蒙古農村。他方正耿直,嫉惡如仇,看到當地農民吸食鴉片,非常痛心。他曾經目睹農民毒癮越來越大,煙癮一上來,鴉片斷供,只好把以前吸食剩下的鴉片膏注射進血管,結果當場死亡。用方冰的話說就是:脖子向前一伸,“艮摟”一聲就死了,人命還不如一只小雞崽,場面慘不忍睹。方冰經常出面制止村民吸食鴉片,他不知道,也不屑于知道,當地鴉片交易背后有著巨大的利益鏈條,方冰不但動了利益團體的奶酪,而且他的行為也惹惱了吸食鴉片的農民,丑惡的利益和可悲的愚昧攪和到一起,眼看要燃起一場大火燒毀方冰的“冰”。一伙農民聚集到一起想要滅了他。方冰和方孝孺是一樣的“方”,不過關鍵時刻發現自己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方冰的理智占了上風,他知道好漢不吃眼前虧,于是緊急避險,不得不跑回大連投奔女兒。結果到了大連以后,被警察當作盲流抓了起來。在一起被抓的三十多人中,只有方冰穿著呢子大衣。當過戰士的他身姿挺拔,氣質出眾,小警察懷疑方冰的問題最大,就向旅大公安分局副局長匯報,說抓到的盲流里面有一個人不同尋常,請領導親自審查。這位副局長見到方冰,愣了一下,趕緊快步向前握住方冰的手說:“老首長,你怎么也被抓到這里來了?”原來這位公安分局副局長曾經是方冰的警衛員。在旅大剛剛解放時,方冰隨大部隊進入旅大城市接管,帶的就是這個警衛員。當年的警衛員如今已經成長為公安分局副局長,副局長當場釋放自己的老首長。
“文革”結束后,方冰又回到作協,擔任領導工作的同時仍然堅持創作,1978年后陸陸續續寫了不少詩,1985年出版了詩集《大海的心》。正是在那段時間里,我也對詩歌創作有著濃厚的興趣。關于什么才是優秀作品,我和方冰討論過,他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近幾年來,《歌唱二小放牛郎》這首歌被不斷翻唱。歲月滄桑,社會發展波瀾壯闊,似乎一切都變化了,但這首歌沒變,它依然受到人們的喜歡,依然被廣為傳唱,方冰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了什么是優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