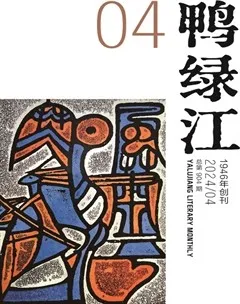大地與夢想的詩意映照
崔國發
作為一個文學尋路者,遼寧作家張少恩在他的散文詩中找到了大地與夢想。出于對生生不息的莊稼的致敬,他以一顆詩心照亮了大地上的萬物,作品里流淌著日常生活的經驗、時光流轉的深思與鄉愁縈繞的情愫。他的作品血肉豐沛而情感深沉,氣象渾雄而魄力宏大,筆力峻厚而相濟剛柔,胸次開闊而曉暢洞達。作為一個多年從事散文詩寫作的“文學的癡心漢,詩歌的朝圣者”,他的作品散見于全國百家報刊雜志,收入多家選本,曾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雄辯的青春》。這本由萬卷出版有限責任公司出版的《大地上的莊稼》,收錄了作者20多年來創作的141章散文詩作品。這些作品編成7輯。作者以“山野之人、農民根脈”自況,他的這些作品就像他筆下厚植的可親、可敬、可愛的莊稼一樣,綠葉蔥蘢而怡心,果實飄香而沁脾,氣韻生動而暢神,而又直面命運的堅韌與隱忍,實現了靈魂與精神在大地上的一次深深的扎根。
靈魂的露珠
詩可以培根鑄魂、啟智潤心。張少恩的散文詩來自靈魂又照耀靈魂,看《大地上的莊稼》,紛披的葉片上托起了心靈的露珠,思想在這里顯得鮮活明亮。一粒粒晶瑩的露珠,折射著太陽的光輝。作者仿佛是一位被美照亮了靈魂的歌者,在本書序言中說“夢想是對生命的滋潤;詩歌是對靈魂的觀照”“心靈時有剎那地顫動。像晨光里一顆熱淚盈眶的露珠”。可見,靈魂的詩來自生命深處的脈動,來自“潤物細無聲”的清露的滋養、疏瀹與澡雪。詩人“凝視一滴露珠,看它怎樣地豐盈”,他“用苦難之光贖回真理之身”;或把額頭舉得更高更遠,招引真理的鋒芒;或如一只持守夢想天空的鷹,不停地探求著真理;或渴望浴火重生的靈魂,“露珠上的光芒叫醒了我啞默的喉嚨”。他相信“露珠可以潤喉,讓我唱出時代的光芒”,更確認“生命必須是燃燒狀的”“存在或是盛開,或是結果,或醞釀吐芽!即使死亡也要讓飄散的靈魂像蝴蝶一樣飛”,可見詩來自靈魂又歸于靈魂,主體靈魂與生命的同構關系,借由露珠、鷹、蝴蝶等意象或客體的對應,形成了思想含量與藝術能量的轉換關系。
生活的地氣
好的散文詩,要求詩人以厚重、扎實、詩情洋溢著現實主義精神,做到“煙火漫卷”。作者從日常生活出發,抵達情感的縱深與人生的本質。將“地氣”接入散文詩,意味著詩人必須介入到那最有質感、最為樸茂、最能體現生活真實的生活現場,即所謂在場,回答好“散文詩如何更有效地回應現實”這個問題。只有建立在廣闊田野與綠色原野上創作出來的作品,才能使散文詩有煙火氣、無功利心,再經由作者充滿激情的想象與入木三分的思考與創造,讓散文詩從“實然”到“應然”,實現“實然”與“應然”的高度統一。張少恩的散文詩便是在這原汁原味的生活中觸發靈感、激活靈性、拷問靈魂。莊稼之于大地總是富于深情,作者之所以虔誠地融入火熱的生活,永葆赤子之心,“把太陽的光芒落在實處”,是因為“大地上的莊稼恩重如山”“母愛般寬廣的田野是我心靈的朝向,令我沉醉、流連,無限地歡喜和依戀”。詩人愛“低處的生活”,喜在高處思考,他把自己的“心與遼闊的田野交換思想”,把他的愛納入大地恢宏的體系,看見那沉甸甸的稻穗、柔韌的菖蒲、裊娜的蘆葦、辛勤的蜜蜂,聽見遍地的蟲鳴、豐收的嘹亮,茂密的枝葉在風聲里的絮語……詩人從內心深處“總能找到鼓舞的力量”。作者與稻鄉建立血緣關系,生命就有了依靠,他的散文詩是從地氣中萃取出來的精品。
花朵的異彩
春蘭秋菊,殊有芬芳;姚黃魏紫,各呈異彩。張少恩的散文詩是有獨特性、辨識度的,他認為“詩必須有自己的異響”。他在本書的序中坦言:“我時常感到沉悶,甚至疑惑——為什么要受困于固有的東西,沿舊詞語的路線走。我想給詞語洗牌,讓它摩擦、碰撞,濺出耀眼的火花,發出異音。”這正如他筆下寫的各種各樣的花朵,如狂野的玫瑰、“黃玫瑰獨辟蹊徑的開辟”,又如“新的詞語是創世紀的斧頭,是生命與靈魂優異的載體。必須獲取這神力,對僵化的思想和邏輯各個擊破。”(《俄耳甫斯手捧的是黃玫瑰》)曾幾何時,一些散文詩從題材到寫法都很陳舊,同質化而沒有新意,缺少創新性,根子就在于詩者閉門造車、無土栽培。張少恩的創作卻能異質變構,異彩紛呈,“丁香也讓我敬畏——深邃的姚紫,高貴的氣息,精巧又細微的花瓣透出其卓異的思維。”(《哦,丁香》)強調的是卓異思維。他從荷花、格桑花、馬蓮花、梨花、蘆花等的鮮明個性與相異特點中獲得自然、人生與藝術的啟示,在守正與創新、推陳與出新之間找到新穎獨特之處,進而自成一家,獨樹一幟,別具一格,努力促成了文本新質的生成。“春天來了,每一朵花都有開天辟地之力!” 藝術創作如此,實現人生的價值莫不如是:創新是人的發展的靈魂。
萬物的靈性
張少恩的散文詩,追求具象與抽象、物性與人情的融合。具象即天地、萬物,抽象即是靈性、心魂;物性即物理屬性,人情屬于社會屬性。它們之間的統合,及物生情,即器見道,使散文詩賦得深情與深意,這是一種關乎物、情、理,并相輔相成的通靈物學或博物詩學。在張少恩的作品里,干凈的枝柯、金絲柳、風中的一叢芍藥、枯萎的野草、桃花、繽紛的落葉、白楊林中的鵲、蝴蝶和蜜蜂等等盡入詩行,無論是寫植物還是寫動物,都是人的內心情感世界的外化表達,或者說,托物言志,借物抒情,于物性中見人情,物的象征與隱喻,直通人的內心與靈魂,物與人在散文詩中始終處于一種對話關系,以物為鏡,以詩為媒,詩人讓我們完成了一種情感教育或理性啟悟。“我要配合風的行動,體現風的意識,風一樣撫觸萬物。比哲學還哲學,比宗教還宗教,那是天籟與地籟的融合;是幽邃的隱喻;是創造世界的能手。”(《像風一樣觸摸萬物》)“陽光的意圖萬物都領會,春天的思想也總能及時到達所有的枝條和根莖。”(《陽光的意圖萬物都領會》)“人間三月,道出萬物的玄機,所有的存在都卓爾不凡”“春天,所有的思想和事物都緊密相連。”(《三月,道出萬物的玄機》)詩人與萬物建立了雙向激活的能動關系,或建立了心與物的關系。《禮記·樂記》說:“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心內在地感觸于物,物外在地作用于心,對于物的頓悟,源自對生命本身的感受。詩人是通靈者,物我相契,靈性便附體且聚魂也。
夢想的翅膀
張少恩善于在散文詩中筑夢追夢。這夢想是大地的夢想,是大地上的莊稼成長中的夢想,是透著歲月輝光的夢想。夢的幽影系于詩的想象,它常會搖蕩性情,恰如鐘嶸在《詩品》中所言:“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借之以昭告。”無論是“幽影”還是“幽夜的夢”,都要求詩人把握住“性靈與靈機、遐思和虛幻”。散文詩如果沒有想象與夢想,詩的美神便不會翩然降臨。明乎此,張少恩這樣寫道:“幽影砸向石頭,濺起了火花。顫巍巍藤勾連星辰,去圓自己的夢。”(《夏至》)“美好的夢想,是最興旺的期貨市場……/豐沛的夏日,我愛它的夜色。信心在遐思和虛幻中出塵。”(《幽夜的夢》)原來這夢想、遐思或虛幻的想象,也來自生活真實的感召。虛實真幻的交織,超凡脫俗的聯想,使散文詩別具新趣,空靈超雋,靈魂搖曳與婆娑。詩人確認繁茂是大地的自豪與榮耀,秋天不是陽光的磨損而是夢想的擦亮,人間的燈火因夢想而分外明亮,這不僅僅是對大地的情深一往,也是詩人心中對于大地價值的一種執著的追求。“我夢見風舞動著蔥蘢的青紗帳;/夢見我披著滂沱的大雨登上山岡。/夢是我,我是夢。我在夏末秋初為大地的豐收交付了定金”“我是我夢的水手,在云間升帆;/我是我夢的農夫,一手老繭直通碩果累累的收成。”(《鮮活的生命賴于詩意的手巧》)──作者的夢想是什么呢?是大地、山川滿身蔥蘢,是瞬間獲取的滿枝甜美,是風舞動著蔥蘢的青紗帳,是為大地的豐收交付的定金,是思想進入風雨的核心,為豐饒的秋天披肝瀝膽,是明月為光榮的秋天錦上添花,是燈火在夢鄉里結籽,是每一粒果實穿越風雨都身懷絕技……雨果說:“想象就是深度。”這深度就是表達感情與表現生活的深度。詩人與大地的夢想擊掌,他的散文詩“長出乘風破浪的翅膀,喜遇天使飛翔的誕辰”(《大地是裝滿天籟的吉他》),作者的心靈與詩歌,均乘著想象的翅膀,在散文詩藝術的天空中,向著夢與遠方振翅高翔。
濃郁的鄉愁
張少恩的散文詩,從現實故鄉到詩歌故鄉,書寫的是發自肺腑的生命的鄉愁、親情的真愛、敷著月光的回憶與沉思,以及對精神的反哺與施洗。詩人念念不忘故鄉大西溝深邃、清澈、寧靜而致遠的夜晚,念念不忘鄉間的光影和一縷縷溫暖的炊煙,念念不忘孩童時代紫燕呢喃、自己也深情據守的老宅,念念不忘父親的一場大雨和娘的大雪,情有所動,心有所感,回到初心,回到自己出發的地方,他始終堅守,鄉愁永是心靈的朝向。每當詩人看見那一盞搖曳的燭光,或者聽見白毛草喊著月色的好,詩人都有著刻骨銘心的生命體驗與生活感知,故鄉便成為詩人鮮明而深摯的精神印記。行走在故鄉豐收的田野上,詩人仿佛看見父親粗糙的大手分蘗出精細的農業,仿佛又感受到母親勞作的幅度像田野一樣寬廣。他在《一盞燈火不斷地向我發散人間的溫暖》中寫道:“有時我側耳傾聽故鄉隱秘的聲息;傾聽草木芳香的窸窣。/故鄉的路雖崎嶇,卻是回放自己的唯一途徑。二姐接替的那盞燈火,在那棵滄桑的老槐樹旁不斷地向我發散人間的溫暖。”著名作家汪曾祺說:“家人閑坐,燈火可親。” 作為一位“城市寄居蟹、鄉愁領受人”,漸走漸遠的鄉土,越來越濃的鄉愁,詩人知道在闊別故鄉很久之后,如何確認精神坐標、在心中安置濃郁的鄉愁,如何讓灼燙的鄉情閃耀著詩意的光芒,如何從濃濃的親情與淡淡的感傷里找到生命的魂路。
讀張少恩的散文詩,我們獲得生命的樸素與敦厚,也領略到大地的廣袤與溫暖。他的作品立魂魄、閃異彩、帶露珠、接地氣、通萬物、連鄉愁、有情懷,既有高邁的人生境界,又有幽微的人間真情,更有深長的思想意味。他的散文詩踔厲發越,振采練情,一定會因為精神的充實與飽滿、氣質的豐富與高貴、詩意的氤氳與華嚴、技法的別致與異響而贏得讀者的垂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