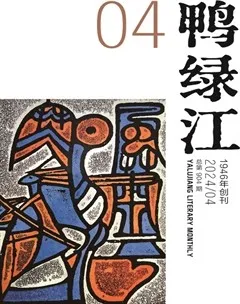巴金致沈從文手札賞析
王增寶
巴金和沈從文是一生的老友。他們于1932年相識于上海,此后,無論在日常生活中,還是文學創作上,二位文學大家都是相互關心,相互激勵。目前所見二人往來書信并不多,《巴金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僅收致沈從文信三通,《沈從文全集》(北岳文藝出版社)所收致巴金及夫人陳蘊珍(即蕭珊)信也在十通以下,且二集所收皆為整理本文字,并未提供原札影印件。2009年,陳建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珍品大系:信函卷》出版,其第一輯中收入了巴金致友人的一批書信,其中有致沈從文手札三種。摩挲筆跡,舊事重溫,益發使人感慨二人之間無拘無束的珍貴友誼。
其中有一通書信,作于1942年6月4日,時值抗日戰爭的艱難時刻,大片國土淪陷。1942年4月,中國入緬遠征軍全線撤退,日軍沿滇緬公路直犯怒江,國民政府命令進攻部隊撤回怒江東岸,固守防線,自此,滇西戰事進入對峙局面,巴金于信首所說“滇局轉安”,即指這種形勢。當時沈從文正在昆明,巴金希望他能夠“在平靜的快樂中打發日子,多寫點好文章出來”。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沈從文逃離北平,于1938年4月到達昆明,1939年8月受聘于西南聯合大學師范學院國文系,開設“國文”“各體文習作”等課程。跑空襲警報是家常便飯,時時感受到戰爭的危險,生活條件也大不如前。
戰爭期間,百姓流離遷徙,類如蓬轉。巴金為了《烽火》《文叢》等雜志編輯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叢書、叢刊出版工作及社務活動,輾轉于上海、香港、廣州、武漢、昆明、重慶等地。1941年9月,巴金到桂林,籌建開辦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辦事處。因陳蘊珍在西南聯大讀書,巴金時常來昆明,偶與沈從文見面,雖然時間不長,但兩位老朋友得以再續友誼,他們在小飯店里吃米線,一同出游,一同跑警報,也一同看見了空襲中的炸彈和尸體。巴金于1942年5月赴成都治牙,致沈從文的這封信即作于此間。信中談及時局、出版、個人努力等諸多事體,細述瑣瑣家常,備見二人友誼真情。
沈從文到昆明后,雖然仍是編書、教課、寫文章,但戰時物價上漲,家庭生活已不如從前寬裕。好在有巴金幫忙,克服戰時紙張、印刷困難諸問題,設法在重慶印了張兆和的短篇小說集《湖畔》,在成都印了沈從文的散文集《昆明冬景》。巴金在信中還特別問及《長河》的出版打算,這正是沈從文當時的一大困擾。因《長河》內容涉及湘西少數民族與國民黨當局的矛盾諸問題,小說在香港《星島日報》連載時即被刪節,1942年重寫書稿準備在桂林明日社出版時,又被國民黨檢查機關以“思想不妥”為由全部扣留。經輾轉交涉,由桂林、重慶復兩度審查仍無法出版。巴金說希望用幫忙印書的方式“逼幾個熟朋友多寫點東西”,其實這何嘗不是幫忙沈從文解決最現實的生計問題?
身處亂世,仍要認真地做事、做人、生存,這是兩位朋友的共同信念。巴金在信里說:“對戰局我始終抱樂觀態度。我相信我們這民族的潛在力量。我也相信正義的勝利。在目前,每個人應該站在自己的崗位努力,最好少抱怨,多做事;少取巧,多吃苦。”當時的沈從文也在思考文學與民族的命運問題,其《文學運動的重造》(1942)一文,對文學的過度商品化和作家的純粹清客化現象進行批評;同時也指出希望所在:“職業作家中少壯分子,更有不少對文學抱了一種遠大憧憬,心懷宏愿與堅信,來在艱苦寂寞生活中從事寫作的。”這些作家中就包括茅盾、丁玲、巴金等人。其實,早在《一般或特殊》(1939)一文中,沈從文就對“抗戰八股”文學的政治化傾向提出批評。他認為文學創作的特殊性不應混同于抗戰宣傳的一般性:“中華民族想要抬頭做人,似乎先還得一些人肯埋頭做事,這種沉默苦干的態度,在如今可說還是特殊的,希望它在將來是一般的。”這一觀點曾受到左翼作者的尖銳批判,如巴人認為沈從文“這一毒計”已經超過了梁實秋的“抗戰無關論”。巴金在此信中則極力肯定老朋友的意見:“自己走自己的路,不必管別人講什么……你那埋頭做事的主張,我極贊成,也盼你認真做去。”國家民族存亡憂患之際,每個人都“埋頭做事”,抗戰成功與社會進步,其轉機實在于是。
巴金此札寫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成都辦事處”的兩頁紙箋上,每頁12行,四周有邊欄,豎行界格,毛筆行草,天頭處有關于“我在此醫牙”的小字補述語。在現代文學館所公布的這一批巴金手札中,另有致冰心、陳荒煤、李健吾、汝龍等人若干通,多用鋼筆寫就,雖然也是自由飄逸的書風,但硬筆書寫的線條容易流于單一,缺少粗細、輕重的變化。巴金致沈從文的這三通書信,皆用毛筆寫就,用筆也頗為講究。沈從文于書法素有專攻,章草風流有別裁,巴金給這位胸懷“勝過鐘王”壯志的老友寫信時,或許也隱隱有一種以書法對等交流的意識。此札整體上給人飄逸灑脫之感,結體收放自如,點畫精熟謹嚴,卻多有放縱之意。一字之中,有時突然宕出一筆,而別生出一種瀟灑姿態。其長橫的書寫最見個性,用筆多從極左側空中蓄勢,果斷入紙,向右上斜向疾行,落筆之初即大膽越出當前界格。如“事”“不”的起筆,“我”“景”中間的橫筆,“寫”字的末筆長橫,等等,皆刻意發力,筆勢開張舒展,有力量感,有英武氣。信札紙面密密麻麻的文字布局中,忽飛來長劍似的一橫,警拔獨秀,如詩之詩眼,為全篇增添一股豪放氣勢。當然,這種氣勢是蘊含在信札整體的飄逸風格中的。巴金寫信時應是處于一種愉悅自由的心境當中,信筆由之,隨心所欲,所以章法上搖曳多姿,連帶自然,用筆酣暢淋漓,頗似兩位老友的交往風格:有話就交談,無話便沉默,自由自在,無拘無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