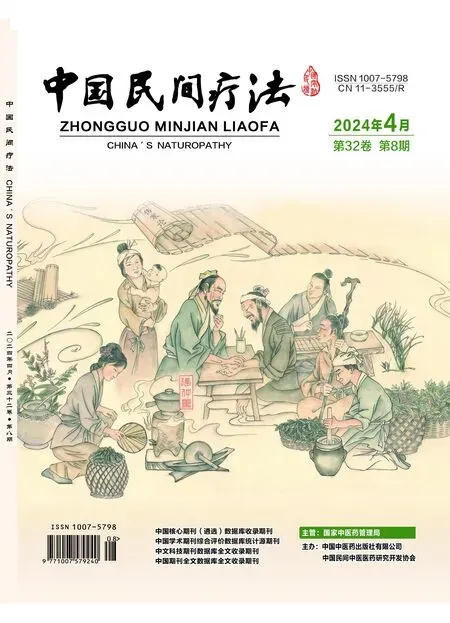督灸聯(lián)合西藥治療強直性脊柱炎的系統(tǒng)評價
陳王,范超領,游玉權,魏志勇,余添賜
(福建省泉州市正骨醫(yī)院,福建 泉州 362000)
強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AS)是一種由環(huán)境和遺傳等多種因素導致的以侵犯中軸關節(jié)為主的全身性、慢性、炎癥性疾病[1-3]。本病發(fā)病隱匿,病情復雜,早期誤診率及中晚期致殘率均較高,可導致患者脊柱強直畸形、活動受限等,目前尚無特效藥可根治[4]。統(tǒng)計資料表明,我國AS的發(fā)病率為0.3%[5],國外AS的發(fā)病率為0.1%~1.4%[1-3]。西醫(yī)在本病活動期主要應用抗風濕藥、非甾體抗炎藥、糖皮質激素和生物制劑等口服藥物治療,在疾病晚期(出現(xiàn)椎體楔形變或嚴重畸形)則采用手術治療,但療效往往不佳,且存在潛在不良反應[4,6-7]。
中醫(yī)根據(jù)AS “病及骨節(jié)、遷延難愈、甚則傴僂”的特征性表現(xiàn),將其歸于“痹證”“大僂”“骨痹”等范疇,認為本病病位在脊,多由先天稟賦不足,腎精虧虛,加之后天外邪侵襲,督、腎二脈經(jīng)氣運行不暢,痹阻經(jīng)絡所致。研究顯示,督灸作為一種中醫(yī)傳統(tǒng)特色外治法,聯(lián)合西藥治療AS療效顯著、不良反應少,但相關臨床研究也存在辨證施治觀念弱、療效評定標準不統(tǒng)一及樣本量較小等不足[6,8-9]。基于此,本研究系統(tǒng)收集國內(nèi)外已公開發(fā)表的關于督灸聯(lián)合西藥治療AS的隨機對照試驗(RCT),并嚴格按照Cochrane系統(tǒng)評價學方法客觀探討其真實療效和安全性,以期為臨床治療AS提供循證依據(jù)。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標準 ①研究類型。RCT,語種限中/英文,文中需明確提及“隨機”字樣。②研究對象。明確診斷為AS,年齡、性別及病例來源等不限。③干預措施。對照組采用單純西藥等治療,觀察組在對照組基礎上加用督灸治療。④結局指標。主要結局指標:總有效率、視覺模擬評分法(VAS)評分和晨僵時間;次要結局指標:C 反應蛋白(CRP)、紅細胞沉降率(ESR)、Bath強直性脊柱炎疾病活動性指數(shù)(BASDAI指數(shù))、Bath強直性脊柱炎疾病功能指數(shù)(BASFI指數(shù))、胸廓活動度、腰椎活動度(Schober試驗)、枕墻距、指地距及不良反應。
1.2 排除標準 同一試驗或數(shù)據(jù)重復發(fā)表的文獻;觀察組所用灸法不屬于督灸;納入文獻的數(shù)據(jù)資料不完整。
1.3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綜合檢索如下數(shù)據(jù)庫:Pub Med、中國生物醫(yī)學文獻服務系統(tǒng)(CBM)、中國知網(wǎng)(CNKI)、維普中文科技期刊數(shù)據(jù)庫(VIP)、萬方數(shù)據(jù)知識服務平臺。檢索時間:從各數(shù)據(jù)庫建庫到2022年7月。中文檢索詞:灸、灸法、督灸、長蛇灸、鋪灸、強直性脊柱炎、類風濕性脊柱炎、變形性脊柱炎、萎縮性脊柱炎。英文檢索詞:moxibustion、cauterize、AS、ankylosing spondylitis。檢索策略優(yōu)先考慮查全,故依據(jù)每個數(shù)據(jù)庫的特征用自由詞檢索和相應高級檢索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檢索范圍包含題名、關鍵詞、摘要或全部內(nèi)容,同時對檢出的文獻進行引文追蹤檢索,以擴大檢索范圍,從而降低漏檢率。以CNKI為例,具體檢索策略如下:“#1=強直性脊柱炎OR類風濕性脊柱炎OR變形性脊柱炎OR 萎縮性脊柱炎”;“#2=灸OR灸法OR督灸OR長蛇灸OR鋪灸”;“#3=#1 and#2”。
1.4 資料提取和質量評價 采用NoteExpress 3.0軟件管理和遴選文獻。由2名研究員獨立進行文獻資料的提取及方法學質量評價,如二者存在分歧,與第3名研究者協(xié)商解決。納入文獻的方法學質量評價采用改良Jadad量表[10],評價內(nèi)容包括隨機方案的生成、是否隨機隱藏、是否采用盲法、失訪或退出。針對每1項研究結果,做出“恰當”(2分)、“不清楚”(1 分)、“不恰當”(0分)的判斷,并計算總分。總分>3分為高質量研究,總分≤3分為低質量研究。采用Cochrane協(xié)作網(wǎng)提供的RCT偏倚風險評估工具繪制納入文獻的偏倚風險匯總圖[11]。
1.5 統(tǒng)計學方法 應用Rev Man 5.3統(tǒng)計軟件進行Meta分析,數(shù)據(jù)審查用交叉核對法。計數(shù)資料采用比值比(OR)及其95%可信區(qū)間(95%CI)作為效應指標,計量資料采用均數(shù)差(MD)及其95%CI作為效應指標。首先根據(jù)合并研究的變異程度確定Meta分析的統(tǒng)計分析模型,即計算各研究間的I2統(tǒng)計值。I2為0~40%、30%~60%、50%~90%、75%~100%分別表示異質性為可能不重要、中度、實質性、高度[12]。I2≤50%表示異質性不顯著,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合并分析;I2>50%表示存在顯著異質性,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合并分析,必要時考察異質性來源或進行亞組分析。Meta分析的檢驗水準為α=0.05。不適宜納入Meta分析的文獻則采用描述性分析。繪制倒漏斗圖定性分析潛在的發(fā)表性偏倚,同時采用敏感性分析評估Meta分析的穩(wěn)定性。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 嚴格按納入和排除標準進行文獻篩選,最終納入文獻19篇[13-31],均為中文文獻。篩選流程圖見圖1。

圖1 督灸聯(lián)合西藥治療強直性脊柱炎納入文獻的篩選流程圖
2.2 納入文獻的基本特征及方法學質量 19篇RCT文獻合計納入患者1 559例,其中觀察組784例,對照組775例,單個研究組內(nèi)樣本量為20~129例,療程最短3周,最長3 個月。納入文獻的基本特征見表1。19篇RCT 文獻中,僅9篇文獻[13,15,17,21,23-25,29,31]提及隨機數(shù)字表法,1 篇文獻[20]采用1∶1 隨機分組法,1篇文獻[14]使用就診順序號進行分組,但均未說明具體隨機方案的產(chǎn)生過程。所有研究均未使用盲法,也未對脫落或失訪患者進行意向性分析。依據(jù)改良Jadad量表進行質量評價,2篇文獻[17,21]達到“高質量研究”標準。納入文獻的偏倚風險匯總圖見圖2。

表1 督灸聯(lián)合西藥治療強直性脊柱炎納入文獻的基本特征

圖2 督灸聯(lián)合西藥治療強直性脊柱炎納入文獻的偏倚風險匯總圖
2.3 主要結局指標的Meta分析
(1)總有效率 15 篇文獻[13-20,22,24,27-31]以總有效率為效應指標,合計納入患者1 307 例,其中觀察組657例,對照組650 例。異質性檢驗結果(I2=0%,P=1.00)表明研究間無顯著異質性,故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結果顯示,觀察組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OR=4.14,95%CI(2.88,5.95),Z=7.68,P<0.000 01]。見圖3。

圖3 督灸聯(lián)合西藥治療強直性脊柱炎總有效率的Meta分析森林圖
(2)VAS評分 5篇文獻[19-23]以VAS評分為效應指標,合計納入患者312例,其中觀察組157例,對照組155例。異質性檢驗結果(I2=98%,P<0.000 01)表明研究間存在高度異質性,考慮與受試者對疼痛的耐受程度、督灸操作不同等因素有關,故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結果顯示,觀察組VAS評分低于對照組[MD=-0.95,95%CI(-1.84,-0.07),Z=2.11,P=0.03]。見圖4。

圖4 督灸聯(lián)合西藥治療強直性脊柱炎視覺模擬評分法評分的Meta分析森林圖
(3)晨僵時間 5篇文獻[16-18,22,26]以晨僵時間為效應指標,合計納入患者328例,其中觀察組165例,對照組163 例。異質性檢驗結果(I2=99%,P<0.000 01)表明研究間存在高度異質性,考慮與受試者對疼痛的耐受程度、督灸操作不同等因素有關,故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結果顯示,觀察組晨僵時間短于對照組[MD=-4.61,95%CI(-6.78,-2.43),Z=4.15,P<0.000 1]。見圖5。

圖5 督灸聯(lián)合西藥治療強直性脊柱炎晨僵時間的Meta分析森林圖
2.4 次要結局指標的Meta分析
(1)除不良反應外的次要結局指標 結果顯示,除胸廓活動度和BASFI指數(shù)外,觀察組在其他6個次要結局指標方面均優(yōu)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2 督灸聯(lián)合西藥治療強直性脊柱炎除不良反應外的8項次要結局指標的基本情況和Meta分析統(tǒng)計量
(2)安全性評價 19篇RCT 文獻[13-31]中,8篇文獻[14,16-17,20-22,24-25]報道不良反應的發(fā)生情況,其中2篇文獻[14,17]僅提及兩組患者在治療過程中均未見嚴重不良反應的發(fā)生,1篇文獻[24]僅說明對照組在治療期間出現(xiàn)消化道反應、皮疹、頭暈不適9例,無目標數(shù)據(jù)可提取。對剩余5篇文獻[16,20-22,25]的不良反應進行資料和數(shù)據(jù)提取后發(fā)現(xiàn),胃腸道反應、皮膚水泡及谷草轉氨酶(AST)升高的報道數(shù)≥2,以上述3項不良反應分為亞組進行Meta分析,結果顯示,組間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故從定量角度出發(fā),不能認為兩組患者在不良反應的發(fā)生方面存在差異。見圖6。

圖6 督灸聯(lián)合西藥治療強直性脊柱炎安全性評價的亞組分析森林圖
2.5 發(fā)表偏倚分析 19篇RCT 文獻中,以總有效率為結局指標的文獻最多,有15篇,故對其進行倒漏斗圖分析。結果顯示,所有圓點大致向漏斗圖頂端集中并靠攏,且圖形基本對稱,表明存在發(fā)表性偏倚的可能性不大。見圖7。

圖7 督灸聯(lián)合西藥治療強直性脊柱炎總有效率的倒漏斗圖分析
2.6 敏感性分析 總有效率為本系統(tǒng)評價的主要結局指標,且以其為結局指標的文獻最多,故對其進行敏感性分析以考察Meta分析結果的可靠性。首先,剔除樣本量最大的1篇文獻[24]重新進行Meta分析,結果顯示[OR=4.52,95%CI(3.05,6.72),Z=7.48,P<0.000 01]與剔除前結果一致。其次,剔除樣本量最小的1 篇文獻[17]重新進行Meta 分析,結果顯示[OR=4.11,95%CI(2.84,5.96),Z=7.47,P<0.000 01]與剔除前結果一致。最后,轉換總有效率的Meta分析模型重新進行Meta分析,隨機效應模型結果顯示[MD=4.07,95%CI(2.82,5.86),Z=7.52,P<0.000 01]與轉換前固定效應模型結果一致。綜上所述,可以認為本次Meta分析的可靠性較好。
3 討論
AS的早期癥狀不顯著,隱匿性強,往往錯過最佳診療時機。近年來,諸多學者著重從督脈入手,應用灸藥并用治療AS,療效獨特,逐漸被臨床重視[32]。《素問·痹論》云:“腎痹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又如《素問·骨空論》所云:“督脈為病,脊強反折。”中醫(yī)認為,AS以風、寒、濕、熱、瘀諸邪阻滯為標,以腎督虛衰為本,治宜補腎強督,輔以散寒、祛風、清熱、除濕、活血等,正如《素問·痹論》所言:“故骨痹不已,復感于邪,內(nèi)舍于腎。”《證治準繩·雜病》云:“若因傷于寒濕,流注經(jīng)絡,結滯骨節(jié),氣血不和,而致腰胯痛。”《醫(yī)學衷中參西錄》曰:“凡人之腰疼,皆脊梁處作疼,此實督脈主之……腎虛者,其督脈必虛,是以腰疼。”背為陽,督脈循行于身之背,而諸陽經(jīng)交會于督脈,故有“督為陽脈之海,總督諸陽”之說。若督脈受邪,各陽經(jīng)氣血必然運行失常,從而導致相關病證的發(fā)生。督脈上貫脊而系腦戶,下循腰腎而聯(lián)系命門,與腎密切相關。督脈需腎氣滋養(yǎng),當腎氣不足時,督脈亦可起到滲灌和蓄積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督灸作為傳統(tǒng)中醫(yī)經(jīng)典外治法之一,是在督脈對應的脊柱節(jié)段上施以特制中藥灸引起皮膚發(fā)泡的一種灸法,集藥物、經(jīng)絡、發(fā)泡和艾灸的作用于一體,融溫督、補腎、祛寒、通絡于一爐,使藥力直達病所,且操作安全可靠、方便有效[9,27]。譚潔等[8]從“扶陽”理論角度淺析督灸治療AS的理論依據(jù),認為督灸有“以通為補”之效,可溫補腎、督二脈之虛,疏通脈絡,使氣血運行暢達,陰陽升降有序,進而振奮陽氣,促進病理產(chǎn)物的排出。長蛇灸又稱鋪灸,是在傳統(tǒng)督灸基礎上發(fā)展而來的灸法,多施灸于大椎至腰俞間的督脈段,具有灸面廣、艾炷大、火力宏及溫通強之長,常用于痹證、虛損等疾病的治療[13,18,30]。
筆者認為,督灸治療AS的關鍵在于把握督脈與AS發(fā)病部位一致的特點,督灸可直接作用于病所,逐寒濕,溫經(jīng)脈。研究發(fā)現(xiàn),督灸可通過調(diào)節(jié)輔助性T細胞(Th)17/調(diào)節(jié)性T 細胞(Treg)/Th1免疫失衡,改善AS患者的炎性反應狀態(tài),調(diào)節(jié)氧化指標,延緩AS患者骨質、軟骨的破壞,從而改善其關節(jié)功能活動度,防止關節(jié)畸形,降低致殘率[13,16,33-34]。近年來,國內(nèi)關于督灸聯(lián)合西藥(柳氮磺吡啶、氨甲蝶呤和非甾體抗炎藥等)治療AS的報道層出不窮,但在臨床療效和安全性方面缺少循證醫(yī)學的相關證據(jù)。本研究系統(tǒng)收集相關文獻,并進行系統(tǒng)評價,主要結果可歸納為以下幾點。①除胸廓活動度和BASFI指數(shù)外,督灸聯(lián)合西藥治療AS 在總有效率、VAS 評分、晨僵時間、ESR、CRP、BASDAI指數(shù)、腰椎活動度、指地距和枕墻距方面的療效均優(yōu)于對照組。②從定量角度出發(fā),目前尚不能認為兩組患者在不良反應的發(fā)生方面存在差異。③納入文獻的倒漏斗圖結果提示,本研究存在發(fā)表性偏倚的可能性較小。④敏感性分析結果證實,本研究結論的可靠性較好。督灸聯(lián)合西藥治療AS的這種優(yōu)勢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中醫(yī)的內(nèi)外兼治、灸藥并用、整體與局部相結合的治療特色,這種“內(nèi)外同治”的中西醫(yī)結合治療策略或許是今后治療AS的發(fā)展趨勢。
盡管本研究對當前督灸聯(lián)合西藥治療AS的證據(jù)進行了循證醫(yī)學評價,但仍需指出的是,其仍存在諸多局限性。①納入RCT 的方法學質量普遍偏低,如按就診順序進行隨機分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RCT,屬半隨機臨床對照,另外在納入的文獻中未見盲法、隨機隱藏及意向性分析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多種偏倚風險。②終點療效指標并不完全統(tǒng)一,難以全部合并進行分析,如在12項目標結局指標中,部分文獻僅有總有效率可提取。③所有文獻均為中文文獻,漏斗圖雖對稱性尚可,但地域、語言及結果報告偏倚等仍不能排除。④本系統(tǒng)評價遴選文獻的初衷是國內(nèi)外數(shù)據(jù)庫中公開發(fā)表的RCT 期刊文獻,并輔以引文檢索和手工檢索,以保證納入文獻的質量,故相關會議論文、碩博士畢業(yè)論文等不在本研究的納入范疇,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文獻選擇偏倚。⑤多數(shù)研究對于不良反應和隨訪未給予足夠重視,致使本研究安全性評價的信息量匱乏,因此在后續(xù)臨床研究中應進行定期有效的隨訪觀察。綜上,臨床研究者有必要參加相關臨床試驗方法學培訓,并根據(jù)試驗報告統(tǒng)一標準(CONSORT)聲明要求嚴格規(guī)范設計方案,今后開展更多大樣本、多中心聯(lián)合的高質量研究,以提供更強有力的證據(jù)評估灸藥并用方案的療效和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