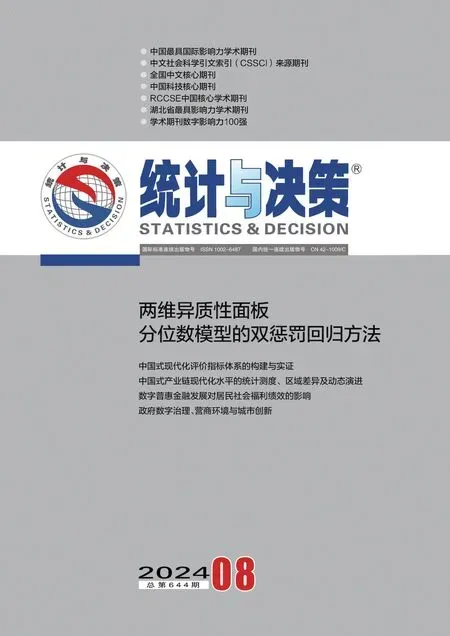中國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的測度、異質性及動態演進分析
曾 鵬,程 寅,魏 旭
(廣西民族大學a.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b.經濟學院;c.管理學院,南寧 530006)
0 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數字經濟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指出,在“十四五”時期,我國數字經濟轉向深化應用、規范發展、普惠共享的新階段[1]。城市群作為能產生巨大集聚經濟效益的區域空間形態,其數字經濟發展狀況能較為客觀地反映出我國數字經濟的建設水平,目前區域內部仍存在數字資源難以有效利用、數字資源分布不均等問題[2]。因此,本文通過測度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來分析不同區域的數字經濟發展狀況,對準確把握城市群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和規律,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目前,對城市或城市群數字經濟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是理論研究方面,學者們總結了國際經驗[3],對數字經濟的概念[4]、創新模式[5]、科學問題[6]進行總結,構建了數字經濟理論體系。其二是地區差異分析方面,學者們通常選用Dagum基尼系數測度數字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7],并運用插值模擬、Zipf位序-規模法則、地理探測器等方法對數字經濟發展的空間分異影響因素進行探測[8]。其三是數字經濟的效率方面,部分學者運用三階段超效率SBM 模型,引入外部環境變量、隨機性因素、松弛變量和非參數的分位數回歸模型,考慮非期望產出,測度了國家層面的數字經濟效率[9];并從行業視角,對省域數字經濟效率的區域差異進行分析,進而運用Markov 鏈等方法從時間和空間的角度對省域數字經濟效率演變趨勢進行分析[10]。通過以上文獻梳理發現,目前對城市群層面的數字經濟效率進行分析的研究相對較少。
綜上,本文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拓展:第一,運用DEAMalmquist 指數來測度中國城市群的數字經濟效率;第二,運用Dagum基尼系數分析中國城市群區域內、區域間和總體差異;第三,運用Markov鏈估計方法分析各城市群內的城市在不同狀態下的轉移概率,探討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的動態演化趨勢。
1 研究設計
1.1 樣本選擇
本文參照國務院、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及各省級政府批復印發的19 個城市群發展規劃文件,確定中國的城市群分布狀況,其中包含重點建設五大國家級城市群(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長江中游、成渝),穩步建設八大區域級城市群(山東半島、粵閩浙沿海、中原、關中平原、遼中南、哈長、北部灣、天山北坡),引導培育六大地區級城市群(滇中、黔中、晉中、蘭西、呼包鄂榆、寧夏沿黃)的229 個城市,本文剔除數據缺失的城市,最終選取城市群包含的196 個城市2012—2021 年的數據進行研究[11]。
1.2 研究方法
1.2.1 DEA-Malmquist指數
本文采用DEA-Malmquist 指數[12]來測度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具體模型如下:
其中,ρSE表示效率值,該模型存在n個DMU(決策單元),當ρSE≥1時,表明該決策單元有效;每個決策單元中有m項投入指標和s1項產出指標,x表示投入,yd表示產出,s-表示投入的松弛變量,λ表示權重。
EDA-Malmquist 指數衡量某DMU 在t和t+1 時期 的相對效率,即反映了效率的變化情況。
1.2.2 Dagum基尼系數
本文運用Dagum 基尼系數[13]對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的地區差異進行測度,根據基尼系數及其按子群進行分解的方法,將城市群差異的總體基尼系數G分解為區域內差異的貢獻Gw、區域間差異的貢獻Gnb以及超變密度的貢獻Gt,以此來測度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差異,公式如下:
其中,k 表示城市群數量,n 表示城市數量,yˉ表示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均值,yji表示第j 個城市群第i 個城市的數字經濟效率,yhr表示第h個城市群第r個城市的數字經濟效率。
區域內差異的貢獻Gw、區域間差異的貢獻Gnb以及超變密度的貢獻Gt的計算公式分別為:
其中,djh表示城市群間數字經濟效率的差值,即第j個城市群和第h 個城市群中所有yji-yhr>0 的樣本值加總的數學期望,公式為:
其中,Fh表示第h個城市群的累計密度分布函數,Fj表示第j個城市群的累計密度分布函數。
1.2.3 Markov鏈
本文運用空間Markov 鏈[14]來分析中國城市群內各城市數字經濟效率的內部動態特征及其演變規律,其表達式見式(9)。將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劃分為N 種類型,通過Markov 鏈轉移概率矩陣可得到一個N×N的城市數字經濟效率狀態轉移概率矩陣P,如式(10)所示;采用地理距離權重矩陣將地理空間上的滯后效應與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的時間序列相結合,進而將N×N的轉移概率矩陣分解成N個N×N的條件轉移概率矩陣。
其中,nij表示在樣本期內i類型在第t年轉移到第t+1 年的j類型的城市的數量,ni表示在樣本期內為i類型的城市個數,Pij表示屬于i類型的某一城市的數字經濟效率從第t年轉移到第t+1年的j類型的概率,采取極大似然估計來計算,表達式見式(11)。
1.3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首次詮釋了數字經濟的新內涵: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是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主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融合應用、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重要推動力,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的新經濟形態。而數字經濟效率則是對于數字經濟單位時間產出的測度[15,16]。
本文遵循構建指標體系的全面性、系統性、典型性、數據可得性等原則[17],結合蔡昌等(2020)[18]對數字經濟效率和數字經濟產出效率的評價方法,構建中國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評價指標體系,如下頁表1所示。

表1 中國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評價指標體系
根據經濟學家薩伊提出的“生產三要素論”,本文選取的投入指標包含勞動、資本和土地三個方面,勞動用“科研人才投入”表示,資本用“研發資金投入”表示,數字經濟也叫信息經濟,其通過5G網絡、工業互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發展于信息技術尤其是互聯網技術之上,從這個角度來看,推動城市群數字經濟發展的“土地”可通過數字經濟基礎設施來反映,因此本文用“數字基建投入”來表示“土地”這一維度。財政支出中科學技術支出區位熵的計算公式為(地區科學技術支出/地區財政一般預算支出)/(全國科學技術支出/全國財政一般預算支出)。
根據數字經濟三大定律之一的“達維多定律”,進入市場的第一代產品能自動獲得一半的市場份額,任何企業在各自領域中必須第一個淘汰自己的產品,因此,技術創新尤為重要,本文用發明專利申請授權量和專利申請授權總量來反映數字經濟的技術效益。數字經濟產出指標中的經濟效益本應用數字經濟產業產出來表示,但目前對數字經濟產出的衡量仍處于摸索階段,本文選擇地區生產總值作為數字經濟產出的代理變量,其包含了所有數字經濟產出,并且一個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與地區生產總值即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有非常強的關聯。數字普惠金融是實現普惠金融的主要形式,普惠金融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數字經濟的發展;除此之外,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測算數字經濟得到數字經濟主成分,該指標參考了趙濤等(2020)[19]的研究。本文采用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和數字經濟主成分兩個指標來反映數字效益。
1.4 數據來源
由于城市群樣本中包含部分地級市代管的縣級市或省直管的縣級市,數據樣本可能會出現重疊,因此予以剔除,加之部分城市數據缺失嚴重同樣需要剔除,因此選取城市群包含的196個城市2012—2021年的數據。其中,各城市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從業人員數量、科學技術人員數量、科學技術支出、經濟與財政相關數據均來自歷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全國的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部分數據來源于國家和各省份統計局官方網站。
2 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的測算結果
2.1 描述性統計分析
將各個城市群2012—2021年的數字經濟效率進行匯總(見表2),從城市群整體空間演化格局來看,各城市群內的數字經濟效率分布較為不均衡,東部地區數字經濟效率較高的城市要多于西部地區。目前中國城市群區域內數字經濟發展較為不平衡,各城市群內的數字基礎設施和數據中心存在一定程度的供需失衡、失序發展等問題。數字化發展面臨東西部地區數字化發展失衡的區域性問題,因此帶動相關數字產業有效轉移,促進東西部地區數據流通、價值傳遞就顯得尤為重要。

表2 2012—2021年中國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
2.2 城市群差異測算與分解
2.2.1 城市群差異整體情況
下頁表3顯示,數字經濟效率的群內差異較大的有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哈長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寧夏沿黃城市群以及北部灣城市群,差異較小的有天山北坡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山東半島城市群。整體來看,城市群群內差異在時間序列上是上下波動的,說明數字經濟在過往年份的發展并不穩定,但這種狀況在逐年改善,數字城市群建設的潛能還在持續釋放,全國城市群數據一張網,探討數字化發展中存在的城市群區域性問題及其解決之道必將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

表3 2012—2021年19個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的群內差異
2.2.2 差異來源
下頁表4 顯示了2012—2021 年中國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總體差異來源及其貢獻。根據表4可知,19個城市群在樣本期內的總體基尼系數均值為0.217,從基尼系數發展進程來看,2014年和2017年均出現較大降幅,其余年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動,在2015 年19 個城市群的數字經濟效率的地區差異最大,此時基尼系數為0.289,2017年地區差異最小,此時基尼系數為0.170。整體來看,區域間差異在2013 年和2015 年對總體基尼系數的貢獻率最大,其余年份則是超變密度對總體差異影響最大。從演變過程看,區域內差異貢獻率基本上在0.065上下浮動;區域間差異貢獻率從2012 年的0.395 上升到2021 年的0.440,其中在2013年和2015年一度超過超變密度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超變密度的貢獻率從最初的0.536 降至0.497,最大貢獻率出現在2014 年,除2013 年和2015 年之外,超變密度始終是總體差異來源里貢獻率最大的部分,說明城市群間存在的交叉重疊問題是造成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總體差異的重要原因。

表4 城市群數字經濟發展效率的來源
2.3 數字經濟效率地區分布的動態演進
2.3.1 基于傳統Markov鏈的狀態轉移分析
表5 將中國城市群不同數字經濟效率的城市劃分為狀態Ⅰ(低水平地區)、狀態Ⅱ(中低水平地區)、狀態Ⅲ(中高水平地區)和狀態Ⅳ(高水平地區)四個等級。由表5可知,各水平城市維持原有狀態的概率較高,數字經濟發展存在“俱樂部趨同”現象,但是各城市發生狀態轉移的概率也較大,今后應注重帶動高水平以下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促進城市群數字經濟協同發展。

表5 數字經濟效率的傳統Markov鏈轉移概率 (單位:%)
2.3.2 基于空間Markov鏈的狀態轉移分析
由表6可知,數字經濟高水平和低水平地區發展趨勢相反。具體來看,當鄰居數字經濟效率等級為低水平時,Ⅰ類至Ⅲ類地區分別有25.8%、25.0%和8.3%的概率上升一級;Ⅰ類和Ⅱ類地區存在25.8%和27.5%的概率上升兩級,Ⅰ類地區有33.9%的概率上升三級;Ⅱ類至Ⅳ類地區存在32.5%、33.3%和22.2%的概率下降一級,Ⅲ類和Ⅳ類地區存在41.7%和11.1%的概率下降兩級,Ⅳ類地區有44.4%的概率下降三級。當鄰居數字經濟效率等級為高水平時,Ⅰ至Ⅲ類地區存在23.5%、20.8%和22.2%的概率上升一級;Ⅰ類和Ⅱ類地區存在41.2%和20.8%的概率上升兩級,Ⅰ類地區存在17.6%的概率上升三級;Ⅱ至Ⅳ類地區存在37.5%、33.3%和19.1%的概率下降一級;Ⅲ類和Ⅳ類地區存在22.2%和20.6%的概率下降兩級,Ⅳ類地區存在26.5%的概率下降三級。

表6 數字經濟效率的空間Markov鏈轉移概率
3 結論與建議
本文構建了數字經濟效率評價指標體系,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數測算城市群地區差異,運用Markov鏈估計方法分析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的動態時空演進趨勢和規律。得到以下結論:(1)從數字經濟效率的測度結果來看,中國城市群的數字經濟效率表現出空間上的非均衡性。(2)從Dagum 基尼系數測度的地區差異來看,超變密度在城市群總體差異中的貢獻基本上是最大的,是造成地區差異的主要因素,說明城市群間存在的部分交叉重疊問題是造成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總體差異的重要原因。(3)從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的動態演進來看,各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并不十分穩定。
為解決我國城市群內部分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存在的無效率狀態,本文提出以下建議:第一,針對中國城市群的數字經濟效率表現出的空間非均衡狀況,應當打通數據壁壘,強化城市群間高質量數據要素供給。城市群內部城市之間應有效拓寬數字經濟發展的合作渠道,加快區域貿易數字化發展,打破區域行政、技術和協議壁壘,城市群之間應統一標準,推動數據資源標準體系建設,形成完整貫通的數據鏈,創建良好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第二,針對數字經濟發展總體差異很大部分來自城市群之間交叉重疊問題的情況,需要著重優化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區域云網協同和算網融合發展,推進基礎設施智能化升級。城市群內存在中心城市和省會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遠遠領先于其他城市的現象,各城市群存在或輕或重的極化現象,因此需要最大限度地發揮中心-副中心城市對城市群內其余城市數字經濟發展的引領帶動作用,充分實現其對周邊城市或地區的輻射效應。第三,針對城市群數字經濟效率的動態演進規律,應推動數字經濟普惠共享發展,把握信息通信業以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為主線,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加快城市群內城市數字基礎設施向農村覆蓋延伸,使城鄉要素能雙向有效自由流動,完善鄉村地區及偏遠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形成以城帶鄉、共建共享的數字城鄉融合發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