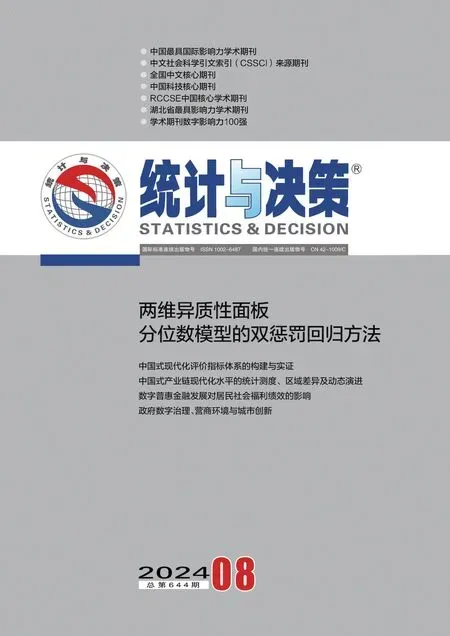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行業差異及分布動態演進
閆永蠶,李 健,徐 藝
(1.天津理工大學 管理學院,天津 300384;2.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 研究生處,天津 300222)
0 引言
全球制造業競爭態勢和競爭格局都在不斷發生變化,各國高度重視制造業發展優勢,積極實施“再工業化”戰略,以搶占未來產業發展制高點。從國際形勢來看,制造業關系著國家綜合實力提升和國際競爭力地位,產業發展格局的不斷變化,考驗著我國制造業發展的韌性和應變能力,制造業的發展水平成為衡量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標志[1],然而,相比發達國家,我國制造業不具備質量效益優勢。走量質齊升、雙管齊下的制造強國之路,是新時代我國制造業的重點任務。
制造業發展深受各國重視,澳大利亞制造業不斷通過數字化、服務一體化與可持續發展提高制造業資源配置效率,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2]。俄羅斯合理調整經濟政策,在優化經濟結構過程中,樹立新的工業化發展理念,提升制造業發展水平[3]。我國較多學者采用全要素生產率測度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但評價結果不穩定且具有片面性。Yu 等(2022)[4]采用灰色動態雙激勵決策模型測算了長江經濟帶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Wang 等(2022)[5]基于省域面板數據得出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穩步提升,70%的省份制造業均處于低質量發展階段,且區域差異大。毛夢偉和施進發(2021)[6]以長江經濟帶11 個省份為例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評價,認為11 個省份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差異明顯。劉怡君和方子揚(2021)[7]測度了108個地級市的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得出長江經濟帶上、中、下游城市的發展水平極不均衡,且僅有江蘇省的六大發展維度較均衡。蘇永偉(2020)[8]多維度評價了中部地區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認為中部六省的發展水平不斷提升,但各項指標的變化態勢存在顯著差異。楊浩昌等(2021)[9]基于2011—2018 年的動態面板數據測度了全國、三大地區及各省份的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強調了我國制造業“量”的發展水平高于“質”的水平。王中亞(2018)[10]、段國蕊和于靚(2021)[11]分別對河南、山東的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了評價。
總之,制造業高質量不僅需要區域間協調發展共同提升發展質量,還需要各行業間形成均衡發展的穩定局面。從現有研究來看,多數學者以省域為研究對象進行高質量評價,對制造業各行業的高質量發展差異關注較少,少數學者從行業角度進行了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評價[12],但未揭示各行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差異的來源及原因。因此,本文在構建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理論模型的基礎上,對制造業28 個行業的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度,揭示了其分布動態規律及行業差異來源,以全面反映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情況。
1 理論模型與指標體系構建
1.1 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理論模型
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是對產業量與質的綜合權衡,擴展量的核心在于數量要增長、規模要龐大,提升質的重點在于技術要先進、產品要高端、生產要智能。當制造業整體發展現狀能滿足技術發展要求,符合生態效率標準,處于價值鏈高端才表明制造業走向高質量階段。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實質是污染少、效率高、質量高、技術高的有機統一,是在國內外發展環境的不確定性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雙重制約下,在經濟、生態、社會、政策和市場五大發展環境中,追求以綠色制造與安全生產為前提,創新發展與高端轉型為動力,協調發展與資源共享為核心的高端、公平、優質、高效、穩定的產業發展系統。在復雜的系統中也需充分重視系統內部的要素投入、技術創新、結構調整等發展條件的平衡性,以不斷促進制造業實現動力變革、效率變革和質量變革,進而使制造業能達到供需平衡發展、創新發展、綠色發展、智能發展、高端發展,滿足制造業高效率、高品質和高質量的終極目標。
1.2 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結合制造業高投入、高回報、高技術和高質量的特性,參考黃順春和張書齊(2021)[13]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的綜述與整理,從規模發展潛力、經濟創造能力、對外開放程度、科技創新活力、綠色發展水平、高端轉型實力及社會貢獻能力7 個維度構建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表1 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方法
2.1.1 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方法
基于熵權法與TOPSIS法構建的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動態評價模型如下:
初始矩陣構建。研究采用時序立體數據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全面評價,設選取n個評價對象(y1,y2,…,yi),m個評價指標(x1,x2,…,xj),k個不同年份(z1,z2,…,zt)的面板數據,即每一年(t=1,2,…,k)每個行業(i=1,2,…,n)的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指標(j=1,2,…,m)的取值為,構成的時序立體數據矩陣為。
指標標準化處理。由于各指標的量綱不同,采用極差標準化方法對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得到標準化矩陣。
計算指標權重。采用熵權法對制造業高質量指標進行賦權,各指標權重的計算式如下:
確定各指標中的正負理想解。各指標的正、負理想解如下:
求解各評價對象與正、負理想解之間的歐幾里得距離,計算式為:
2.1.2 行業差異分解方法
采用Dagum 基尼系數及其分解測度制造業各行業高質量發展的差異來源及其貢獻,得出樣本期內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在行業間的差異變化趨勢,揭示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組內差異及組間差異。Dagum 基尼系數分解法可按照子群分解的方法分為:組內差異、組間差異和超變密度[14]。通常,總體基尼系數是組內差異貢獻、組間差異貢獻以及超變密度貢獻的總和,且求得的基尼系數越小表明地區間的差異越小,反之,則差異越大。由總體的基尼系數(G)、組內差異(Gjj)和組間差異(Gjh)的基尼系數可得到各行業組內差異Gw、組間差異Gnb和超變密度Gt為:
式(7)中,pj=nj/n,sj=njYˉj/nYˉ,j=1,2,…,q。式(8)、式(9)中。Djh是行業組j和行業組h間的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互動影響;djh表示行業組間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差值,表示行業組j和行業組h間所有Yjl-Yhr>0 的樣本值加總的數學期望;pjh表示超變一階矩,是所有Yhr-Yjl>0 的樣本值加總的數學期望。Djh、djh、pjh可表示為:
其中,函數Fj和Fh分別表示行業組j與行業組h的累計密度分布函數。
2.1.3 行業動態演進評價方法
核密度估計法是一種非參數的估計方法,能擬合樣本數據的分布情況,反映分布形態,應用于經濟、社會等一些空間分布不均衡的現象分析中,具有應用范圍廣、反映現象精準、穩健性強等特點。本文應用高斯核函數對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分布動態進行估計[15],為提高估計精度,需選擇較小的帶寬值。在核密度估計中,不僅可看出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分布位置和分布形態,還能通過核密度的延展性掌握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行業差異大小,當繪制的核密度圖拖尾較長時,表明我國制造業的行業差異越大。此外,通過波峰數量的個數可判斷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是否具有極化現象。
2.2 行業類型劃分
根據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754—2017)把制造業28個行業作為研究對象,為揭示各行業的發展情況,借鑒汪芳和石鑫(2022)[12]的方法,通過創新研發投入強度反映各行業的技術需求力度,將28 個行業劃分為低技術制造業、中技術制造業及高技術制造業3大類型。由于制造業行業名稱復雜,為方便后續分析,將各行業賦予相關代碼,如表2所示。

表2 制造業行業類型劃分與代碼
2.3 數據說明
本文數據庫源于《中國工業統計年鑒》,其中2018 年制造業各行業數據由《中國經濟普查年鑒》查得,2017 年的數據由線性插值法進行補充。由于研究期限為2010—2020 年,年鑒中2012 年將橡膠制品業與塑料制品業合并為橡膠和塑料制品業,而將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分為汽車制造業與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制造業。因此,對2010 年和2011 年的橡膠制品業與塑料制品業加總得到各年份的橡膠和塑料制品業,將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按2012年汽車制造業與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制造業在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中的占比求得2010與2011年汽車制造業與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制造業的相關數據。
3 評價結果分析與差異比較
3.1 制造業各行業高質量發展評價
采用熵權TOPSIS 法對28 個行業的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得到2010—2020 年制造業行業的發展質量水平,測度結果如下頁表3所示。由于等距劃分不符合我國制造業各行業發展現狀,綜合各類文獻以實際評價結果為基礎,將0.3設置為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界線,增大了制造業各行業質量提升空間,有利于促進各行業向更高水平發展。設定綜合評價值在[0.3,1]的為高質量行業,因此綜合評價值在[0.1,0.3)的為中質量行業,綜合評價值在[0,0.1)的為低質量行業。

表3 制造業28個行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值及排名
由表3可知,從低、中、高質量3類行業看,中、高質量與低質量行業的差異較大,發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高技術制造業>中技術制造業>低技術制造業,高技術制造業的發展形勢良好,發展水平約為低技術制造業的兩倍,2020 年其高質量發展水平已經達到0.311,突破了質量的轉型,由中質量轉為高質量發展階段。中技術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下降趨勢后又小幅提升,一直在0.2 上下徘徊,屬于中質量發展階段,因此,中技術制造業應該掌握行業發展特色,揚長避短才能實質性地提升發展質量。但低技術制造業出現略微降低的狀態,且一直處于中質量發展階段較低的水平。由上述分析可看出,我國高技術制造業的創新引領作用得以發揮,但中、低技術制造業應不斷提升發展質量。為進一步比較3類行業的變化趨勢,繪制了制造業3 類行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均值及年均變化率如圖1所示。

圖1 制造業3類行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均值及年均變化率
由圖1 可以看出,3 類行業均表現出波動變化趨勢,2012 年3 類行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變化率均出現負增長現象,2013 年3 類行業的高質量發展水平大幅增長,2014—2017年波動變化狀態后,2018年呈現下降趨勢,但在2018 年低技術制造業的負增長率高于中、高技術制造業,2019—2020 年中、高技術制造業出現正增長趨勢,但低技術制造業的負增長率有所減小。
從28 個具體行業高質量發展變化情況來看,2010—2020年大部分行業的時序演變規律屬于平穩波動無明顯提升狀態及波動微降低狀態,僅有醫藥制造業(C27)與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C39)呈現較大幅度提升。表3中的數據顯示,2010年28個行業中9個行業屬于低質量階段,占總行業數的比重為32.14%;13個行業屬于中質量發展階段,占總行業數的比重為46.43%;6 個行業屬于高質量發展階段,占總行業數的比重為21.43%。2020年28個行業中部分行業實現了“低→中→高”的質量跨越,其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C30)在2020年的高質量發展值達到0.306,從中質量發展階段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C40)2020年提升到了0.104,由低質量發展階段轉入了中質量發展階段。從3 個質量階段的行業2020 年的高質量發展水平看,低質量發展階段中8個行業中有7個屬于低技術制造業,另外一個是高技術制造業中的化學纖維制造業(C28),而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行業中6 個行業都屬于高技術制造業。
由制造業各行業的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均值排名看,排名前10的行業分別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C39),汽車制造業(C36),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C38),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C31),通用設備制造業(C34)、醫藥制造業(C27),化學纖維制造業(C28)、專用設備制造業(C35),農副食品加工業(C13),橡膠和塑料制品業(C29)。其中,前3名均屬于高技術制造業,中技術制造業有兩個行業,低技術制造業中僅農副食品加工業(C13)排名前十,原因在于近年來國家在高新技術產業率先轉型方面效果顯著,對農產品質量的提升取得初步成效,并且對農副食品的扶貧政策的實施帶動了其經濟價值的提升。隨著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農副食品出口率的提高,對外開放程度隨之提升,多維度推動了我國農副食品制造業的高質量轉型。對于低技術組內的紡織業(C17)而言,其發展質量也屬于中質量偏上水平,均值排名14,原因在于我國紡織業不斷向紡織強國靠攏,在綠色、開放、創新等方面都受到國家重視,節能減排效率顯著,科技支撐力度增強,先進的紡織裝備賦能紡織業不斷走高質量發展道路。
綜上可知,我國制造業行業的高質量發展水平差異較大,高技術制造業與低技術制造業的差距尤為突出,基本遵循了高技術-高質量、低技術-低質量的規律,低質量行業尤其需注重技術創新的驅動作用,通過加大研發投入力度,提高先進技術應用,加快實現制造業整體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3.2 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行業差異分解
基于上述測度值可看出,制造業各行業的高質量發展水平差異較大,進一步采用Dagum基尼系數法測度了行業差異來源及其貢獻率,為清晰地揭示差異變化趨勢,依據基尼系數結果繪制了制造業行業高質量發展總體差異及低、中、高技術制造業組內差異演變趨勢,見下頁圖2。

圖2 制造業行業高質量發展總體差異及組內差異演變趨勢
由圖2可知,制造業行業總體差異在樣本觀測期內呈現“W”型的變化態勢,變化幅度較小,由2010 年的0.340增長到2020年的0.379,僅僅上升了0.039個百分點。從低技術行業組看,組內差異值呈現波動下降的態勢,表明低技術行業組內各行業的發展質量差距在不斷縮小,由2010 年的0.255 降低為2020 年的0.192,下降了0.063 個百分點。中技術行業組內差異在2018年之前呈現微降趨勢后,2020年有微升狀態,但整體中技術組內差異比低技術組內差異小。對于高技術組內差異而言,2010—2018 年呈現上升趨勢,但在2018年出現拐點,樣本研究末期出現了明顯下降趨勢,但高技術行業組內的差異是3類行業中較大的一組,其原因主要在于高技術行業的發展質量普遍較高,但該組化學纖維制造業(C28)與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機械制造業(C40)由于規模發展潛力弱、對外開放程度低、科技創新實力不足等原因導致發展質量整體偏低,造成高技術行業組內的差異較大。我國應重點提高上述兩個行業的發展質量,以促進高技術制造業向更高質量發展。
為對比行業組間差異情況,繪制了制造業行業組間差異雷達圖,如圖3所示。可以看出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行業組間差異由大到小依次是高-低、中-低及高-中,但在2015—2017 年,高-中技術行業組間差異超過了中-低技術行業組,2018 年后高-中技術行間差異又變為3 組組間差異最小的狀態。高-低技術組的組間差異最大,均值為0.471,中-低技術組間差異均值為0.327,高-中技術組間差異均值為0.299。組間差異大的原因為高技術行業在資金與技術研發投入中都具有領先優勢,并且其高端化水平與對外開放度均能夠為行業發展創造更大的優勢,而低技術行業組則在規模與技術上均不占優勢,高質量發展情況較不理想,因此,組間發展差異較難縮小。

圖3 制造業行業高質量發展組間差異圖
為明確我國制造業行業差異的主要來源,結合計算所得的組內、組間及超變密度貢獻值,在圖4 中繪制了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行業差異貢獻率。

圖4 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行業差異貢獻率
由圖4可知,行業組間差異始終是我國制造業行業高質量發展差異的主要來源,在總體差異中的占比始終超過了54%,2020年行業組間差異高達67.23%,表明高技術行業組發展質量遠超過了低技術行業組,我國在高質量發展進程中尤為重視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對低技術行業的重視力度不夠,且低技術行業多為傳統制造業,發展模式與技術改進均無得到突破性進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應重視高技術與低技術行業的均衡發展,行業發展質量懸殊造成的不平衡現象會影響制造業整體的高質量水平。組內差異是影響我國制造發展差異的第二大因素,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在2016年后有所回落,但占比仍在23%以上。因此,行業組內差異縮減存在一定的空間。超變密度在總體差異中的貢獻率則逐年遞減,為促進我國制造業行業差異縮小,應以縮減行業組間差異與組內差異為主。
3.3 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分布動態演進規律
由于制造業發展環境復雜,行業異質性強,為揭示制造業行業差異的絕對差異和分布動態演進規律,采用核密度估計法對制造業行業發展的動態演進特征進行分析,得到了制造業行業整體、高技術制造業、中技術制造業及低技術制造業的分布動態、分布規律、分布延展性、波峰數目等關鍵屬性。各行業的動態分布規律如圖5所示。

圖5 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行業分布規律
由圖5 可知,從制造業整體演變特征來看,分布中心位置隨著時間的增長逐漸右移,表明我國制造業行業的高質量發展水平逐漸提升。主峰分布形態出現高度增大、寬度變窄的趨勢,但依然屬于右拖尾情況;從波峰數目看,存在4 個波峰,且多個側峰值不斷提高,說明我國制造業具有顯著的梯度效應。
從高技術行業組的演變特征看,分布位置不集中,雖然呈現右移趨勢,但波峰較多且復雜,存在分化式發展情況,說明我國高技術制造業行業組應注重平衡化發展。對于中技術行業組而言,主峰呈現先提升后降低的狀態,核密度曲線呈單峰分布形式,表明中技術行業組不存在多級分化現象。而對于低技術行業組而言,最初由一個主峰與一個側峰組成,但逐漸演變為一個主峰,說明低技術行業組逐漸趨于集中發展狀態。由此可見,我國制造業行業高質量發展水平近年來在政策驅動下,高質量雖然有部分行業有所提升,但真正地解決行業間的差異問題任重道遠。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通過對制造業行業的測度與分析得出:2010—2020年制造業整體高質量發展水平逐漸提升,高技術行業組質量提升速度較快,2020 年基本實現中質量向高質量的轉型,但中、低技術行業多數呈現平穩波動無明顯提升狀態,部分發展質量有所下降;制造業各行業基本遵循高技術-高質量、低技術-低質量的規律,行業差異大,總體差異在逐漸擴大,且高技術行業組內差異最大,中技術行業組內差異最小,導致行業差異大的主要原因是行業組間差異,貢獻率在2020年高達67.23%;從分布動態演進規律看,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梯度效應,高技術行業組存在分化式發展趨勢,發展水平不均衡,而中、低技術行業組分布集中,不存在多峰極化現象,但發展水平未呈現明顯右移趨勢。因此,提升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應發揮高技術行業組的優勢,重點提升中、低技術行業組的發展質量,縮小中、低技術行業組與高技術行業組的差異。
4.2 建議
針對制造業行業高質量發展差異大的現象,為有效提升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提出以下建議:
(1)實施創新發展戰略,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創新能帶動制造業開發新的生產技術,強化綠色創新技術應用,中、低技術行業組需重視科技創新在制造業質量轉型的驅動作用,推動企業適應發展需求,掌握核心技術,增強企業競爭力。政府應積極倡導企業科技創新,推進制造業在科技創新中培育新型產業,改造傳統產業。
(2)堅持綠色發展原則,構建綠色制造體系。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實現制造業生產環節節能減排,構建綠色制造體系。高度重視制造業各行業中污染排放大的行業,積極推進綠色技術應用,逐漸改變制造業高污染、高消耗的固化思維,加強重污染省域和重污染行業的綠色監督,鼓勵制造業綠色共性技術的研發,扎實推進制造業清潔生產。
(3)加深對外開放程度,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把握“引進來”與“走出去”均衡發展,在開放合作中形成國際競爭優勢,向價值鏈高端攀升。高度重視制造業引資、引技、引智的質量,把好“引進來”的質量關。持續提升“走出去”水平,加快“走出去”步伐,在市場的主導作用下,促進產品出口,緩解制造業產能過剩現象,助力制造業全面提質增效。
(4)形成共建共享平臺,加快高質量發展步伐。構建制造業信息技術共建共享平臺,使民眾參與到生產加工的監督中,使產品充分滿足用戶需求并為人民所享。在技術研發及生產工藝優化環節,實現資源共享、信息共享、生產共享及模式共享,推動多行業均衡發展,加快制造業高質量轉型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