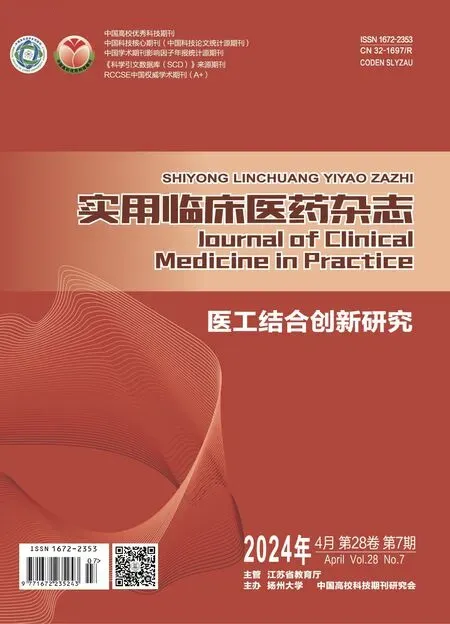鐵代謝與2型糖尿病相關性及胰高血糖素樣肽-1調控作用的研究進展
任志芳, 任 潔, 劉 睿,2, 肖金鳳,2, 秦 潔,2
(1. 山西醫科大學第五臨床醫學院, 山西 太原, 030012; 2. 山西省人民醫院, 山西 太原, 030012)
2型糖尿病(T2DM)是一種以糖脂代謝紊亂為主要表現的慢性代謝性疾病,發病過程可能伴隨胰島β細胞數量減少、功能減退及凋亡增加。胰島β細胞多因素致病反應是T2DM發病的重要機制,包括細胞鐵代謝障礙(鐵沉積、鐵過載、鐵死亡等)、內質網應激、細胞膜損傷和受體介導的信號轉導異常等多種病理生理過程。目前,多種胰高血糖素樣肽-1(GLP-1)受體激動劑或類似物已被廣泛應用于臨床,可改善胰島β細胞鐵代謝及糖尿病相關慢性并發癥,為T2DM及其并發癥的防治提供了新思路。
1 鐵代謝障礙在T2DM及其并發癥中的作用機制
鐵代謝障礙涉及鐵沉積、鐵過載、鐵死亡、鐵自噬等多種病理生理過程,在T2DM等多種代謝性疾病的發生和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研究者在遺傳性血色病(HH)中觀察到鐵代謝與T2DM的關系, HH是由先天性鐵過多沉積于肝細胞、胰腺上皮細胞、心肌細胞、關節軟組織細胞等引起相應臟器損傷的疾病,近半數患者確診時已存在T2DM, 且患者發生T2DM的風險是普通人的7倍[1]。目前, HH相關性糖尿病的發病機制尚未完全闡明,胰島素缺乏和胰島素抵抗被認為是主要的致病因素, HH患者胰島β細胞功能衰退,不能及時調控胰島素分泌水平,若存在胰島素抵抗,則糖尿病發生風險顯著增加[2]。研究[3]表明,胰島β細胞及靶器官中鐵代謝障礙、內質網膜損傷和受體介導的信號轉導異常等病理生理過程在T2DM及其慢性并發癥的發生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1.1 鐵沉積、鐵過載參與T2DM的作用機制
鐵代謝障礙與T2DM相關,尤其是胰島細胞中的鐵沉積、鐵過載。鐵沉積是胰島細胞炎癥的重要標志之一,可預測糖尿病發生風險[4]。鐵過載又稱鐵負荷過多,是指鐵的供給量超過需要量,可導致機體內總鐵量增加并過量沉積于組織器官中,引發多種器官功能障礙[5]。
研究[6]證實,鐵沉積、鐵過載會顯著增加糖尿病發生風險。外源性輸血所致鐵過載和內源性血清鐵濃度升高、胰島β細胞鐵蛋白沉積均會導致胰腺組織鐵過載,進而增加T2DM發病風險。這一現象亦符合T2DM中胰島β細胞凋亡的病理機制,即胰島β細胞通過鐵轉運蛋白增加鐵輸入,引發鐵沉積、鐵過載[7], 進而影響調控胰島素分泌的8-氧代鳥嘌呤DNA糖基化酶(OGG1)和突觸結合蛋白7(SYT7)。鐵過載通過擾亂OGG1對SYT7的轉錄調控抑制胰島素分泌,并損害胰島β細胞功能[8]。
此外,鐵沉積和鐵過載會引起活性氧增加、巨噬細胞轉變為促炎表型,進而誘發胰島細胞線粒體功能障礙[9]、氧化應激反應和炎癥反應[10],干擾胰島素合成與分泌,影響體內葡萄糖穩態的調控。這對T2DM疾病進展中的胰島β細胞損傷具有重要作用,且與T2DM相關脂肪變性及糖尿病晚期慢性并發癥(例如糖尿病性心肌病、視網膜病變、腎病和神經病變)具有一定相關性,可顯著升高糖尿病及其并發癥的致死率[11]。相反,限制鐵攝入可改善胰島素抵抗小鼠的胰島β細胞功能及糖代謝[12]。
1.2 鐵死亡參與T2DM的作用機制
鐵死亡是一種以細胞內脂質過氧化及鐵沉積、鐵過載為特征的鐵調節障礙誘導的細胞死亡,不同于細胞凋亡和細胞壞死,其本質是谷胱甘肽耗竭,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4(GPX4)活性下降,脂質氧化物不能通過GPX4催化的谷胱甘肽還原酶反應代謝,此后二價鐵離子氧化脂質產生活性氧增強細胞氧化應激反應,引發鐵死亡,使得胰島素信號轉導異常,進而增加T2DM發生風險[13]。因此,控制鐵死亡的重要思路之一是保護細胞抗脂質過氧化的能力,尤其是GPX4的功能。
鐵死亡所致胰島β細胞功能障礙具有以下特點: ①鐵死亡是一種鐵依賴性的細胞死亡形式。鐵死亡與機體內鐵沉積、鐵過載密切相關,研究[14-15]證實糖尿病患者各種組織中存在不同程度鐵沉積,可能進一步導致鐵死亡。②鐵死亡是一種由脂質氧化還原失衡所驅動的細胞死亡形式。由于機體內胰島β細胞抗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和過氧化氫酶等)表達水平相對較低,活性氧易累積,極易引發鐵死亡[16]。ZHOU Y[17]發現,桑葉提取物隱綠原酸(CCA)可通過提高GPX4水平,激活Xc-/GPX4系統以及核因子E2相關因子2(Nrf2)通路,改善T2DM誘導的脂質過氧化及氧化應激過程,抑制鐵死亡,發揮抗氧化及保護作用。CCA還可減輕高血糖引起的胰島β細胞損傷,促進胰島β細胞再生[18]。其他研究[14,19]也得出類似結論,即抑制脂質過氧化可有效改善T2DM模型大鼠胰島β細胞的鐵死亡現象。另有研究[20]表明,鐵代謝與脂聯素(ADPN)水平也存在相關性,ADPN可通過糾正脂肪酸氧化/過氧化物失衡誘導的鐵死亡,改善妊娠糖尿病所致胎盤損傷。因此,維持脂質氧化還原平衡對于糖代謝穩態的調控至關重要。③線粒體自噬可調控鐵死亡。相關途徑的激活可導致胰島素分泌功能障礙[13],研究[21]發現水飛薊賓可以增強Pink1/Parkin介導的線粒體自噬,進而抑制胰島β細胞鐵死亡。④鐵死亡具有可調節性。鐵死亡抑制劑(鐵抑素-1/去鐵胺)或鐵螯合劑(槲皮素)可逆轉細胞鐵死亡過程,發揮抗炎、抗氧化、減輕胰島β細胞氧化應激等作用[18,22-23],這將成為防治T2DM的新途徑之一。
1.3 鐵死亡參與T2DM相關并發癥的作用機制
鐵死亡和鐵素體吞噬在糖尿病相關并發癥(糖尿病腎病、糖尿病性心肌病、糖尿病性動脈粥樣硬化、糖尿病卒中及神經退行性改變等)的發生和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24-27], 這可能與鐵代謝參與糖尿病誘導的內皮功能障礙有關,抑制鐵死亡對糖尿病誘導的心肌細胞缺血再灌注損傷具有保護作用[28]。然而,鐵死亡參與糖尿病誘導的內皮細胞功能障礙的具體機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確。在糖尿病進程中,p53信號通路被激活,并進一步激活p53-XCT(系統XC-的底物特異性亞基)-谷胱甘肽(GSH)軸,導致GSH合成減少,引發內皮細胞鐵死亡,繼而導致內皮功能障礙[29]。目前,關于鐵死亡在T2DM相關內皮功能障礙中作用的基礎研究及臨床研究相對較少,未來可聚焦這一領域深入探討,為藥物研發及臨床診療提供新思路。
1.4 鐵缺乏參與T2DM的作用機制
盡管大量研究證明鐵過載與糖尿病風險相關,但值得注意的是,缺鐵與糖尿病另一關鍵風險因素肥胖也存在關聯,肥胖合并缺鐵狀態更易因胰島素分泌不足和胰島素抵抗的協同作用誘發T2DM[30]。鐵調素水平上升及其引發的功能性缺鐵狀態,可加劇胰島素抵抗和葡萄糖耐量異常。鐵調素是鐵穩態的關鍵調節因子,其與鐵蛋白對胞漿內生物活性鐵含量的變化非常敏感; 在糖尿病和肥胖癥中,促炎信號通路的激活會直接促進鐵調素和鐵蛋白的合成,導致鐵調素水平升高,阻斷十二指腸對鐵的吸收和網狀內皮系統內源性儲存鐵的釋放,故肥胖患者血清鐵水平較低。血清鐵蛋白濃度與雙歧桿菌、乳桿菌和微細桿菌的豐度呈負相關,與擬桿菌和普氏菌的豐度呈正相關,在病理環境中,上述腸道微生物群的代謝活性下降,與喂食正常食物的大鼠相比,喂食缺鐵飲食大鼠的代謝產物(丁酸鹽、丙酸、短鏈脂肪酸)水平顯著降低,不能有效刺激GLP-1調節血糖,更易出現胰島素分泌異常和葡萄糖穩態失調情況[8, 31]。由此表明,炎癥介導的鐵調素和鐵蛋白水平升高是糖尿病患者功能性缺鐵的主要驅動因素,而這些鐵生物標志物的增加及由此產生的功能性缺鐵狀態可能進一步加劇胰島素抵抗和葡萄糖耐量異常[32-33]。
2 GLP-1對T2DM中鐵代謝的調控作用
GLP-1是一種由腸道L細胞分泌的激素,主要靶器官是胰腺,對β細胞和α細胞具有雙向調節功能。GLP-1受體(GLP-1R)在多種器官和組織中廣泛分布,包括中樞神經系統、心血管系統、胃腸道、肌肉和皮膚等。GLP-1具有葡萄糖濃度依賴性降糖作用,其受體激動劑(GLP-1RA)能模擬GLP-1的生理作用,是治療糖尿病與肥胖癥的重要藥物,對心血管系統、中樞神經系統及腎臟等亦有保護作用[34]。近年來,隨著對腸促胰素作用機制的深入了解, GLP-1RA藥物的研發不斷取得突破,從最初的短效GLP-1藥物迭代至現今的長效GLP-1藥物,治療范圍亦從降糖拓寬至減重,并有望拓展至慢性心血管疾病、慢性腎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和阿爾茨海默病等領域。
2.1 GLP-1改善胰島β細胞功能
GLP-1RA具有多重生物學效應,可通過消除糖脂毒性、促進胰島β細胞新生及抑制其凋亡等作用,改善T2DM患者胰島素分泌功能和血糖控制水平,實現“標本兼治”的終極目標。
2.1.1 促進胰島β細胞新生及抑制其凋亡: 一方面, GLP-1RA通過與G蛋白α亞基耦合,激活環磷酸腺苷(cAMP)/蛋白激酶A(PKA)信號通路,調控胰島素受體底物2基因表達,從而促進胰島β細胞新生和抑制其凋亡; 另一方面, GLP-1RA可經原癌基因酪氨酸蛋白激酶反式激活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進而通過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信號通路發揮促進胰島β細胞再生及抗凋亡作用[35]。
2.1.2 促進胰島細胞轉分化: 胰島素抵抗小鼠除了會發生胰腺肥大,還會發生胰腺α細胞和β細胞比例失調、凋亡現象,司美格魯肽可有效促進胰島細胞增殖,恢復胰島大小和α細胞、β細胞比例及功能,使機體維持適宜的葡萄糖、脂聯素、瘦素、胰島素、胰高糖素水平,降低白細胞介素(IL)-1β、IL-6、腫瘤壞死因子等促炎標志物水平,從而減輕胰島素抵抗[36]。原α細胞產生的GLP-1可誘導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21(FGF21)表達, FGF21通過增加 PPAR-γ促進β細胞轉錄因子PDX-1和Ngn-3表達增加(PDX-1、Ngn3是胰腺發育和祖細胞分化為β細胞表型的重要轉錄因子),進而促進α細胞轉分化為β細胞[37]。
2.1.3 改善胰島β細胞外基質: 細胞外基質是由膠原蛋白、纖維連接蛋白、肌動蛋白等多種分子構成的三維網絡結構,其在細胞凋亡、增殖、分化和表型穩定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胰島細胞正常發揮內分泌功能的基礎,在T2DM的發病機制中起關鍵作用。司美格魯肽可有效降低胰島細胞外基質中硫酸肝素蛋白聚糖、透明質酸、硫酸素蛋白聚糖和膠原蛋白水平,同時減少細胞損傷相關淀粉樣蛋白沉積的生成,從而有助于重建適宜胰島功能修復的良好微環境[38]。
2.2 GLP-1通過調控鐵代謝延緩T2DM發生發展
2.2.1 GLP-1減輕鐵沉積、鐵過載: 利拉魯肽、艾塞那肽是臨床常用的GLP-1類似物或GLP-1RA, 均可有效減輕胰島細胞中的鐵沉積、鐵過載并改善胰島β細胞功能,但具體機制有所不同。利拉魯肽可通過降低轉鐵蛋白受體表達和增加鐵輸出蛋白表達而抑制鐵沉積,并通過調控糖尿病小鼠肝臟中Nrf2/HO-1/GPX4信號通路而減少鐵死亡[39-40]。利拉魯肽還可增高血漿脂聯素水平,降低炎性細胞因子和游離脂肪酸水平,進而減少脂肪酸氧化與過氧化物失衡誘導的鐵死亡,且其降低血清游離脂肪酸水平的效果顯著優于其他藥物[41]。艾塞那肽通過促進胰島素分泌,誘導Frataxin和Fe-S簇蛋白表達,降低氧化應激水平,進而改善葡萄糖穩態和線粒體功能,且其對背根神經節感覺神經元具有保護作用[42], 進一步闡明了鐵穩態維持與胰島β細胞功能儲備之間的關系。
2.2.2 GLP-1抑制鐵死亡: 鐵死亡的2大特征是鐵蓄積和脂質過氧化,而活性氧積累則是鐵死亡的中心環節。T2DM發生發展過程中,胰島β細胞脂質過氧化、抗氧化能力降低及線粒體形態結構改變與細胞鐵死亡的病理過程是一致的。利拉魯肽在減輕糖尿病小鼠鐵沉積、氧化損傷、鐵死亡和治療T2DM相關并發癥方面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43]。利拉魯肽可通過逆轉非酒精性脂肪肝中脂質代謝相關基因的異常表達,激活AMPK/ACC通路,有效減少不穩定鐵池和細胞內活性氧的累積,控制脂質代謝并負向調節鐵死亡,從而減輕T2DM相關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情[44-45]。利拉魯肽還可通過提高GPX4和谷氨酸/胱氨酸逆向轉運蛋白的表達,抑制過量酰基輔酶合成酶長鏈家族成員4活性,降低機體氧化應激、脂質過氧化和鐵過載水平,進一步抑制T2DM患者海馬區的鐵死亡,減輕對海馬神經元和突觸可塑性的損害,最終促進認知功能恢復[46]。細胞自噬參與調控鐵死亡過程中鐵依賴的脂質過氧化和活性氧累積,在高糖環境下,利拉魯肽還可通過抑制糖尿病大鼠腎臟細胞自噬和鐵死亡而發揮保護作用[47]。此外, GLP-1在糖尿病所致內皮細胞損傷中發揮保護作用,胡珂昕等[48]發現GLP-1及其小分子片段可減少晚期糖基化終末產物(AGE)誘導的人主動脈內皮細胞(HAEC)鐵死亡,其機制可能與激活LKB1/AMPK信號通路有關。
總之,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鐵代謝紊亂與T2DM及其慢性并發癥的發生發展存在密切聯系,體內低水平鐵與肥胖密切相關,可增加T2DM發生風險。而體內鐵超載可促進氧化應激反應激活和炎癥反應發生,并損傷胰腺β細胞,進而導致T2DM的發生與發展。目前,關于鐵代謝在糖尿病及其慢性并發癥發生發展中具體機制的研究相對較少,未來還需探尋更多的證據支撐鐵代謝作為干預T2DM及其相關并發癥的新靶點。
3 總結與展望
當前研究已證實鐵沉積、鐵過載、鐵死亡等病理性鐵代謝途徑可激活氧化應激、脂質過氧化、細胞自噬、細胞凋亡等生物過程,促進胰島β細胞及靶器官炎癥反應級聯放大,降低抗氧化能力,從而促進T2DM及其并發癥的發生與發展。血清鐵水平較低則可增加肥胖或胰島素抵抗等代謝性疾病的發生風險,因此,適宜的血清鐵水平對維持糖代謝穩態具有重要作用。GLP-1類似物或GLP-1RA已逐漸被廣泛應用于臨床,其在調控機體鐵代謝途徑、改善鐵代謝紊亂所致炎癥反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可進一步促進胰島β細胞增殖及分化,減輕胰島素抵抗,抑制血管內皮細胞損傷及神經細胞退行性變。闡明該類藥物在T2DM及其并發癥防治中的潛在機制,或可為T2DM的精準治療提供新的靶點和思路。但目前關于GLP-1類似物或GLP-1RA改善病理性鐵代謝途徑的基礎研究仍較少,且涉及的信號轉導通路尚未完全明確,有待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