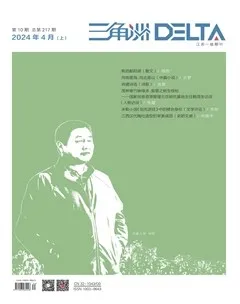作者的真誠讓文學(xué)注入靈魂
真誠是文學(xué)的生命,作者的真誠為文學(xué)注入靈魂。在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是郁達夫的《沉淪》。其中,郁達夫的小說注重“人”內(nèi)心世界的描寫,以坦誠率真的作品感染了讀者。本文主要以郁達夫的作品《沉淪》為研究對象,從文學(xué)活動的視角出發(fā),用辯證的眼光看作者的真誠,分析其對文學(xué)的影響,來探討作者的真誠為文學(xué)注入靈魂這一論題,進而思考當(dāng)下文學(xué)中作者真誠的問題。
關(guān)于真誠及作者的真誠重要性的概述
一、“真誠”一詞的闡釋
真誠,在《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真實誠懇,沒有一點虛假。《說文解字》中,對“真”字的解釋:真,仙人變形而登天也。后人進一步注釋:此真之本義也。經(jīng)典但言誠實,無言真實者。同時,“真”在古時字形較多樣,如“慎”“瞋”“稹”等等,但取“真”聲,多用“充實”之意,引申為真誠。《說文解字》中對“誠”字的解釋:誠,信也。并且在《中庸》中: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注: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在儒家學(xué)說中,“誠”對仁義禮智起著重要作用,首先要表達內(nèi)心的真實,才能進行后續(xù)的探索。
“真”與“誠”構(gòu)成了真誠,在本文中“真誠”表現(xiàn)為一種心理狀態(tài),是一種對待文學(xué)的意圖。真誠是作者寫作緣起的重要一環(huán),寫作緣起影響著文字后續(xù)的表達。雖不以真誠與否去評價一個文學(xué)作品的好壞,但同時要注意到作者真誠對于文學(xué)的重要作用和影響。因此,提出“作者的真誠讓文學(xué)注入靈魂”這一觀點。
二、“作者的真誠”的闡釋
作者的真誠是與藝術(shù)真實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孫紹振指出:“藝術(shù)的真實中就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生活的真實,一個是作家的真誠。二者達到和諧統(tǒng)一時,感染力就強了”“作品中真實既是生活的真實,又是作家的真知、真誠感受”。
作家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決定了他們的創(chuàng)作成果,并且他們后續(xù)對自己所創(chuàng)作的作品的評價也十分重要。作者的真實與作者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是分不開的。作者的真誠表現(xiàn)在作者在創(chuàng)作中真實誠懇的態(tài)度,無論作品成功與否,都能夠坦然真誠地面對。
與此同時,讀者的接受對作者的真誠有重要影響作用。讀者不斷豐富著作品的內(nèi)涵,影響著文學(xué)作品的價值。文學(xué)作品的價值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讀者的閱讀中不斷發(fā)展的。由讀者對文學(xué)作品的影響延伸至讀者群體、社會受眾,整個社會受眾對文學(xué)作品價值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正如余華老師在《文城》發(fā)布會中所說:“每個寫作者都有雙重身份。往前推進故事的時候,是作者;往回檢查問題的時候,是讀者。讀者越來越多時,不可能照顧到所有人的想法,這時,他只需要也只能夠?qū)σ幻x者負(fù)責(zé),那就是他自己。”
三、作者的真誠在文學(xué)中的重要性
文學(xué)是目的與手段的統(tǒng)一,要做到這一點,任何外在的強制都是徒勞的,只需要發(fā)自心底的真誠。我們不能否認(rèn)的是,文學(xué)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被增加上其他附屬價值:利益、金錢、權(quán)力。但這些功利性的“附屬品”終究抵不過非功利性的作者的真誠。
作者的真誠在文學(xué)中的重要性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如果作者對待創(chuàng)作的客觀事實的態(tài)度不真誠,可能會導(dǎo)致文字力量沒有感染力,缺乏力量感,讓讀者感覺,文字是敷衍的,讀與不讀相差意義不大;另一方面,如果作者不真誠地創(chuàng)作,言不由衷,即使再真實的描繪也是蒼白的、無力的,對于作者自身來說,難免不沾惹上世俗化氣息。作者的真誠是對自我的肯定,是對現(xiàn)實的負(fù)責(zé)。作者的真誠影響文學(xué)作品的傳播及其影響。換言之,對文學(xué)缺乏真誠的作者,會遭到文學(xué)的貶斥和淘汰。
“可以肯定的是,一個人僅憑對文學(xué)的真誠并不能保證他成為一個作家。但是對文學(xué)缺乏真誠的人絕對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有出息的作家。”文學(xué)作品的本性是達觀的、超脫的、非功利性的,它承載的應(yīng)該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真誠。
作者在文學(xué)作品中的真誠——以郁達夫《沉淪》為例
《沉淪》的最可愛之處在于,作者以端正的態(tài)度認(rèn)真地描寫了“我”的內(nèi)心,把自己的真誠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沈雁冰在《時事新報·文學(xué)旬刊》中認(rèn)為《沉淪》與《茫茫夜》的主人公“肯自承認(rèn)而且自知”是其可愛之處。
一、郁達夫“作者的真誠”的緣起
郁達夫的“自敘體”小說多取材于自己的生活和經(jīng)歷,寫自己的遭遇和見聞。郁達夫在日留學(xué)期間,受日本“私小說”的影響,傳統(tǒng)文化與外來文化相碰撞而產(chǎn)生了他獨特的風(fēng)格。五四新文化運動,確立了以人文主義為核心的“人學(xué)”。在五四思潮的影響下,部分知識青年開始探索自我。五四前的中國是封建、迷信、故步自封的,有才之士被抑制,自我主觀情感無法釋放。在日本留學(xué)的郁達夫恰好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下,慢慢成長起來,走向文學(xué)道路。郁達夫打破了那種壓抑人性、泯滅欲望的文化傳統(tǒng),將自己的筆觸深入內(nèi)心世界,注重“人”的意義。他逐漸淡化對客觀世界的敘述,轉(zhuǎn)向主觀世界的描繪,帶有濃厚的主觀情緒。
與此同時,郁達夫堅持小說來自生活。“文學(xué)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作者的生活,應(yīng)該和作者的藝術(shù)緊抱在一塊”。小說來源于生活的信念,使郁達夫的文學(xué)作品進一步反映他的創(chuàng)作真誠:“我要把我的生活寫進小說,我的生活就是小說。”對于郁達夫而言,生活和藝術(shù)不過是一種表達的不同側(cè)面。
《沉淪》中的世界是深邃、復(fù)雜、悖論、自我搏斗的。郁達夫把筆觸伸向了在紅塵日常中被藏起來了的那個隱秘的世界。郁達夫在自述上取不虛偽的態(tài)度,不加掩飾地將自己肉的欲望展現(xiàn)出來,他是率真與坦誠的。再加上作者對肉的沉淪時刻加以病的界定,讓人們感覺到他的不得已而為之,最后由此帶來的精神上的苦痛、道德上的折磨又賦予原本就可以被原諒的復(fù)雜的破戒行為以受戒的莊嚴(yán)。郁達夫的小說不僅有對時代真實、生活真實的反映,還具有對作者本身的觀照,作者進行了大膽的自我暴露。
二、自我的寫真,真誠的追求
郁達夫的《沉淪》,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他曾表示寫這本書完全是不得不寫,只是順著自己的情感思緒如行云流水般地寫了下去,也不用考慮什么技巧和修辭,這些他統(tǒng)統(tǒng)不管。馬克思說:“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理智地復(fù)現(xiàn)自己,而是能動地、現(xiàn)實地復(fù)現(xiàn)自己,從而在他所創(chuàng)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
《沉淪》以“伊”為主人公在日留學(xué)的經(jīng)歷為主線展開自我的寫真與真誠的追求,講述了“伊”因為愛情的不可得,又不堪忍受異族的欺辱,最后投海自殺的故事。開篇第一句“他近來覺得孤冷得可憐”,一句話帶入作者的內(nèi)心世界。小說主人公是一個完全沉浸在自我感覺、認(rèn)知中的人,在感覺之外,他開始想象與幻想。
其中,對自我情感的真切表露和性文化的直抒胸臆是作者的真誠最直觀的體現(xiàn)。在郁達夫的《沉淪》中,他無所顧忌地表達作家們想要說的心里話,名譽、知識都不是他想要的,只要求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沉淪》里的“他”“覺得女人口里吐出來的氣息,也熱乎乎地噴到他的面上來。他不知不覺地把這氣息深深地吸了一口。他的意識感覺到他這種行為的時候,他的面立刻紅了起來”,此處就描寫了他在理性地意識到自己下意識的行為后羞怯的、不知所措的心理。而到文章的最后,主人公喊出:“祖國呀祖國!……你快富強起來!強起來罷!”這種直接的表露,讓我們看到了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作家的真誠。
三、郁達夫的真誠對后世的影響
《沉淪》真實地反映了人性的問題,小說的獨特價值在于將原來小說中不敢描繪和“不應(yīng)該”描繪的部分寫入書中。就像郁達夫回應(yīng)責(zé)罵《沉淪》的人:“你們可以罵我不要臉,罵我流氓,但你們得承認(rèn),我比你們真誠。”同時,郁達夫在《沉淪》中所傳遞的情感、真誠,深深影響了丁玲等一系列作家。為后續(xù)文學(xué)創(chuàng)作打開了新篇章,沖破了那種壓抑人性、泯滅欲望的文化傳統(tǒng)。
反思作者在文學(xué)作品中的真誠——從文學(xué)活動的角度出發(fā)
反思作者的真誠在文學(xué)作品中的影響,就好比一個廚師燒出的菜肴是否美味,并不在于他是否真誠對待燒菜這件事,而在于他燒菜的技藝。同樣,作者的真誠對文學(xué)作品起到影響作用,但并非決定性影響。文學(xué)活動包含若干要素,按照艾布拉姆斯的觀點,應(yīng)由四個要素構(gòu)成:世界、作者、作品和讀者。這四個要素在文學(xué)活動中形成相互滲透、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整體關(guān)系。本文提到的“作者的真誠”滲透于四要素的各個方面,在四要素中存在影響“作者的真誠”的因子,由此反思“作者的真誠”對文學(xué)作品的影響。
從世界的層面上講,世界是文學(xué)活動的基本要素之一。主要是指文學(xué)活動所反映的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作者的真誠將自己的主觀世界較真實地與客觀世界結(jié)合,影響文學(xué)活動,但作者的真誠是較難驗證的。
在作者的層面上,作者通過文學(xué)創(chuàng)作來表達他的感受和感情,并試圖以此喚起讀者相應(yīng)的感受和感情。文學(xué)與作者密不可分,作者的內(nèi)心活動一方面可以通過作品描寫、自我表態(tài)等方式展現(xiàn),但另一方面,如果作者以“真誠”為自我表白而無害處,人人都可以說自己“真誠”。我們要認(rèn)識到作者口中所標(biāo)榜的“真誠”與實際作品所反映的態(tài)度之間的關(guān)系,不能以偏概全。
在作品的層面上,文學(xué)反映的世界并不等于世界本身,同時,文學(xué)表達的情感也不同于作者的內(nèi)心的實際感受。“文學(xué)本體論”強調(diào)文學(xué)活動的本體在于文學(xué)作品,而不在于外在的世界或讀者。作者的真誠與作品的價值沒有必然聯(lián)系,因為作者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可能并不知道最后想要表達的內(nèi)容,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主題后行”。當(dāng)作者完成作品,轉(zhuǎn)換角度冷靜下來去分析思考的時候,才會明晰其作品背后的價值。再者,文學(xué)反映的世界并不是在作者完成作品后就能夠下定論的,他所反映的內(nèi)涵是變化的,不斷充盈的。
從讀者的角度來看,文學(xué)接受論,說明讀者在不斷賦予作品意義。作者的真誠會被讀者看到,并且影響讀者對作品的看法,讀者的主觀性較強,在閱讀整部文學(xué)作品時,認(rèn)知過程會影響到讀者對客觀公正的把握。讀者群體為文學(xué)作品賦予不同的內(nèi)涵,“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讀者所感受到的真誠也可能與作品本身存在偏差。讀者對作者創(chuàng)作是否真誠是深有感受的,文字沒有感染力,缺乏力量感,讓讀者感覺文字是敷衍的,讀與不讀相差意義不大,這是一個作者創(chuàng)作文章最失敗的地方。
綜上所述,作者的真誠在文學(xué)活動中的影響是有限的。
思考當(dāng)下文學(xué)中作者真誠的問題
郁達夫的《沉淪》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文學(xué)史上不乏處女作便是巔峰的現(xiàn)象,比如魯迅的《狂人日記》、曹禺的《雷雨》、郁達夫的《沉淪》等,這絕不是偶然。任何一個作家的巔峰之作無不是其嘔心瀝血后的產(chǎn)出,與誕生的早晚沒有關(guān)系,其作品所展現(xiàn)的價值,與他們生命深處的共鳴相連。
但是,在讀后不免會思考一些問題,作者的真誠對文學(xué)有那么重要的影響嗎?結(jié)合近些年文學(xué)的畸形發(fā)展,文學(xué)呼喚真誠的論述,于是產(chǎn)生了此篇文章。真誠是最具有殺傷力的武器,正如本篇文章批判性的地方,作者的真誠為文字注入靈魂,是打動讀者的有力武器。但與此同時,我們要辯證地看待“作者真誠”的作用,要批判地理解作者的真誠在文學(xué)中的影響。作者的真誠對文學(xué)的影響在這個物質(zhì)化的時代,顯得格外重要。
作者簡介:
張廣雯,女,漢族,山東菏澤人,長春師范大學(xué)漢語言文學(xué)本科三班學(xu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