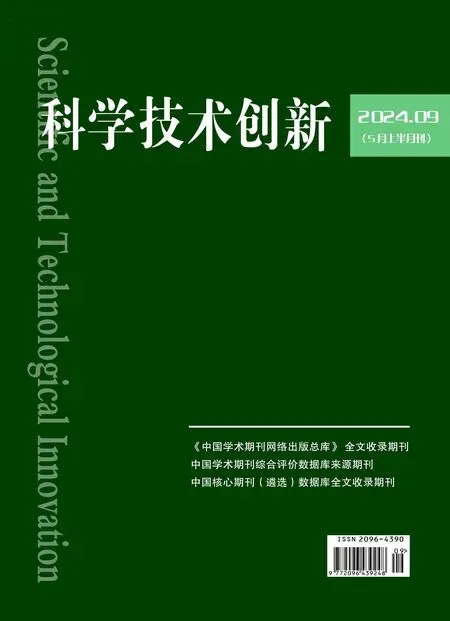蓋挖法基坑上跨既有地鐵盾構隧道方案研究
吳 彬,付春青,彭 華,馬文輝,楊緯華,劉 猛,劉 彤
(1.北京市軌道交通建設管理有限公司,北京;2.北京城建軌道交通建設工程有限公司,北京;3.北京交通大學,北京)
引言
隨著城市的快速建設與發展,基坑鄰近既有地鐵隧道的工程數量越來越多,有的基坑甚至位于既有地鐵隧道上方。基坑施工過程中的土方開挖、降水、加載等過程,都會使既有地鐵產生一定的變形,而地鐵列車的運營對隧道變形非常敏感。由此,對于該類基坑的設計、施工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針對新建基坑上跨既有地鐵的工程,國內外學者開展了一定的研究。Marta[1]利用數值模擬手段,針對基坑開挖引起的近接隧道變形規律、受力特性以及加固和保護措施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Sharma J S 等[2]通過數值模擬方法得到隧道的剛度、埋深、地質、下穿方式等因素與上跨工程施工引起的隧道變形大小存在直接聯系。李志高等[3]分析了東方路下立交工程現場監測數據,得到了基坑開挖卸荷引起下方隧道縱向變形的總體規律和時空效應規律,推導了考慮時空效應影響的隧道隆起經驗計算方法。黃宏偉等[4]通過PLAXIS 研究了外灘通道開挖對下臥延安東路隧道的影響,評價了不同隧道保護措施的效果。黃海濱等[5]采用有限元分析和現場實測方法研究了某箱型隧道基坑上跨已運營地鐵隧道工程,優化設計了工程支護結構及基坑開挖方式。高強等[6]依托市政隧道上跨西安既有地鐵2 號線盾構隧道為依托,根據擬定的設計方案,采用FLAC3D 有限差分程序對市政隧道基坑開挖對下臥地鐵盾構隧道的影響進行數值分析,并對隧道抗浮進行驗算。安偉博[7]采用MIDAS/GTS 建立了三維基坑模型,研究了杭州某基坑工程開挖對下臥盾構隧道變形的影響以及不同加固控制措施的效果。李宗陽等[8]采用現場實測方法研究了徐州粉土地區彭祖大道地道工程明挖基坑近距離上跨地鐵盾構隧道的保護方案,提出了MJS 及管幕相結合的盾構保護措施。施有志等[9]采用有限元分析和現場實測方法研究了廈門地鐵某停車場與地鐵正線重疊段為依托,研究出入線明挖基坑施工對下臥隧道的影響以及采取變形控制措施的效果。
本文以北京某蓋挖法深大基坑上跨既有地鐵盾構隧道工程為依托,采用數值模擬分析基坑施工影響下既有隧道變形規律,比較討論不同措施對既有隧道的保護效果,既保證基坑本身的穩定,又確保既有地鐵安全運營,為相關工程提供理論依據和參考。
1 工程概況
新建基坑位于北京地鐵某區間始發井結構正上方,如圖1 所示。新建建筑結構形式為地上一層、地下三層的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基坑圍護結構為113 根鉆孔灌注樁,圍護樁樁徑1.0 m,樁長17.9 m~22.7 m。基坑底板埋深為14.6 m,與始發井結構頂板凈距為5.915 m,與區間結構最小凈距為9.194 m。

圖1 工程周邊環境
既有地鐵雙線盾構區間,區間線路為直線。盾構直徑為6.0 m,結構頂部埋深約24.2 m,既有線間距14.0 m。
為確保開挖施工安全,減小對既有地鐵盾構區間影響,從地面對區間上方土體進行加固。加固范圍為基坑范圍內、地鐵盾構區間頂板以上6 m 土體。土體加固材料采用單液水泥漿或水泥-水玻璃雙漿液,工程剖面如圖2 所示。

圖2 工程剖面
基坑施工處巖土層從上到下依次為①房渣土、②1粉質粘土、②粉質粘土- 粉質粉土、③粉細砂、④1中粗砂、④卵石、⑤粘土、⑤1砂質粉土- 粘質粉土、⑤2粉細砂、⑥1中粗砂、⑥卵石。
2 模型的建立
結合實際工程,計算模型采用ANSYS 有限元軟件建立地層- 結構三維實體模型,土體與基坑支護結構、新建地下室框架結構均采用實體單元Solid45 進行模擬,既有盾構隧道和豎井結構均采用殼單元Shell63 進行模擬。模型沿既有地鐵線路方向(Z軸方向)取150 m,垂直既有地鐵線路方向(X 軸方向)取120 m,沿地層深度方向(Y 軸方向)取50 m。地表為自由邊界,土體四周及底部采用法向約束,如圖3 所示。

圖3 新建基坑與既有隧道三維有限元模型
2.1 模型假定
(1) 土體為各向同性、均質的理想彈塑性體,對各層土體和地表作簡化處理,使其在水平方向呈勻質層狀分布。
(2) 在模型計算時,初始地應力只考慮土體自重應力;不考慮巖土體構造應力,使巖土體在自重作用下達到平衡狀態,然后再進行基坑開挖施工。
(3) 根據工程地勘報告中所給出的土體參數來選取模型中需要的土層參數。
(4) 假定既有地鐵結構變形和軌道結構變形一致。
(5) 假定在施工前軌道結構處于良好狀態。
2.2 模型參數
根據地質勘查報告,依照地層特性對相近的土層參數取加權平均值。模型土層參數如表1 所示。

表1 土體參數
根據計算假定,既有及新建結構均視為線彈性材料,結構參數如表2 所示。

表2 結構參數
基坑施工采用蓋挖逆作法,逐層分步進行,根據結構板的位置分為三大層,每層土方開挖在平面位置上又分南、北兩幅依次進行,北幅待每層的南幅結構板、墻施工完成后再行施工,共分為11 個施工階段。
3 模擬結果分析
3.1 計算結果分析
按工程方案進行數值模擬,經過計算,分析基坑開挖對地表沉降、隧道結構沉降的影響程度。基坑開挖結束后,既有地鐵隧道變形由中間開挖位置處的峰值向兩側逐漸減小,曲線左右兩側對稱。左線、右線最大上浮值為1.971 mm、2.371 mm,如圖4 所示。

圖4 施工結束時既有地鐵隧道變形云圖
3.2 方案對比分析
基坑的支護形式以及施工注漿情況的不同導致施工對既有地鐵變形的影響程度不同,為了比較影響程度的差異,改變相關參數,如表3 所示,方案一、方案二對比分析注漿情況;方案一、方案三、方案四對比分析圍護結構情況(樁徑和樁距變化)。

表3 方案情況
3.2.1 注漿加固的影響效果
兩方案下地表和地鐵隧道的最大變形對比如表4所示,隧道豎向變形如圖5 所示。

表4 方案一、方案二最大變形匯總(單位:mm)

圖5 方案一、方案二最大豎向變形量對比
在將方案由注漿6 m 改為不注漿后,隧道最大豎向變形由2.371 mm 變為4.42 mm,地表沉降最大值由5.34 mm 變為7.60 mm,超出安全控制范圍,可見基坑開挖前對基坑下方處土體進行注漿加固是十分必要的,能夠有效減小既有結構的變形。
3.2.2 圍護樁結構參數的影響
三個方案下地表和地鐵隧道的最大變形對比如表5 所示,隧道豎向變形如圖6 所示。

圖6 方案一、方案三、方案四最大豎向變形量對比
(1) 方案一、方案三對比,在將圍護樁直徑由1.0 m 改為0.8 m 后,隧道最大豎向變形由2.37 mm 變為2.61 mm,地表沉降最大值由5.34 mm 變為5.47 mm,因此圍護樁直徑的改變能夠影響既有結構沉降。圍護樁直徑越大,控制效果越好,既有結構沉降就越小。
(2) 方案一、方案四對比,在將圍護樁樁距由1.5 m 改為1.2 m 后,隧道最大豎向變形由2.37 mm 變為2.03 mm,地表沉降最大值由5.33 mm 變為5.21 mm,因此圍護樁樁距的改變能夠影響既有結構沉降。圍護樁樁距越小,即圍護樁越密集,控制效果越好,既有結構沉降就越小。
(3) 在圍護樁參數改變后,兩方案中既有地鐵的最大橫向變形值由0.40 mm 變為0.44 mm 和0.34 mm,變化值僅有0.05 mm 左右,因此改變圍護樁參數對結構橫向變形影響效果不大。
(4) 從整體分析,圍護樁參數改變后既有結構變形和地表沉降雖然有改變,但變化值并不大,與方案二注漿情況的改變對結構變形產生的影響相比,圍護樁參數的改變對既有結構變形的影響較小。
4 結論
通過建立ANSYS 三維有限元模型,分析比較了不同施工參數下蓋挖法基坑施工對既有地鐵隧道的影響程度,得到如下結論:
(1) 基坑開挖前對基坑下方處土體進行注漿加固是十分必要的,能夠顯著減小既有地鐵隧道的變形。
(2) 增大圍護樁樁徑,縮小圍護樁樁距,可以減小既有地鐵隧道的豎向變形,但與注漿加固相比,圍護樁參數的改變對既有地鐵隧道豎向變形的影響變化較小。
(3) 由于基坑開挖工程本身對下臥地鐵隧道的橫向變形影響程度較小,改變施工參數對橫向變形的影響變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