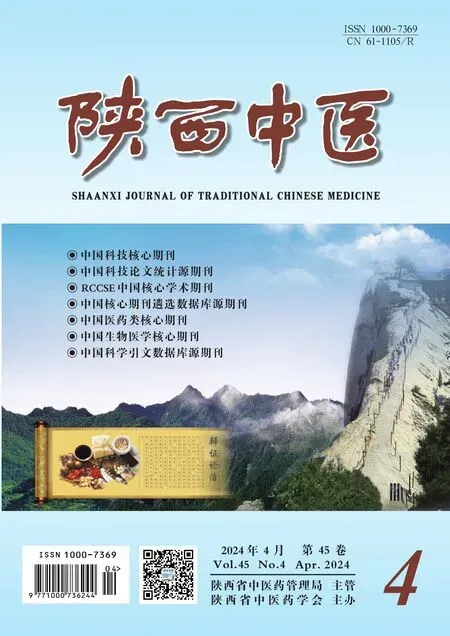基于“形神同調”理論辨治持續性房顫
艾克熱木·艾爾肯,鈕岳岳,李紅萍,李明昊,李琳軒,馮 玲
(1.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北京 100053;2.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 100029)
心房顫動簡稱房顫,是臨床最為常見的心律失常之一,合并高血壓等風險因素的老年群體為好發人群[1]。心房顫動的特征是心房快速、無組織的興奮和心室的不規則激活。房顫可誘發或加重心力衰竭、心肌梗死、血栓栓塞、腦梗死和慢性腎衰竭,增加中風的風險,并延長住院時間,影響心臟功能和生活質量[2-3]。我國45歲以上男性和女性的房顫患病率分別為0.8%和0.6%,75歲以上男性和女性的房顫患病率分別為5.4%和4.9%[4]。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房顫患者發病率逐漸升高。持續性房顫可作為心律失常的首發表現出現,也可以由陣發性房顫病情惡化發展而來。目前針對持續性房顫患者主要包括抗心律失常、抗凝等藥物治療,以及電復律、導管射頻消融、永久起搏器等非藥物治療,術后復發與長期服用抗凝藥物引起的出血風險及肝臟不良反應是現今治療持續性房顫的難題[5]。中醫藥治療持續性房顫的優勢隨之漸顯,可彌補手術及西醫藥物治療之不足,取長補短,相輔相成。失眠會引起自主神經功能障礙,進而誘發房電生理學的顯著異質性改變,最終促使房顫的發生[6]。房顫會引起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礙,失眠又使房顫病情加重[7-8]。同時,在房顫患者中焦慮和抑郁的發病率較高[8]。這與中醫理論中“神病”與“形病”相互影響不謀而合,為基于形神同調治療持續性房顫提供理論基礎。
1 中醫對房顫的認識
中醫學中并無房顫病名,由房顫發作時的癥狀表現可歸于“心悸”“驚悸”等范疇中,主要表現為心悸、脈結或代,常伴頭暈、胸悶、氣短等[9]。本病核心病機有虛實之分,虛證以氣虛、血虛、陰虛、陽虛為主,實證以痰濁、血瘀、水飲、氣滯、內風等為主,多因外邪侵襲、勞累過度、情志因素、素體虛弱等引起,輕者可休息后自行緩解,平素如常人,重者則整日悸動,難以控制。本病其病位在心,與肝、肺、脾、腎相關,病性乃本虛標實[10]。心為陽中之陽臟,為五臟六腑之大主、生命之主宰,是有形之體與無形之神的統一。心主血脈,亦主神明。一方面心氣推動血液運行于脈中,血液由心臟搏動而周流全身;另一方面,心主導人的精神意識、思維活動及生命活動。形神相互影響,互為因果,以調形安神為治療總則,加以日常情志調護,治療持續性房顫效果顯著。
2 現代醫學對房顫的認識
房顫是臨床常見的心律失常類疾病,其特征為心房出現雜亂無序而快速的電活動,導致心房無法進行有效收縮及泵血,引發心臟排血功能下降,心功能降低,繼而導致心室心律失常[11]。房顫分為陣發性、持續性和永久性心房顫動[12]。陣發性房顫患者可自發轉為竇性心律,而持續性房顫的發作持續時間超過48 h,患者需要藥物治療或心臟電復律才能恢復竇性心律,治療難度較前者提高[13]。對于持續性房顫的治療而言,預防栓塞等惡性事件發生的意義要遠大于復律[14]。房顫的發病機制復雜,常由電生理異常和解剖結構改變兩方面因素導致。電生理異常導致的房顫發生機制主要包括觸發離散性早搏,致心房細胞異常興奮,或重入環機制引起快速而無序電興奮波傳播,或因鈉離子通道和鉀離子通道功能異常阻礙心肌細胞去極化過程正常進行從而促發房顫。解剖結構的異常如心臟病變或心肌纖維化導致電信號無法正常傳導與整合,引起房顫。心房纖維化可促進心房結構重塑,從而增加房顫的持續時間,導致陣發性房顫惡變為持續性房顫。持續性房顫的患者可能伴有更多的心房顫動危險因素,并且暴露于更長的心房重塑持續時間[15]。
房顫的發生與自主神經異常密切相關,自主神經系統不僅調節心律,并在心房顫動的觸發和維持中也起著重要作用,主要通過激活交感神經,引起心房釋放無序而快速電信號,成為誘發的動力,并促進神經遞質兒茶酚胺分泌過多,縮短心房有效不應期,心房過度興奮從而導致心肌細胞內鈣離子內流增加,心肌收縮力增強,導致房顫的發生[16]。因此,自主神經調控在房顫的治療中極為關鍵[17]。既往研究表明,不同類型的睡眠障礙與房顫發生的風險相關性高,如睡眠呼吸暫停等疾病會破壞正常平衡的自主神經系統活動,并導致間歇性低氧血癥和急性血流動力學變化,從而對心血管生理產生不利影響。長期處于睡眠呼吸暫停狀態可能通過心房重構及電信號異常從而增加房顫等心律失常疾病的發生風險。與此同時,房顫患者轉為竇性心律時,睡眠質量均有明顯改善[18]。較差的睡眠質量及睡眠時間不足會導致皮質醇水平、交感神經活動和炎癥增加,這些因素都可能介導房顫發病[19]。慢性應激和焦慮狀態對神經內分泌、凝血、微循環和免疫系統可能產生影響,焦慮狀態與房顫的發作之間存在較強的關聯。焦慮癥、抑郁癥患者房顫發病率較高,且有研究表明房顫病程6~10年的患者更有可能出現嚴重的焦慮和抑郁,慢性病程合并心理障礙從而增加疾病的發病率及病死率[20-21]。
3 “形神同調”內涵
3.1 “形”的概念 形,《說文解字》記載:“形,象形也”,指具象的有實體之物。在中醫學中,形可指形質、形態,亦指具有生命特征的血肉有形之體,包括臟腑、經絡、筋脈等有形結構,也包括氣血津液等精微物質。如《素問·上古天真論》曰:“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機體生命活動依存于“形”,《素問·六微旨大論》中記載:“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氣機升降出入及生化功能正常運作依賴于有形之體。中醫“形”帶有強烈生命屬性,呈動態變化并具有時限性,可引申為生命結構具有整體、多樣、有層次、可識別的特性[22]。
3.2 “神”的概念 神,《說文解字》曰:“天神,引出萬物者也。”本意為天神,神靈。在《黃帝內經》中“神”的概念大致有四:一為天地宇宙萬物之間存在的運動規律,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言:“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二為機體生命的活動與功能,如《靈樞·天年》曰:“黃帝曰:何者為神?岐伯曰:血氣己和,營衛已通,五臟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為成人”;三為狹義的精神活動,如意識、思維、情緒等,如《素問·六節藏象論》曰:“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又如《素問·寶命全形論》言:“一曰治神,二曰知養身;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四為鬼神之義,如《靈樞·賊風》曰:“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惟有因鬼神之事乎”。
3.3 “形神同調”釋義 “形神同調”源自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形神一體觀”,并在《黃帝內經》中從中醫學角度發展為“形神合一”思想內涵。《素問·上古天真論》曰:“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形為人體中的有形之體。神為生命活動的基礎,廣義之神指臟腑的外在生理表現及生命功能活動;狹義之神則是人的精神意識思維活動[23]。《慎齋遺書》曰:“病于形者,不能無害于神;病于神者,不能無害于形。”形與神相互制約,互生互用,神損及形,形傷及神。明代張景岳在《類經》中言:“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借血肉以成其形,一氣周流于其中以成其神,形神俱備,乃為全體。”可見,形神為一體,形為神之基礎,神為形之統帥,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須相輔相成,形神統一,方可“盡終其天年”。
4 持續性房顫病因病機中的形神觀
《靈樞·本神》曰:“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心主管感知外界萬物后產生的精神意識思維情感等活動,亦主導神與形的和諧統一。心的兩大生理功能“主血脈”即為形之所用,“主神明”即為神之所用,形神共調合一,則可形與神俱。房顫多發于中老年群體,年事已高,臟腑衰竭,氣血虧虛,心神失養,致血行不暢,瘀阻血脈,發為此病。形神失調為房顫發作的主要病機。心氣不足,心主血脈功能失常,血脈推行無力,血行不暢,心神失養;神明失于濡養,心無以藏神,心腎失交,可致腎無以藏志;或因房顫日久傷津耗氣,血行無力,乙癸同源,腎精虧虛,神機失用,發為“神病”。患病日久,心陽衰微,心氣虧耗,無以化飲,水液運化失常,積聚成痰,郁而化火,內擾心神;血運失暢,內生瘀血,痰瘀等有形之邪上擾清竅,亦可致形神失調而發病。心悸日久,氣血運行不暢,瘀血阻于脈內,可致中風、胸痹。持續性房顫相較于陣發性房顫更易引起失眠、焦慮、健忘等神志病變,同理,神病日久亦可加劇房顫,氣機不暢,氣血運行受阻,邪氣內積,心失所養,水飲上逆于心,加重疾患。可見,“神病”與“形病”可同時出現,亦可相互轉化,通血脈,調神明,以求形神同調。
5 基于“形神同調”理論治療持續性房顫
5.1 治形為先,形全則神安悸止 形為神之宅,氣血津液充盈,脈道通暢為心神清明的基礎。心氣盛,則心陽通,血液依靠心陽推動循于脈道濡養周身。《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陽氣之精在上濡養神明,而陽氣之柔在下營養筋經。可見,陽氣通達充盈,臟腑得以榮養,神明得以安寧,在調形與神中尤為關鍵。久病體虛或心氣損耗日久傷及心陽,可致心陽不足。心陽虧虛,氣血運化無力,則心神失養,心動失常,癥見心悸不寧、胸悶憋氣、四末不溫、舌淡苔白、脈虛弱或沉細。此時當治以溫通心陽,安神止悸,可選用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加減治之。若思慮過極,損耗心血,陰血俱虛,致神機失養,心神不寧,治宜益氣養陰、寧心安神,可予炙甘草湯加減。《內經》載:“血實宜決之,去菀陳莝”。有形之邪,亦傷形神,瘀血、痰飲、濕濁、火熱宜祛邪治之,全其形而安其神。若氣血不足,痰濕、瘀血阻塞血脈,心脈不暢,心失所養可予血府逐瘀湯。若本虛標實,當標本兼顧,祛邪扶正。
5.2 安神為要,神安則形全悸止 房顫病位在心,可涉及肺、脾、肝、腎。《素問·宣明五氣》言:“五臟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臟所藏”。心主血脈與藏神功能共同完成主神明之職,雖言神為心之藏,但五臟之間的協調亦會影響神明,五臟不調,傳變心神,或心神不統五臟,均可使心神不寧,發為心悸。心病當先治心神,然五臟六腑皆可致心悸[24]。如“脾藏意”“營舍意”,而意又為“心之所存”,脾居中焦,為后天之本與氣血生化之源,營氣由脾生化水谷精微而來,并滋養脾意,脾安則氣血生,心神得安。若脾失健運,氣血不足,心神失養則發為動悸,癥可見心悸,時作時止,氣短乏力,神疲少言,納呆,舌淡,脈細弱。在治療時需注重健脾養心、安神補形,可選用歸脾湯加減,方中茯神、遠志、酸棗仁可寧心安神。脾意得養,脾氣升清,上養心脈,氣血充盈,心神則安。同時,日常情志調護亦非同小可,《素問·四氣調神大論》言:“春生則舒緩以利升發,夏長則外張使所愛在外,秋收則內斂以靜神氣,冬藏則伏匿以順蟄閉。”順應四時變化,保持情緒平穩。此外,已有研究發現睡眠時間過短或過長均可增加房顫發作的風險[25],因此對于房顫患者的睡眠調理及相關宣教亦尤為重要。充足、高質量的睡眠可預防房顫的發生,減緩持續性房顫的進展。
5.3 脈神同調,脈通神清則悸止 馮玲教授基于形神一體觀提出“脈神同調”理論治療持續性房顫。《靈樞·本神》曰:“心藏脈,脈舍神”,脈為有形之物分布形體,藏而不泄,流通血液及精微物質,如網如渠遍布周身。脈形可分為脈體與脈律,脈體為有形之體,脈律為脈之節律,脈中氣血為神安之要,為神之所居[26]。血液運行正常,需血液充盈,心氣充沛,脈道通利,缺一不可。脈病可因實,如痰濁、瘀血閉塞脈道,亦可因虛,氣血虧虛,脈道失于充盈,周身難以濡養。脈體飽滿柔韌,可知氣血津液充盈,心脈通暢;脈律均勻和緩,可知陽氣溫煦,脾氣升清,氣血運行有律。馮玲教授自擬定顫方治療持續性房顫,臨床運用多年效果顯著。定顫方以丹參、苦參、玄參、酸棗仁、柏子仁、甘松、檀香、珍珠母為基本組成,在調形、調脈的基礎上佐以調神之品,調其神明,調形與神并重,形神同治,方可顯效。方中丹參、苦參共用養血清熱,人參補氣養血,玄參滋陰降火,諸參合用氣陰清補,脈律整齊;酸棗仁寧心安神,柏子仁交通心腎,珍珠母平肝魂、重鎮安神,甘松安脾神、理中氣,諸多安神之法同用五臟神安,則神清志明,夜寐得安;檀香溫通血脈,與丹參合用行活血行氣通脈之效;全方形神同調,形充神安則心悸自止。調理氣血,養陰清熱,息風安神,使脈體充盈,脈道通暢,神志安寧,脈律如常。
6 小 結
形神本為一體,形為神之基礎,神為形之統帥,二者和諧統一,方可形全神安,脈律有節。氣、血、陰、陽虧虛或痰、瘀、風、火傷形,亦可致神病;心神不統,五臟或因情志不暢傷神,亦可致形病;形神失調,心脈不通,心神不寧,發為心悸。《類經》中言:“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無形則神無以生,無神則形不可活”,故治心悸需“調形”與“調神”兼顧,全其形而補其神,脈通神清而心悸自止。介入治療或射頻消融術后房顫復發為持續性房顫治療中的難點。手術治療后的患者易出現血流動力學紊亂,嚴重時可出現心源性休克,增加心衰、中風、死亡等發生率。調控自主神經、調整睡眠模式、預防并積極治療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狀態在其治療過程中尤為重要,在持續性房顫的轉復、防止復發、預防心房纖維化及心房結構重塑中均起到積極作用,這與中醫學理論體系中的“形神一體觀”不謀而合。在心血管疾病發病率逐漸上升并年輕化的當今社會,“雙心治療”思路在心血管疾病的治療中愈發被重視,在心血管疾病自身防治的基礎上,注意精神障礙對機體的影響,以求身心健康、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