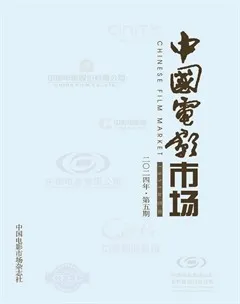論“缸中之腦”假想在科幻電影中的運用及主題表達的變遷
任圣 崔雅清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缸中之腦”這一假想在科幻類型電影中的運用及流變,試圖歸納總結出此類電影的一般特征,由此探討該類電影主題表達及其背后隱含的內涵的共性與差異,以及對中國科幻電影創作的啟發。
【關鍵詞】科幻電影 缸中之腦 類型特征 擬態環境 洞穴隱喻 元宇宙
科幻類型作為當今世界電影主流類型之一,從其誕生之初就備受關注,發展至今已積累起大量受眾。其基本特征是從當下已知的科學原理和科學成就出發,對未來世界或遙遠過去的情景作出幻想式的描述。因其不必拘泥于已達到的科學現實,創作者可以在科學原理的基礎上充分展開想像的翅膀,預想人類生活的未來面貌[1]。基于影片圍繞的核心科學原理、科學成就和科幻概念在細分領域的不同,誕生了大量不同題材的科幻類型片,比如時間穿越題材、外星人與星際旅行題材、人工智能題材、機甲怪獸題材等等。
在科幻類型電影提及并運用的眾多核心科幻概念中,有一個科幻概念雖然被運用的不多,但因其概念的新穎性和哲學思辨性,使基于這一概念衍生的電影作品在電影史上占據了重要地位,這一概念就是“缸中之腦”。
一、 “缸中之腦” 概念起源與現實基礎
對于“缸中之腦”這一科學假想的最早闡述,出自美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希拉里·懷特哈爾·普特南1981年出版的《理性,真理和歷史》一書,書中有這樣一段描寫:“一個人的大腦被科學家通過手術取出,與身體分離,被放進一個盛有維持腦存活營養液的缸中。腦的神經末梢與計算機相連,這臺計算機按照指定的程序向大腦不停地輸送信息,用這樣一種方式使他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覺。對于他來說,人、物體、天空依然存在實體,自身的運動、身體感覺都可以輸入。這個大腦還可以被輸入或截取記憶(截取掉大腦手術的記憶,然后輸入他可能經歷的各種環境、日常生活)。他甚至可以被輸入代碼,‘感覺到他自己正在這里閱讀一段有趣而荒唐的文字:一個人被科學家施行了手術,他的腦被從身體上切了下來,放進一個盛有維持腦存活營養液的缸中。腦的神經末梢被連接在一臺計算機上,這臺計算機按照程序向腦輸送信息,以使他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覺……”[2]。有關這個假想的最基本的問題是:“你如何擔保你自己不是處在這種困境之中?”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通過技術手段幫助人類重建感官的設想儼然已經逐步成為現實,最典型的人工耳蝸技術,已經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應用于聽障人士的治療,隨即而來的還有人工視覺、人工嗅覺、人工味覺的不斷研究。2021年,澳大利亞研究團隊Cortical Labs開發了一種微型人類大腦,被稱為盤中大腦(DishBrain),正式論文中則描述為體外神經網絡(Invitro neural networks),它其實就是培養皿內盛有的80萬-100萬個活的腦細胞,這個規模接近于蟑螂的腦部。腦細胞下面排列著密密麻麻的微電極,負責刺激它們。通過學習,盤中大腦成功學會了雅達利乒乓球游戲《Pong》,并且學習速度要遠高于現有AI水平。那么我們反向思考一個問題:這些“盤中大腦”會知道自己其實是被裝在培養皿中的嗎?
通過上述案例,我們可以合理推論,在不久的將來,普特南所描述的情況極有可能會從思想實驗轉而成為現實。到那時,人類將不得不面對一個困境———“人類要如何確認自己究竟是身處真實,還是僅僅是感覺真實?”。
二、典型案例
(一)《黑客帝國》系列(1999、2003)
在“缸中之腦”假說提出18年后的1999年,一部以“缸中之腦”概念作為核心科幻設定的影片《黑客帝國》第一部上映。電影世界觀的架構在物理層面上與“缸中之腦”假說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人類肉身被機器接上各種各樣的連接管和插頭,浸泡存活在充滿培養液的缸型容器中,人類意識則“生活”在虛擬世界“矩陣”中,但他們自己感覺自己仿佛生活在真實世界中。絕大多數人并不懷疑自己所處情境的真實性,除了以主人公尼奧為代表的“黑客”———一小部分覺醒的人類。“黑客”們游走于虛擬與真實之間,為人類的存續和自由與機器進行抗爭。
如今,互聯網幾乎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人類已越來越離不開互聯網,《黑客帝國》系列電影所構建的世界觀已不再神秘,但是回想其上映的那個年代(1999年、2003年),其超前的世界觀設定、表現形式及背后要表達的主題無一不震撼著當時的觀眾。
(二)《異次元駭客》(1999)
在《黑客帝國》第一部上映兩個月后,電影《異次元駭客》便緊隨其后上映了,該片同樣以“缸中之腦”這一假說為基礎,不同于《黑客帝國》在科幻類型方面的毫無爭議,《異次元駭客》在當時更多被看作是一部懸疑、驚悚電影,票房成績遠不如前者理想,但是該片的表現形式、故事模型以及內含的哲學思辨性對之后同題材類型的電影創作啟發和影響并不亞于《黑客帝國》(后文提及的《盜夢空間》《失控玩家》等影片都能看到該片的影子)。
相較于《黑客帝國》在開篇之時就把世界觀的建構交代清楚,《異次元駭客》則選擇把世界觀設計為懸念的一部分,伴隨劇情的展開而對其逐步進行揭示:故事的前半段,我們認為“缸”是1937年的世界,主人公道格所在的1999年的世界是真實的世界;但真實情況卻更加復雜, 1999年的世界其實是一個更大的“缸”,真實世界是2024年的世界。主人公道格在1937年和1999年之間不斷穿越尋找真相,最終發現自己其實也只是一顆“缸中之腦”。
(三)《楚門的世界》(1998)
上述案例中,“腦機相連”是作為一種真實可見的物理設備存在的,而這種“物理性”的呈現也被看作是“缸中之腦”模式影片的一種標志,但是也有一類影片,并沒有用物理設備的方式去呈現“缸中之腦”,而是將“缸中之腦”這一概念進行抽象化運用,其中最為典型影片就是《楚門的世界》。
影片《楚門的世界》中,楚門這個人物就是“缸中之腦”中抽象化的“腦”,楚門所生活的“桃源鎮”,或者說是攝影棚,其實就是抽象化的“缸”,而負責給楚門以刺激,使其感覺一切正常的電腦就是《楚門秀》導演克里斯托弗和整個劇組。
(四)《盜夢空間》(2010)、《源代碼》(2011)
影片《盜夢空間》與《黑客帝國》《異次元駭客》相比,淡化了與“缸中之腦”物理層面的相似性,直接以“夢境”和“清醒”兩種狀態映射出“缸中之腦”假想下虛擬與現實的兩種世界觀。不同的是,《盜夢空間》是以一種有意識的辨別,即主人公對真實和虛擬有所認知,但自愿選擇沉睡,主動成為“缸中之腦”,當之前的作品都在尋求真實與覺醒時,主人公科布卻反其道而行之,逃避真實,回避覺醒,因懷念亡妻而在自己的潛意識中建立起一個虛擬的夢境來求得內心的安慰。
影片《源代碼》在物理設定層面基本符合“缸中之腦”假說的所有條件,雖然不如《黑客帝國》的世界觀龐大,但同樣帶有典型性:《源代碼》中同時存在三個世界———客觀現實世界、八分鐘的源代碼世界以及以一個狹窄的密閉空間為形式的主人公彌留世界。與《黑客帝國》不同的是,《源代碼》的兩個虛擬世界與真實客觀世界基本一致,主人公在兩種身份的不停轉換下其身份認同仍是統一于客觀真實世界的。雖然最終主人公因為客觀原因(身體已經無法在現實中存活),不得不生活在虛擬世界之中,但在這部影片當中,能感受到創作者已不再將“真實”和“虛擬”看作是完全對立的兩面,虛擬正在成為可平行于真實存在的另一種選擇,某種意義上來說,虛擬已漸漸成為“真實”坍塌之后的避難所。
(五)《頭號玩家》(2018)、《失控玩家》(2021)
與上述案例相比,在2018年上映的影片《頭號玩家》和2021年上映的影片《失控玩家》也許不夠典型。《頭號玩家》中,人類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虛擬、什么是現實,虛擬世界“綠洲”是人類逃避殘酷破爛現實世界的精神家園,無論多沉浸其中,也總有下線的時候;《失控玩家》的主角“蓋”和《異次元駭客》的主人公道格相似,是一個虛擬游戲中的NPC,甚至沒有肉身實體。但是,通過抽象概念,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兩部影片中存在“缸”與“腦”的映射關系,只不過在這兩部影片中,“缸”和“腦”的關系發生了轉變,《頭號玩家》中“缸”不再是牢籠,“腦”也不再是被蒙在鼓里一無所知的人;《失控玩家》中,“缸”就是“蓋”認同并存在的唯一世界,作為“腦”的他并不向往也不在意那個他無法到達的現實世界。
三、 “缸中之腦”模式影片的一般特征
通過對上述案例的分析和歸納總結,我們可以發現這類影片在世界觀的構建、人物設定和故事模型上,存在較為突出的共性特征。
(一)世界觀建構
科幻電影的世界觀設定———科幻故事展開所需要的一個想象出的空間載體和意識形態體系,是想象力的空間化和概念化,也是科幻故事雖然虛幻但具有可能性和可信性的基石[3]。“缸中之腦”模式的影片中,其世界觀的設定往往表現為“真實”世界唯一,一個或多個“虛擬”世界并存的形式。
所謂“真實”世界,我們可以理解為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它有可能和我們所處的現實世界一樣(例如《楚門的世界》),也有可能是假定性極高的對未來世界的某種想象(《黑客帝國》《頭號玩家》的“真實”世界都是創作者想象下未來某個時間節點下的人類世界);而“虛擬”世界的呈現則更加多種多樣,總體可以概括為:與“真實”世界平行的、可以被某種手段改變或影響的存在,例如《黑客帝國》中的“矩陣”、《楚門的世界》中的“桃源鎮”、《頭號玩家》中的“綠洲”,以及《失控玩家》中的“自由城”。“真實”世界與“虛擬”世界之間往往存在較大的差異,從而影響人物動作和劇情走向。
(二)人物設定
基于上述世界觀的設定,相應的人物設定也往往呈現出某種共性:不同世界中,人物的身份往往也不相同,人物對自身身份的認同和對世界的認同在相當長的時間段內也會出現較大的偏差,人物會因為這些偏差讓自己陷入自我懷疑或者崩潰邊緣,然后逐步接受現實,轉而尋求突破的方法。
(三)故事模型
這類影片往往圍繞上述“真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差異和人物身份認同的錯位展開敘事,雖然不同的影片會有不同的側重和劇情走向,但是其故事發展基本可以概括為:主人公從自我認識的世界中覺醒(或反覺醒),主人公的覺醒(或反覺醒)促使人物發生轉變,讓人物選擇擺脫束縛或是查明真相亦或是達成和解。
四、 “缸中之腦”模式影片的主題表達變遷
隨著科技發展和社會環境的改變,我們能夠清晰地察覺到蘊含在科幻電影作品中人類意識產生的微妙變化。
(一)《黑客帝國》與《楚門的世界》:現實與虛擬的二元對立
在二十世紀末,人類似乎對新世紀的到來或是充滿期待或是未知恐懼,畢竟早在1968年,人們對于21世紀的想象便已達到影片《2001太空漫游》中所呈現的高度,仿佛跨入2000年后,無論是科學技術還是人類意識,都會突破線性發展規律,來到一個新的紀元。而2000年前后正是人類信息化高速發展的時代,計算機、互聯網技術突飛猛進,人們對于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變革與沖擊尚未習以為常,因此幻想人類被科學技術奴役或威脅、人類奮起反抗的故事也成為科幻電影的一大經典命題。除上述案例影片外,《終結者》三部曲(1984、1991、2003)、《我,機器人》(2004)等表現人與機器直接對抗的影片也在此期間大量出現。無論是《黑客帝國》《異次元駭客》,還是《楚門的世界》,其核心表達的精神內核是一致的,即人類渴望真實與自由,人類應沖破虛假的牢籠,回歸真實生活。
(二)《盜夢空間》《源代碼》:從對立到共生的轉向
當時間來到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互聯網已經迅速發展成為人類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盜夢空間》和《源代碼》的主題表達已不再是對“虛擬”“機器”的極端抗拒。此外,觀眾對于《黑客帝國》系列的解讀也悄然發生變化,影片中的機器為人類設計的“矩陣”不再被看作是“牢籠”,而是“天堂”般的世界。這些現象從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人們對虛擬的態度已經逐漸發生改變,從抵觸轉變為逐步接受,甚至形成了某種共生關系。同樣在這一時期也涌現了一大批探討人與機器共存、共生、互為伙伴、賽博朋克為主題的影片,并一直延續至今,例如:《她》(2013)、《超能查派》(2015)、《攻殼機動隊》(2017)、《銀翼殺手2049》(2017)、《阿麗塔:戰斗天使》(2019)、《芬奇》(2021)等。
(三)《頭號玩家》與元宇宙未來:虛擬世界雖幻猶真
之所以上文認為《頭號玩家》與其他案例相比,在“缸中之腦”概念的運用上不夠典型,是因為這部作品更為核心的概念其實是近些年大熱的“元宇宙”。
“元宇宙”是指人類運用數字技術構建的,由現實世界映射或超越現實世界,可與現實世界交互的虛擬世界,具備新型社會體系的數字生活空間[4]。在《頭號玩家》的世界中,真實世界滿目瘡痍,人類放棄了解決現實問題,轉而在“綠洲”里尋找樂趣,畢竟“綠洲”幾乎能夠滿足人類除了維持生命個體運作的必要生物行為外的所有需求,“綠洲”雖然是一個物理層面虛擬的世界,但是其內在世界觀建構層面已經形成了完整的且與時俱進的社會體系。游戲世界與現實世界平行,并反作用于現實世界,這兩個元宇宙最重要的特征在影片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呈現,人們“生存”在真實世界中,但真正的“生活”卻在“綠洲”中。
當下,隨著VR、AR技術的日漸成熟,世界各大科技、互聯網巨頭紛紛在“元宇宙”領域開啟布局,也許在不遠的將來,“綠洲”的世界真的會來到我們身邊,“虛擬”與“現實”的邊界也不再分明。
五、總結與啟發
自古至今,人類從未停止過對真理的探求、對真假的追問,而電影作為一門綜合性的現代藝術,同文學、音樂、美術一樣,也成為人類表達對世界認知、思考與探究的重要途徑。
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的思想家莊子就曾提出與“缸中之腦”假說在哲學思辨性上高度一致的假想,即家喻戶曉的“莊周夢蝶”的典故;此外,柏拉圖的“洞穴隱喻”也探討了相似的困惑。無論是“缸中之腦”“莊周夢蝶”還是“洞穴隱喻”,其背后本質所探討的其實是同一個恒久而經典的哲學命題———“現實與非現實”,或者說是“真相與假象”。
現代社會日益龐大和復雜,人們對超出自己生活經驗之外的事物不得不通過一些媒介去了解,如新聞廣播、電視報道、社交媒體、網絡等。如此一來,現代人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對真實的客觀環境反應,而是對大眾傳播所構造或加工過的“擬態環境”反應。因此,真實與虛擬、真相與假象在現代人的生活中的交織越來越緊密,也越來越難以區分,對于人類生存世界真實性的思考也不斷成為電影作品的一個重要命題。
表面上看,科幻電影主題表達的變化是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創作觀念的一種必然流變,但其背后所暗含著的卻是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之間階段性的博弈結果,這尤其值得我們注意。人們長期以來所一直推崇的人文主義或者說人文關懷似乎正漸漸消解,并以一種不易察覺的沉默方式和我們作別,科學至上主義以一種勢如破竹的氣勢在百年間迎頭趕上甚至超越人文主義的地位,并給人文精神以致命打擊,成為整個世界所追逐與信奉的主流觀念。眼下看來,這似乎已是一個既定事實或必然趨勢,但人文關懷是否真的會徹底退出歷史舞臺?其消解可能引發的后果又是什么?或許是我們更應該思考的問題。
當下,以《流浪地球》系列為代表的中國本土科幻電影正在迅速崛起,國產科幻電影的類型化已經越來越成熟,視聽效果也愈加震撼,但是在主題表達的哲學性和思辨性上似乎還有提升的空間。
令人欣喜的是,我們已經能夠看到創作者開始重視這部分的表達,譬如《流浪地球2》中“數字生命”的概念和情節想要探討的哲學命題其實在某些方面與“缸中之腦”的內核契合;《宇宙探索編輯部》在看似荒誕的故事背后提出了人類存在于宇宙的意義是什么的終極問題;《被光抓走的人》用一則思想實驗的形式探討了人與人情感鏈接中的存在主義問題……但從國產科幻電影的長遠發展來看,這些還遠遠不夠。一方面,隨著中國電影工業化程度不斷提高,觀眾很快會接受并習慣國產影片在敘事、視聽等方面達到一定的高度。到那時,觀眾將不再滿足于故事和視聽,也會對主題表達有所要求。另一方面,縱觀當下中國電影產業,數億元資金投入、數年制作周期的重工業、大制作的科幻影視項目畢竟還是鳳毛麟角,能承擔其中風險的主創和資方也十分有限。相比之下,將創作重點放在核心科幻概念的搭建或者追求更為深刻的主題表達上,也許會相對容易生產出以小博大的“爆款”產品,這不失為青年電影創作者以及風險承擔能力較弱的制片方在科幻電影創作上的一條可行之路。
注釋
[1]許南明,富瀾,崔君衍.電影藝術詞典[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 2005: 69
[2] (美)普特南.理性、真理與歷史[M].童世駿,李光程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7.
[3]陳旭光,薛精華.論中國科幻電影的想象力與“想象力消費”[J]. 電影藝術, 2021, (05): 54-60.
[4]百度百科“元宇宙”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