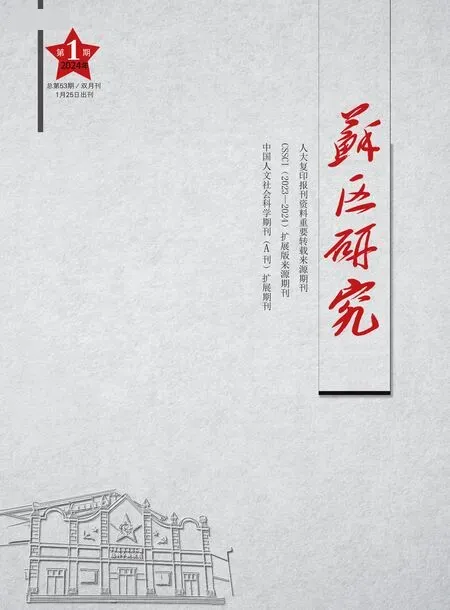鄂豫皖蘇區(qū)紅二十五軍武裝整改研究(1932—1934)
梁晨暉
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二十五軍,是以黃(安)麻(城)起義、商南(商城南部)起義和六(安)霍(山)起義的一部分工農(nóng)武裝為基礎(chǔ),于1931年10月在鄂豫皖革命根據(jù)地建立的一支主力紅軍。1932年10月,紅二十五軍主力隨紅四方面軍總部一同撤離鄂豫皖蘇區(qū),留在鄂豫皖蘇區(qū)的紅二十五軍其余部隊及各獨(dú)立隊伍根據(jù)情況變化與斗爭需要,經(jīng)過不斷整編,逐漸形成以紅二十五軍為核心力量的武裝建制。1934年11月,國民黨軍隊大規(guī)模“圍剿”鄂豫皖蘇區(qū),紅二十五軍開始戰(zhàn)略轉(zhuǎn)移。1935年9月,紅二十五軍到達(dá)陜甘蘇區(qū)與陜甘紅軍勝利會師,為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落腳陜北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近年來學(xué)界關(guān)于紅二十五軍的研究已屬不少,大多從紅二十五軍長征及紅二十五軍相關(guān)人物等角度入手,(128)陽勇、楚艷輝:《紅二十五軍長征中“擴(kuò)紅”述論》,《廣西社會科學(xué)》2018年第4期;楊軍紅:《孤軍北上:紅二十五軍的長征》,《江西社會科學(xué)》2017年第6期;黃亞楠:《紅二十五軍長征戰(zhàn)略轉(zhuǎn)移的提出及其抉擇》,《中國延安干部學(xué)院學(xué)報》2016年第5期。應(yīng)星較早注意到鄂豫皖蘇區(qū)紅軍的整編問題,(129)應(yīng)星:《1930—1931年主力紅軍整編的源起、規(guī)劃與實(shí)踐》,《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楊增強(qiáng)初步探討了紅二十五軍的整編問題。(130)楊增強(qiáng):《1932—1934年紅二十五軍的五次整編》,《商洛學(xué)院學(xué)報》2018年第3期。但總體而言,學(xué)界缺乏對紅二十五軍整改的專門研究,對紅二十五軍整編、改造過程背后所蘊(yùn)含的黨軍關(guān)系更未觸及。需要具體闡明的是,黨軍關(guān)系一般涉及三個層面,一是中央(包含中央分局)與軍隊的關(guān)系,二是地方黨部(包含省委、特委等)與軍隊的關(guān)系,三是軍隊內(nèi)部的軍事干部與政工干部之間的關(guā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