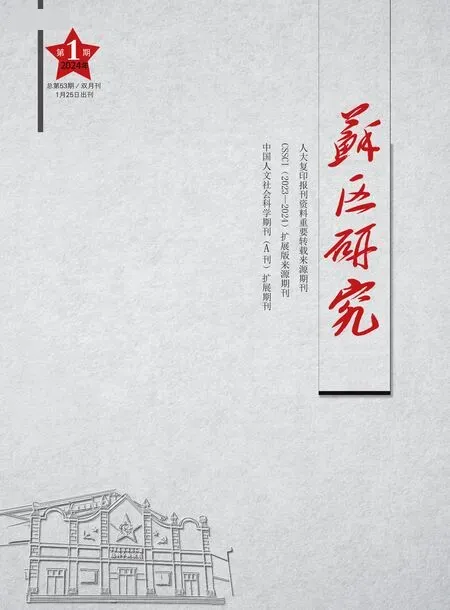收放之間: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共軍隊的連隊民主整軍(1947—1948)
劉星熠
新式整軍運動,是中共于1947至1948年間在軍隊內(nèi)部普遍開展的、以訴苦和“三查三整”(296)由于各軍區(qū)開展整軍的實際情況不同,“三查三整”的具體定義也不盡相同。總體上,按照朱德關(guān)于整軍問題的報告來看,軍隊中的“三查”指“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fēng)”,“三整”指“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fēng)”。(朱德:《整軍問題》(1947年9月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新式整軍運動》,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頁。)為主要內(nèi)容的大規(guī)模民主整軍運動。該運動大致起始于1947年的全國土地會議,結(jié)束于1948年戰(zhàn)略決戰(zhàn)前夕。出現(xiàn)于此承上啟下的關(guān)鍵時期,其重要性不言自明。關(guān)于這場運動,學(xué)界現(xiàn)階段已取得一定學(xué)術(shù)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探討運動中訴苦的開展,(297)張永:《解放戰(zhàn)爭中以訴苦會為中心的新式整軍運動》,《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6期,第72—80頁。對解放軍的改造等舉措。(298)盧毅:《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chǎn)黨改造俘虜?shù)臍v史經(jīng)驗》,《理論學(xué)刊》2013年第4期,第30—35頁;秦程節(jié):《溶俘:新式整軍運動中“解放戰(zhàn)士”思想改造研究》,《黨史研究與教學(xué)》2016年第2期,第14—24頁。總體上看,目前學(xué)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觀層面,較少與業(yè)已豐富的整黨研究成果對話,(299)從決策、部署到開展的全過程來看,整軍都與同期地方上開展的土改、整黨具有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目前學(xué)界關(guān)于整黨的研究已十分深入,參見黃道炫:《洗臉——1946年至1948年農(nóng)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歷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89—110頁;李里峰:《黨組織、黨員與群眾——華北土改期間的整黨運動》,《安徽史學(xué)》2012年第1期,第66—76頁;徐進、楊雄威:《政治風(fēng)向與基層制度:“老區(qū)”村干部貪污問題》,《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15—1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