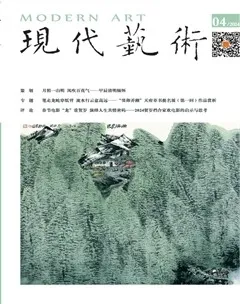情與法的深刻詮釋
王燕 羅勤
從表面上看,影片《第二十條》是一部賀歲檔的喜劇片,但是張藝謀導演并沒有放棄風格化的敘事,現實主義題材展現,外加浪漫主義情懷的敘事處理風格,以及披著喜劇元素的外衣讓整部影片呈現出該有的時代印記。
春節檔影片《第二十條》,名字來源于刑法中的第20條規定,突出正當防衛的法律條令,從生活中的小人物和社會中普遍關注的事情入手,通過三個不同人物的案件來展現老百姓的遭遇與法治的碰撞和沖突,體現群眾的呼聲,激化傳統觀念與現代法治的沖突,最終實現對法律公平和正義的守護。影片《第二十條》的出現,不難讓我們想到張藝謀導演早期的電影《秋菊打官司》,不同的是一個是對法律不熟的農村婦女,一個是都市里知法守法的檢察官,前者教會我們要用法律的武器保障我們的合法權益,后者則是從一個法律從業人員的視角讓法治堅守最后一道防線。這是時代的進步,是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展現。在此影片中,張藝謀導演同樣用其較強的作者意識在講一個時代的法治故事,用其畢生在電影中感悟的理念和信念完成一部全方位精彩的影片。
一、普法類現實主義題材影片的顛覆性創新
影片《第二十條》的故事取材會讓多人想到張藝謀導演早期的電影《秋菊打官司》,影片中秋菊“一根筋”式地要討個說法,堅定地要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同樣的現實主義題材,老百姓關心的題材,但此次張藝謀導演把矛盾的核心放在了條條框框的法令法條上,足以體現張導對社會現象的觀察力,在較為常見的普法電影中實現一種文藝與商業的創新結合,在春節檔打贏一場漂亮的仗。王永強案件、周顯平案件、賈云珂事件、何峰事件以及曹愛玲事件都是現實中發生的真實事件,所有的事件都指向一個中心就是“正當防衛”。
對于影片中普法類型的創新,雖然沒有改變對法律法條的普及和宣傳,但是影片中的敘事人物發生改變,以往電影的開篇都是普通老百姓拿著一紙狀書層層上訪,經歷九九八十一難通過各種途徑,得到高級領導的重視,然后下達命令審理案件,而影片《第二十條》,阻礙案件審查的是司法從業人員。影片中呂玲玲拖著王永強的案子不起訴,原因在于尋找丟失的關鍵的刀,這把刀也是能改變案件性質的刀,從呂玲玲的堅持上可以明確地展現出敘事角度的創新性。
相比于2023年國慶檔的《堅如磐石》,張藝謀導演在現實題材上的挖掘有了更新的認知和詮釋,他揚起現實主義這把利刃,揭露出普通老百姓現實世界中的迷霧,通過影片中三個事件來呈現現實主義題材的代入感。首先第一個故事是發生在男主一家的故事,身為檢察官的韓明,為了讓兒子考上一個好大學,不惜讓老婆李茂娟辭職全職在家照顧孩子,韓明也在市里掛牌工作,目的是把孩子送到城里升學率高的學校,增加考上好大學的幾率,無奈正義的兒子韓雨辰看到同學被霸凌,見義勇為幫助弱勢同學,反而出手打傷教導處主任的兒子。為了不讓兒子被拘留,李茂娟在處理中情緒過激打傷校領導被抓進看守所,這兩個事件其實也是整部片子中至關重要的一條線,也是為何韓明由剛開始處處謹慎圓滑的處事風格到最后能夠改變法律條款的原因。這個事件本身是大眾所熟知的校園霸凌事件,但是在這部電影中,導演用了高明的手段讓其在敘事的過程中作為一個激勵性事件存在,既體現了目前教育領域存在的問題,也讓觀眾有極強的事件代入感。第二個事件則是公交車司機張貴生的見義勇為,這條線相對比較簡單,張貴生作為一名公交車司機,在工作中看到女孩被混混欺負,因見義勇為導致傷害而獲罪,妻子因為受到打擊離開了,留下未成年的女兒,女兒因為相信法律的正義,手寫訴狀,想要父親繼續申訴,最后父親死在了申訴的路上。女兒拿著父親留下的頭盔,撕掉申訴書,淚如雨下地哭訴:“在你遇到這樣的問題時,你會怎么做?”這句話是問給韓明的,也是問給所有觀眾的,也是導演想要闡述拍攝這部影片的現實意義。在現實生活中這些多數會發生在新聞里的案件,沒有太多共情和感知,但是當真正發生在我們眼前的時候,我們又會怎么做呢,這部現實主義的電影給了我們最好的答案,張藝謀導演給了我們最好的答案。第三個事件是電影從頭到尾貫穿的事件,王永強和聾啞妻子郝秀萍因為女兒看病借下高利貸,被村霸劉文經長期欺辱,王永強在親眼目睹妻子被多次強奸后,恐慌之下刺傷劉文經導致劉文經去世,劉父則要求殺人償命,利用烈士家屬和村里霸主的勢力制造輿論壓力和威逼利誘郝秀萍母女,最后郝秀萍被逼絕望跳樓,此案件在呂玲玲和韓明的堅守下,王永強被無罪釋放。呂玲玲和韓明堅守住了法律的底線,而王永強和郝秀萍也終于等到了光明的結果。這些現實生活中真實發生的相似案件有很多,無疑都在向法治提出疑問,到底法能不能容情,這是在情和法中找到一個最佳答案,就達到了和觀眾的高度共情,既是讓百姓對法治更加信任,也是給執法者提出新的挑戰。對于這部電影,最高人民檢察院連發兩篇影評,指出電影中的故事“是真真切切發生在我們百姓身邊的事情,看似遙遠,卻時時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影評還提到,《第二十條》不僅是一部法律題材的電影,更是一部屬于每個人的生活片,會影響一個人的是非觀和正義感。
二、浪漫主義情節的人文氣息展示
張藝謀作為第五代導演,對宏達的歷史故事有著極深的執念,從張藝謀導演早期的作品中,《大紅燈籠高高掛》《紅高粱》,再經歷文藝到商業的轉型,《英雄》出現在觀眾的視野,再到近兩年的命題式的現實主義題材,《滿江紅》《堅如磐石》,每部電影都是張藝謀導演對不同時代的反思和解讀,也讓觀眾和社會更好地審視我們的時代和社會。《滿江紅》這部電影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例證。一個命題題目,張藝謀導演給了一個超出滿分的答卷。尤其是在最后高潮時“假”秦檜慷慨激昂地吟誦《滿江紅》,然后由將士一層層傳頌出去,再到門外的小孩子跟著吟誦,將整個家國情懷體現得淋漓盡致,這個時候封閉的環境空間發揮到了敘事的極致,時間和空間上的敘事達到了空前的一致,極顯浪漫主義情懷詩意,無不讓觀眾動容。同樣的方式張藝謀導演放在了《第二十條》的結尾,在整部電影中,講述的三個事件都是壓抑的,都是悲憤的,都存在一個正當防衛卻又防衛過當的情節。不管是案件的檢察官呂玲玲還是掛職的韓明,還有因為見義勇為而反被告的韓雨辰,以及因為保護兒子沖動施暴的李茂娟,甚至是跳樓后救治在床的郝秀萍,失去雙親的張貴生的女兒,影片中大多數人的內心都是委屈和不甘,需要一個情緒釋放的端口,也是整個劇情高漲的火山口,故導演在最后的聽證會上上演了“雷佳音”充滿激情地慷慨陳述。這個情節極具有浪漫主義的人文氣息,也正是因為這段高潮的陳述,讓整個故事講得合情合理,打破了原有的冰冷的法治條令的禁錮,不僅讓百姓看到社會法治的溫暖,還有執法人員“我們辦的不是案子,而是一個人的人生”的態度。但是縱觀王永強案主辦檢察官呂玲玲在與韓明爭論案件時發出的質問時,韓明例舉了“2014年周顯平案,故意傷害罪;2015年賈云珂傷人案,故意殺人罪;2016年何峰傷人案,故意傷害罪;2017年曹愛玲傷人案,故意傷害罪”等。這些案件與王永強案件一樣,都指向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條——正當防衛,包括韓明自己辦的張貴生的案子,結果都是防衛過當結案,這就是現實,但是導演打破了事實的常規,讓正義的結果浮出水面,這就是導演內心浪漫主義的真實表達。影片是將現實主義的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相互融合,在“笑中有淚”的悲喜劇式的戲劇框架中,呈現一堂高水準的“普法課”。
電影本身是對現實社會和時代的映照,通過一個故事展現一個事件的縮影,是社會發展的鏡子,但是電影又是夢幻的、理想的、圓滿的,之所以強調社會現實是因為身為普通觀眾的我們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導演當然也深知此理,故在故事的結尾給我們一種夢幻煽情的相信的動力,正是因為好的結局的事件難得,才有了電影,才是電影呈現的意義,也感謝導演激發觀眾心中的夢想和希望,共同推進了法治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這也是浪漫主義結局的真實意義所在。
三、輕喜劇和黑色幽默式的敘事風格
在這樣一部現實主義題材的影片中,張藝謀導演還是大膽地嘗試了輕喜劇和黑色幽默的方式,這種方式足以緩解沉重、壓抑的訴訟案件,讓整個影片的情緒得到一些舒緩,相較于大多數導演把喜劇的元素放在情節的設置上,張導則更多地把重心放在了韓明和李茂娟兩夫妻上。影片一開始,敘事的重心從王永強刺傷劉文經后工人討要工資不成堵住檢察院的大門開始,看似是一個難題的解決,韓明的主要人物性格就清晰地體現出來,一個中年男人,遇到事情不慌不忙,用豐富的經驗機智地解決困局,想到用司法援助的方式解決工人的問題,也從側面展示韓明內心深處的人民公仆形象,但是轉過頭就是對于上司領導的“圓滑”行為,讓我們更加直觀地了解到韓明的人物形象。韓明也是整個事件的核心人物,三個事件串聯在一起,才達到最后聽證會上的背水一戰。對于這個人物的塑造上,導演是花了很多心思和精力的,工作上圓滑逢迎,作為父親對孩子耐心教導,作為丈夫對老婆左右逢迎,作為同事以及曾經的戀人對呂玲玲善意引導,這些角色中都摻雜著微喜劇的元素,是一種藝術的表達方式,當然也是化解沉重主題的高明手段。
影片中有個爭議比較大的點,就是韓明和妻子李茂娟的“唇槍舌戰”,看得出來導演在拍攝的時候給了很多演員自由發揮的空間,包括爭吵到激烈的時候忘記臺詞的真實反映,但在你一言我一語的高強度輸出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會有些“聒噪”,前半段戲包括韓明兩夫妻因為前任呂玲玲的爭吵,對于解決韓雨辰打架的爭吵以及和大舅子的爭吵,以至于現場的觀眾都感覺到聒噪,但是導演的厲害之處在于他預判了觀眾的情緒,當觀眾馬上要不耐煩的時候,整個事件的走向開始變得緊湊,故事到達高潮,觀眾也就忘記了之前的情緒,反而被帶入到事件中,也就是在這種潛移默化的文化輸出中開始接收到法治的審判。這種節奏的把控也是非常考驗導演功力的,但是張藝謀導演每次都做得很出色。依托于賀歲檔的背景下,影片《第二十條》也要讓位于商業元素,影片的敘事雖然一直在沿用現實主義的帶有“軸”特性的秋菊堅持要的伸張正義,這種普通模式的敘事在類型片中并不討喜,但是導演骨子里的這種堅持是一點都不想放棄,所以安排了呂玲玲的角色,她一直在堅持正義,一直不改變,即使被停職依舊說服韓明繼續審理此案。這里的巧妙安排是對韓明人物角色的塑造,他是一個商業電影背景下被修改的人物。其實拍攝都市題材導演還是非常有經驗,比如早期的《有話好好說》,同樣展現的是現實社會中大小人物的心境和想法,同樣在拍攝上也延續了李保田和姜文的經典巔峰對決片段,這些都是在行業領域內室內調度的教科書級別的拍攝技巧,故在整個的拍攝影像上能夠完美地契合到劇情,沒有過度的渲染和表達。
從表面上看,影片《第二十條》是一部賀歲檔的喜劇片,但是張藝謀導演并沒有放棄風格化的敘事,現實主義題材展現,外加浪漫主義情懷的敘事處理風格,以及披著喜劇元素的外衣讓整部影片呈現出該有的時代印記。縱觀整部影片,三個真實的血肉案件將情與法有機地交融,并深刻地探討了法理上的矛盾爭議,用影像的方式對刑法中的第二十條做了深刻全面的解讀。影片傳達了民意和法治的互動,把現實主義的利劍與法治社會的良知編織在一起,在電影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