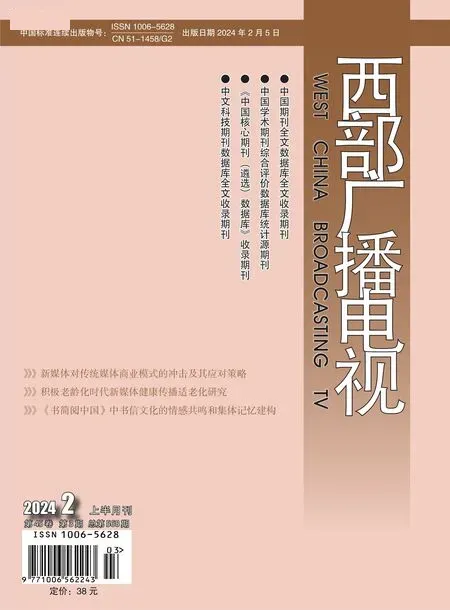《書簡閱中國》中書信文化的情感共鳴和集體記憶建構
李雨格
(作者單位:浙江傳媒學院)
在這個互聯網高速發展的時代,生活節奏的加快促成生活方式的改變。紙質書信逐漸被電子短訊取代,紙質書信的應用頻率大幅下滑,逐步退出了大眾的視野。然而,這是否就意味著書信文體因此失去時代立足點,消散了承擔文化情感的能力?傳媒影視行業一直是我國文化傳播的重要窗口,電視節目能夠利用其獨特的文藝特質在思想文化傳播領域對人們的思想產生很大的影響。在電視領域早有《朗讀者》《見字如面》《信·中國》等朗讀式綜藝節目彰顯書信文化的魅力,而2021年央視紀錄片頻道播出的《書簡閱中國》再次把關注點聚焦在古代書簡信件上,以虛實結合的情境演繹與創新性的技術,發掘并呈現出傳統書信的內涵,成功收獲豆瓣8.4分的高分評價。這一人文歷史紀錄片利用書信的私密特性,在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共生關系下完成新記憶的建構,喚起了當代民眾的情感共鳴。
1 書信文體的私密性與對象性造就情感共鳴
根據《卜辭通纂》中有關甲骨卜辭的記載,最早的通信文字使用出現在軍事領域,戰士們利用文字傳遞來完成軍情的通信與匯報,這種通信文字被認為是以“信息傳達”為基本屬性的書信體的本宗。隨著人類文明水平的不斷提高,社會化活動也日趨豐富,遠距離的信息傳輸變得越來越必要,就此郵驛體系也得到逐步的完善與發展。書信文體的使用范圍突破了軍事領域的局限而向市井拓展,書信文體逐漸流通并遍布于社會的各個階層,民間書信得到廣泛發展。民間書信的發展與平民化流通也豐富了書信文體的媒介功能,除了信息傳輸的基本功能外,書信文體更增出情感傳遞的功能,被賦予“情感對話”的典型文體意義。有了情感的介入,書信文體便由僅傳遞信息的文體,逐漸發展成為有精神內涵與藝術可讀性的文體,具有了一定的文學性。也正是因為如此,古老的書信在今天仍能映出歷史的倒影,以共通的情感撥動讀者的心弦,引發人們的欣賞與情感共鳴。
在普遍使用方式上,書信文體多用于遠距離傳輸信息的情況。書信雙方由于空間距離限制或其他限制因素無法進行面對面交談時,便需要借助第三方媒介——信紙,完成間隔性的信息和情感傳達。在傳輸的過程中,傳達內容具有非公開性,傳達結果僅指定收信人可見。由此觀之,書信文體的既定使用設置本身就蘊含極強的私密屬性,這種媒介形式為書信雙方交流構筑了一個專屬于他們的私密空間,在這個空間之內,他們可以直抒胸臆,暢所欲言。書信文體的文本安全滿足了人性中某種原始的生存需要,即“本體安全”的需要[1]。因此,相比其他文學作品中表達使用的刻意性,書信文體中表達出的情感往往更加真實,所進行的“情感對話”也更貼近筆者本心。《書簡閱中國》正是把握書信文體中的這種“更加真實”的情感,因而更容易喚起觀眾的情感共鳴。在《再大的風我都去接你》一集中,觀眾看到了不一樣的康熙皇帝。看到康熙與發小曹寅之間的書信往來內容,不禁讓人們感嘆,除了君臣的尊卑禮數,原來還有來自人間真情的溫暖滋味。康熙在朱批曹寅的奏折時甚至還會畫上一朵小紅花,原來一向威嚴的帝皇在面對發小情誼時,也會流露出可愛溫存的一面,這樣的反差感正是源自書信的私密語境下的“更加真實”的情感展示。
書信文體的私密特性所帶來的真實感能夠引發觀眾情感共鳴,同時,私人書信的公開展示也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觀眾“窺私”的欲望,從而更加提升共情的興致。弗洛伊德認為,“窺私”來源于“本我”的本能欲望,這種欲望來自人們作為獨立個體對另一個體產生好奇關注的本能心理。同時,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也提到,窺私欲源自個人積極探求環境的需要,人們總會對周圍未知的、神秘莫測的事物心馳神往。因而《書簡閱中國》將書信進行公開呈現也滿足了觀眾對古人“私信密語”內容的好奇,從而激發觀眾對人文歷史故事的興趣。歷史上的第一封家書究竟寫了什么樣的內容?秦嘉和徐淑這對恩愛夫妻怎樣千里傳情?嵇康和山濤兩位昔日至交好友為何立下絕情書?紀錄片使觀眾在貼近歷史人物心境的同時滿足其對窺私欲望的集體心理的宣泄。
《書簡閱中國》利用現代化的視聽表達方式,將書信私密語境中所呈現的真實感進行還原與展現。結合書信的內容進行合理想象,將書信雙方的故事進行情景再現與演繹還原。秉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中現實主義的原則,演員沉浸于歷史人物角色之中的表演極具歷史還原的真實感。同時,攝制組也對情節設計進行嚴格的史實考究,從而使布景與服裝道具極具歷史感;并且,導演組在劇情設置上著重捕捉關鍵細節,以此帶給觀眾更真實的沉浸感。在私密語境下形成對話關系是書信區別其他文體的典型特性。倘若沒有對話,便無法形成書信交流。因此,書信體成立的根基在于預設對話環境的產生,包括在書寫之初擬定對話對象,以對話的口吻進行語言表述。其間,除私密性呈現的真實感與引發窺私欲的好奇心理以外,這種指定交流身份的第二人稱對象性語境表達也為書信文體增添了代入感,正是這種交流設計進一步增強了書信文體引發的共情。《書簡閱中國》將這種對話進行視覺化的還原再現,把觀眾腦海中想象出的虛擬對話場面轉化為現實畫面,營造書信雙方紙墨間的情感氛圍,引發觀眾共鳴的同時,書信文體“遠距離對話”也因郵遞屬性達到超時空“傳情”的效果。
2 郵遞特性在情感跨越時空傳輸中的優勢
書信作為一種具有遠距離傳輸功能的應用文體,在運用之初便帶上“時空間離”的標簽。受古代傳輸技術的限制,書信傳達往往要歷經幾日到幾月不等的時間,倘若遭逢變故,能否順利送到收信人手中都難以預料,詩人王灣曾感慨“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因此,不同于當今媒介的即時送達,古代書簡文本有著更強的“耐力”,這也為其跨越古今傳輸、引發延時共情提供了可能。《書簡閱中國》之所以選擇以書簡為線索,利用現代視聽手段再現優秀文化經典,離不開書信文體在藝術表達中的跨時空傳輸優勢。書信的溫情可以跨越山河送到收信人手中,便也可以穿梭千年被當今審美捕獲。書信所蘊含的情感魅力古今共通,其郵遞特性賦予了它“千里面語”的可行性因素[2]。
從字緣結構角度分析,“信”字本身就帶有“書信”與“使者”的雙重含義[3]。由此觀之,傳輸環節對于書信文體成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既然書信對話的成功與否是書信文本成立的關鍵,那么傳輸環節是否順利,書信能否完成“有效性傳達”便成為書信文體存在所依托的重點。也正是這種傳達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使得書信郵遞出的瞬間就被賦予情感守望的色彩。這種古今共通的等候與期盼之情連通著歷史長河間人類的共鳴。傳達的有效性成為塑造書信文本實現價值的重要條件與籌碼,因而書信傳遞中寄收雙方對于對話最終實現的盼望與渴求是無比真切的。這種情愫與由此引發的“遠距離想象”構成書信文體藝術賞析的亮部[4],也是情感共鳴的關鍵。在《再大的風我都去接你》一集中,元稹聽說有信送到,不用看就知道是好友白居易寄來的,還沒等出家門就已經淚流滿面。這正是知音之間,在得知對方平安后,無法掩飾的情感。在那個變幻莫測的年代,白居易的一封書信,使得元稹多日以來的擔憂與惦念得以平復,終于可以心石落地,元稹激動之情溢于言表。書信中體現的元白之間的這種守望之感也使得觀眾產生共鳴。在《小人物大歷史》一集中,獨自守在家中的母親默默期盼上戰場的兒子寄信回家,不單單是期盼一份“我兒生還”的安心,更是期盼收到信件后,能觸碰并感受兒子筆記的溫度。友情與親情間的真摯情感使人動容,書信傳遞中闡發出的“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般的“遠距離想象”更令人深感共鳴。
書信文化中由于“時空間離”而引發的對親人及其所處環境的細膩構想被《書簡閱中國》細致的影像表達刻畫出來。顧貞觀為救老友吳兆騫不惜寄人籬下,本應享受安逸生活的他鍥而不舍地為吳兆騫案爭取案件重審機會,以致不惜下跪求情。這封書信的兩端分別是身在府邸的顧貞觀和苦寒獄中的吳兆騫,導演利用蒙太奇的剪輯手法將兩人相距千里、處境相差甚遠的時空間離對比聲情并茂地演繹出來。在書信文字中推衍出現今人們對古典情思的想象,“千里之行”的跨越式傳輸引發跨時空的共鳴。翻開歷史書簡,重拾古人記憶,進而喚醒時代的回響。《書簡閱中國》對個體書信的展示,更是揭開了集體記憶的面紗。兩者共生關系下的互相影響與互相展現,烘托出歷史文化的厚重的同時完成集體記憶的更新建構。
3 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共生關系建構
在《留取丹心照汗青》一集中,《書簡閱中國》收錄并展示了岳飛、文天祥、林則徐、陳京瑩等多位愛國將士的書信。其中“壯懷激烈”的言辭無不昭示著祖國存亡之際這些民族英雄胸懷大志與舍生取義的犧牲精神。無論是岳飛英勇抗金,是林則徐虎門銷煙,還是文天祥寧死不屈,從這封封書信中可以提煉出屬于這些民族英雄的個體記憶,而這些個體記憶并不是憑空或孤立存在的,它們都蘊含著集體記憶的烙印,正是這些個體記憶拼湊塑造起歷史時代風貌,建構出立體生動的歷史集體記憶。個體記憶是集體記憶的反映,個體記憶是集體記憶的一個部分或一個方面,每個印象或事實雖只涉及特定的個體,但無不與社會環境、思想聯系在一起。“只有把記憶定位在相應的群體思想中時,我們才能理解發生在個體思想中的每一段記憶。”[5]這一集紀錄片通過對書信故事的展現完成對歷史記憶的回溯,將山河破碎、風雨飄搖的歷史環境再現于觀眾面前。配合豐富的史實資料佐證,使得觀眾加深了對宋末、清末動蕩格局間歷史脈絡的認識及對于歷史人物的理解,某種程度上是對當代個體記憶的更新與重塑,也是對保家衛國的社會價值觀念的傳承與發揚。法國著名媒介學家雷吉斯·德布雷認為,媒介化可以使一個觀念轉變成為物質力量,媒體則是媒介化當中一種特殊的、后來的、具有侵略性的延伸。在《是你告訴我愛情的模樣》一集中,李商隱寫給柳仲郢的書信中,短短一句“雖有涉于篇什,實不接于風流”道盡他被世人構陷之苦。通過對李商隱與友人密信的揭示,紀錄片為后世之人開拓嶄新的思路,使得觀眾得以跳脫出“牛李黨爭”的閉塞,領悟史書中“罵名昭著”的李商隱更加真實的感懷,體會其淪為政治斗爭犧牲品的苦痛,共鳴于他與王氏愛情的悲哀。這便是《書簡閱中國》作為一部頗具關注度的人文歷史紀錄片對當代個體記憶帶來的直接影響。
正如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故事與產物,不同時代形成的記憶亦是如此。莫里斯·哈布瓦赫認為,世上沒有完全獨立產生并存在的記憶個體,記憶事實上是以系統的形式出現的。個體記憶的形成必將潛移默化地受到其相應群體思想的影響,同時構成新的集體記憶。《書簡閱中國》創新性地使用多維度的敘述方式,激發新時代審美樂趣。通過對個體記憶的重塑逐步形成廣泛的影響,進而刻畫當代群體的記憶。這一次金鐵木一改以往《大明宮》等傳統人文紀錄片較為嚴肅正式的講述風格,利用更為輕松新穎的表達方式,將煩瑣難懂的古文書信轉化為通俗易懂的現代語言表達并附以配音展現。除了精心構圖的實拍畫面,《書簡閱中國》還突破次元壁壘,利用二維計算機動畫(Computer Graphics, CG)等手段將史實“畫”著講述出來,如秦人不重視文書而諷刺讀書人為“豎儒”的現象、古代士兵打仗的模式圖例、牛李兩黨對峙斗爭的畫面等。設計表達上創新地利用水墨畫的方式畫出“國風版”微信對話框以及微博熱搜榜等觀眾熟悉的界面講述人物故事,輕松歡快的氛圍間歷史文化知識也更容易被觀眾所廣泛接受。《書簡閱中國》調動個體記憶并將優秀傳統文化與價值觀念逐步根植其中,呼吁回歸與傳承優秀的文化價值導向,進而逐步完成新的集體記憶的建構。在龐大的集體記憶中思考個體回憶內容的定位,在個體記憶的影響下進一步建構全新的集體記憶,兩者共存共生之下,書信文化存儲個體記憶從而喚醒建構集體記憶的魅力盡顯。
《書簡閱中國》的情感追溯與表達以書信為媒介線索,同時也著重突出書信這一文化載體在敘述語境中的核心地位。這部人文歷史紀錄片圍繞書信展開,以私密對話重啟交往自由,“跨時空傳達”重拾書信件文化的魅力,喚醒人們深埋心底的情感與集體歷史記憶。《書簡閱中國》突出書信文化在中國博大的傳統文化歷史中不可替代的位置,為人文歷史紀錄片選題創作提供了多元化的思路。除了特色中華美食、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傳統題材外,還有書信媒介也可以承載厚重的傳統文化基因。此外,情境再現、CG技術、虛擬特效等多重表現元素的嘗試更是探索了新時代紀錄片創作的邊界,為“大紀錄片產業”發展打造“紀實+”的創新形態延伸提供啟示。《書簡閱中國》是響應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增強文化自信,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兩創”精神的積極嘗試,能夠為紀錄片創作更好地宣傳優秀傳統文化、講好中國故事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