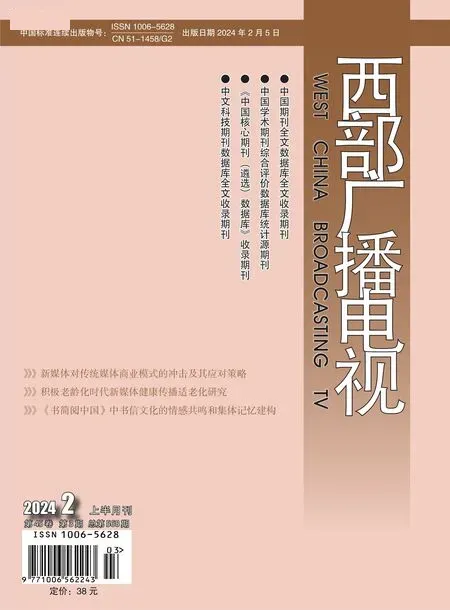電影對文學文本的影像重構
——以《河邊的錯誤》為例
張松琪
(作者單位:河北傳媒學院)
影片《河邊的錯誤》改編自余華的同名小說。從文本意義上來說,《河邊的錯誤》作為先鋒派小說本身故事為偵探懸疑題材,在文本結構中設置空白性和不確定性,讓讀者能沉浸到文本故事的解讀中。電影同樣也設置了許多的空白和召喚結構,給受眾留下了想象和解讀的空間。該影片的英文名稱“Only River Flows”(只有河流繼續流淌),與余華的觀點“藝術家只能來自無知,又回到無知之中”相契合。
文本依賴的是大眾的想象,大眾通過想象填補作品中的空白從而生成自身的作品世界。而影像作品通過具體可感的畫面和聲音來構建影視空間,觀眾在具象化的屏幕空間中獲得審美體驗,所以經典文學改編為電影是導演與作者的較量,導演在改編時要注意原著與影像化的平衡。導演為突出《河邊的錯誤》的畫面質感和年代感,采用膠片的拍攝方式,為體現荒誕感和懸疑感,在這部類型片中融入謎題電影的風格和元電影元素,使得電影情節更加撲朔迷離。
1 重構:文學意向的轉換
中國的故事片電影一直延續著以經典名著為藍本的創作傳統,改編過程中導演和編劇需要將文本空間轉化為影像空間,使文本能夠以可感的畫面呈現在人們眼前,這個過程需要傾注導演和編劇大量的心血。作為余華先鋒小說的《河邊的錯誤》由文本改編為電影同樣經歷了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在將這部文學作品改為電影的過程中,導演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將文本中的文學隱喻轉化為電影的視聽語言,將文學意象轉化為電影中具體可感的真實畫面。
在文本中隱喻不單作為一個修辭手法使用,還可以傳達深層次的意義,通過本體、喻體表達思想情感、激發讀者的想象,增添文學作品的解讀性,使讀者可以通過某種事物解讀文本中的含義。“隱喻的本質就是通過另一種事物來理解和體驗當前的事物。”[1]在將小說改編為電影時,文本隱喻需要從文字描述轉化為畫面呈現,并通過符號化的視覺信息體現。在電影中馬哲作為主人公穿著標志性的皮夾克,皮夾克在劇情中充當了重要的符號表征。電影開頭,在滿屋子穿著制服的同事之間,穿著皮夾克的馬克顯得格格不入;在和領導打球時,他不給領導讓球;拍合照時穿著皮夾克站在一堆穿著制服的同事中間。這些情節呈現出他不善與人交際、性格上的孤僻。之后,馬哲的穿著由皮夾克轉換為便裝,最后他眼神迷離地身著警察制服站在領獎臺上,這隱喻著社會對個體的規訓。當馬哲精神崩潰走入河流后,瘋子站在岸邊穿上他的夾克,象征著二者身份上的互換。由此可見,在電影創作過程中,導演使用服化道、場景設置、人物刻畫等多種手法將文本中的隱喻呈現在影像之中,從細節之處將抽象的文字轉化為直觀可感的畫面聲音,觀眾在觀看影片的過程中能夠仔細推敲導演設計畫面的用意,從而使影像解讀更添意味。
文學隱喻通過文字將隱喻編織到故事之中,而電影則通過畫面中的符號、蒙太奇的組接進行隱喻。“藝術創作離不開想象,藝術家在進行藝術想象的同時,經常選取人們生活中熟知的事物來描述人們不太熟悉的事物,這一過程與隱喻不謀而合。”[2]在結構學領域電影中成組的鏡頭能夠對現實世界進行影像化表征。《河邊的錯誤》中導演通過夢境與現實交織相連,使用大量意象化的鏡頭,例如乒乓球從影院的屏幕中散落一地,暗喻馬哲在一系列案情的發展下精神出現崩潰。在馬哲喝醉酒射殺瘋子的過程中,觀眾并沒有看到瘋子被槍射中的直觀畫面,卻知道瘋子被馬哲連開三槍,因為電影通過不同機位角度的變化、畫面的選擇,完成了對情節的敘述。而該電影之所以讓觀眾感覺撲朔迷離,是因為在影片中現實和夢境并沒有隔絕開,觀眾以為這個段落中馬哲已經犯下大錯殺掉瘋子,通過下一個段落的鏡頭,又發現那只是馬哲的幻想。在很多電影作品中,導演為了讓觀眾分清電影空間中的現實和夢境,會將二者進行區分,通過模糊的鏡頭、演員夸張的表演、意象化的音樂、怪異的色彩突出夢境。例如電影《八部半》中,男主人公圭多面臨個人感情生活的混亂與電影拍攝的雙重壓力,夢境與幻覺不斷侵入他的現實生活。在克里斯托弗·諾蘭執導的影片《盜夢空間》中,劇情游走于夢境與現實之間,以旋轉的陀螺作為區分現實與夢境的依據。但是在《河邊的錯誤》中,導演用一種混淆視聽的方式,將現實與夢境拼接起來,以一種平滑的敘事方式,讓觀眾后知后覺。
此外,電影開頭小男孩與朋友玩警察抓犯人的游戲,當他推開一扇“真相之門”后,看到的卻是滿目廢墟。而這一段隱喻著馬哲對于真相的追求,最終得到的是一片虛無。電影以影像化的敘事始終在突出文本中所體現的非理性的敘事話題,并且運用大量的意象化、夸張的手法,突出主人公在案情一步步進展的過程中,精神開始崩潰。文學化的語言留給讀者更多的想象空間,而可視化的影像同樣可以用隱喻、象征、符號化的鏡頭來構成影片的召喚結構,使觀眾能夠通過解讀感受電影內部所表達的思想。
2 追溯:哲學命題的討論
電影開篇引用了阿爾貝·加繆在作品《卡利古拉》中的一句話:“人理解不了命運,因此我裝扮成了命運,換上了諸神那副糊涂又高深莫測的面孔。”阿爾貝·加繆是法國著名的哲學家,是“荒誕哲學”的代表人物,在其作品中深刻揭露了人在社會中的異化、孤獨、罪惡和死亡不可避免,但是他認為人們依然可以在荒誕的世界中追求真理和正義。導演在電影開篇用加繆的話帶出了他對于文本深層次的哲學理解,使影片增添了荒誕主義的意味。
《河邊的錯誤》在人物設置上呈現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中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概念。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中“本我”是潛意識的表現,更接近獸性;而“自我”遵循現實原則,介于本我和超我之間;“超我是人格中的道德成分,是由父母及其他社會權威的是 非觀念和善惡標準內化而來的,其形成主要是由兒童的獎懲經驗決定的”[3]。“超我既置自我于積威之下,乃臨之以最嚴格的道德標準;可見我們的罪惡之感也即超我壓迫自我的一種表示。”[4]“超我”和“自我”會通過道德來監管約束“本我”。而在影片中瘋子就是“本我”的化身,是一種無序的存在,也是個體無意識的物化體現。影片中馬哲之所以不能很快結案,是因為他是以正常的思維方式去分析瘋子為什么把這兒幾個人都殺了,想要找出其中的隱秘的關聯或者是某種聯系。而作為“本我”化身的瘋子就是瘋癲的、非理性的象征,他的想法是非理性的、無序的,所以就導致馬哲在分析案件的同時自身陷入了精神陷阱。
在文本中馬哲是作為“超我”存在的,4個被害者代表著“自我”,瘋子則是“本我”的化身。馬哲在不斷尋找真相中,發現了被害者的秘密,即幺四婆婆的受虐癖、王宏的婚外情、理發師的異裝癖,間接導致了他們的悲劇。隨著案件的一步步推進,馬哲精神崩潰,他在夢境和幻想中以“本我”的姿態將瘋子繩之以法。這表明“非理性瘋癲對于理性世界的威脅促使理性世界采取了暴力手段將瘋癲從理性世界鏟除,然而這種鏟除卻是以破壞理性世界秩序為代價的”[5]。現代社會更加注重事件的結果,而忽略掉過程的重要性。在這種錯亂的非理性世界中,不論是小說作者還是電影導演都需要給受眾一個結果,諷刺的是,馬哲想要在非理性世界中找尋一個理性的結果,但是在探尋的過程中,自己也成為秩序的破壞者。
人類因為理性思維能力而區別于動物成為萬物的靈長,但是世界本身就存在很多不確定性,而在這些不確定因素的面前人的這種理性思維就會陷入“不可知”的困境。從古至今,人類對于世界中“不可知”都有著深刻的思考和研究。例如,中國的典籍《周易》中所展現的命、運、氣以及王陽明的心學,都在探討人們如何在不可知的世界中正確認知世界。《河邊的錯誤》中折射著中國古代哲學中的命、運、氣,正如馬哲的汽車車牌是31415,即類似數學中的圓周率π,暗含無限和無序。馬哲的孩子被診斷出可能存在智力障礙,電影結尾孩子與瘋子做出了同樣的玩耍動作,暗示馬哲的孩子很可能會成為下一個瘋子,呈現出荒誕的循環。導演為了呈現非理性將生活中的偶然性和不可知性放大,使得整部片子都呈現了一種荒誕的宿命感。因為偶然性因素,詩人和理發師出現在案發當天的河邊,之后詩人被瘋子殺害,理發師被發現異裝癖的秘密,從大樓上一躍而下。現實的不可知和這種荒誕的宿命感給影片蒙上一層悲劇的面紗,使馬哲和觀眾陷入“理性的怪圈”。
3 再現:少數群體的呼喚
現實主義影片注重對于生活的再現。在電影創作中運用現實主義創作手法,旨在通過對現實生活客觀、具體的描寫,從作品的場面和情節中自然地體現出作者的思想傾向和情感,展現真實生活中的人和事物,引發觀眾思考當下社會中的重要議題。現實主義電影作品作為“現實的漸近線”,要求導演在創作過程中以求真的態度、虛擬的形象,打造接近真實的體驗。《河邊的錯誤》導演為貼合20世紀90年代的風格,在拍攝過程中使用16 mm的膠片拍攝,為突出年代感特意在膠片中加入劃痕,制作后期專門設置了三間沖洗膠片的暗房。
案件發生在河邊,南方潮濕的小鎮不停地下雨,破壞了現場證據,這些微妙的設定與電影的敘事邏輯相契合,經得起觀眾推敲。這些細節的處理、細膩真實的還原都是現實主義作品慣用的創作方式。現實主義電影只有體現真實的場景,基于真實性創作,經得起觀眾推敲,才能立足于市場和大眾。
現實主義的影片中需要塑造可信的典型人物形象。“典型是共性和個性的統一,或普遍性和個別性的統一。”[6]典型形象要求藝術家從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出發,對客觀生活加以藝術概括,在生活中挖掘人物原型,創作出的具有較高典型性的藝術形象。例如,瘋子的形象常常會出現在電影和文學作品中,有著強烈的隱喻性特征,導演選取身材高大的演員能夠強化其作為連環殺人案兇手的軀體化呈現,“瘋子”的形象象征著在約定俗成中的常規社會里不遵守規矩的異類。又如,《河邊的錯誤》中,王宏的詩人形象是通過他戴著眼鏡在詩歌大會中侃侃而談,以及那封寫給情人的訣別信等情景來塑造的。幺四婆婆是電影中最早出現的人物,但也是電影中最難刻畫的一個形象,大銀幕創作傳播受到多種限制,所以電影通過馬哲在房屋中看到鞭痕的鏡頭隱晦地表現出幺四婆婆的受虐傾向以及她和瘋子之間的關系。而這些隱秘的事件和關系被放置在大眾視野中,他們將面臨傾瀉而下的流言蜚語和同事、親人、村民的審視,所以他們的死亡可以被認為是社會對小人物的一次無意識“傾軋”。
導演將自己的思想傾向和情感隱藏在影片內部中,以“瘋子”為媒介,呈現出一連串社會中異化、被異化和正在異化的人物,在這些異化的人物中探究人與集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文本中人物形象最大的改編是將理發師的無意識行為轉變為一種合理的行為,將他塑造為有著“異裝癖”的人物形象,使他身著女裝卷進兇殺案中,不論是否能夠洗脫嫌疑,他身著女裝頭戴大波浪的形象和之前被判“流氓罪”都會被公之于眾。理發師是馬哲追求真相的頭號受害者,而他跳樓砸在馬哲車上也成為壓倒馬哲精神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
電影選取社會中少數群體進行刻畫,采用夸張的手法,將現實與影像之間的裂縫彌合,讓觀眾感受到人物對于現實生活的困頓與迷茫以及他們在面對眾多審視者的目光下所作出的反應。當觀眾將其與現實聯系,進行深入思考,對于這個影片中誰是真正的兇手,或許就有了答案。
“元電影是回歸電影最基本的概念來省思電影自身,在影片中展示電影制作過程,或電影再現形式的符號系統”[7],也是一種比較抽象和自我意識強烈的創作方式。魏書鈞在其影片中多次表達出他對于“元電影”概念的自我認識,影片中警察在電影院辦公,在舞臺上領取“三等功”功勛獎勵、電影院招牌被重重砸在地上、放映機被燒毀,通過這些夸張、顛覆傳統邏輯的情節和畫面,用電影的造夢功能讓觀眾在真實與夢幻之間游離,感受從少數者那里帶來的靈魂叩問和社會倫理。近年來,中國電影不斷找尋新的突破口,魏書鈞對于電影的創作基于他對于電影本身的理解和熱愛。《河邊的錯誤》將現實與夢境置于影片內容中,探究電影新的表現方式,將目光集中到社會上的少數人群身上,以導演獨有的創作風格,為中國電影的發展加入新鮮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