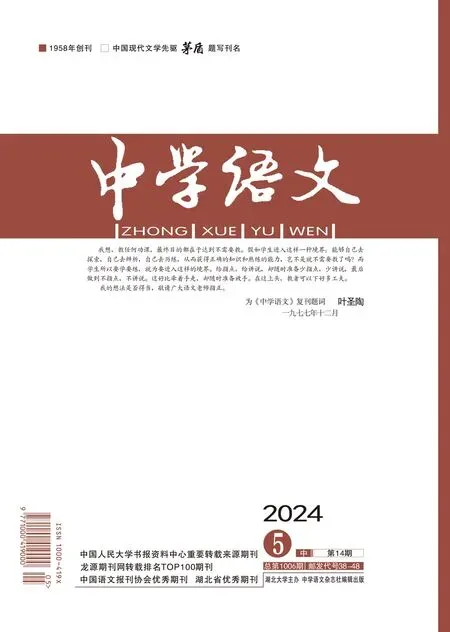巧于因借 情景交融
—— 高中文言文思辨性閱讀教學策略
左金苗
文言文思辨性閱讀教學的核心目標是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在思辨性閱讀教學模式下,學生能深入理解作品,在不斷的辨別、思考過程中,整合文言文各個層次的信息,從而在思維中構建完整的信息圖景。高中語文教材中的文言文體裁豐富,具有極高的思辨性教學價值,在文言文教學過程中進行思辨思維能力的培養是基于新課標要求的積極探索,同時也是文言文教學的新視角。思辨性閱讀教學區別于傳統的閱讀教學模式,強調學生思維過程的反思性,要保證思辨性閱讀教學的效果能充分體現出來,需要教師積極探索文言文思辨性閱讀教學的高效實踐路徑。
一、思辨性閱讀教學的內涵辨析
“思辨”在我國文化體系中可追溯至《中庸·二十》:“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其中“慎思之,明辨之”強調的就是學習中的“思辨”過程,“慎思”強調要展開全面思考,“明辨”強調的是清晰地辨別是非。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思辨”是“思考,辨析”的意思。在西方,“思辨”最早是“觀看,看”的意思,隨后發展為哲學中的思維方式,黑格爾是思辨哲學的代表人物,他強調要用邏輯思維的形式推理世界法則,并在自我本體化、邏輯化的過程中培養個體的思辨思想,屬于純粹的理性思維模式。
基于思辨的內涵理解“思辨性閱讀教學”,思辨性閱讀教學區別于傳統的解釋性閱讀教學,是引導學生在批判性思維模式下閱讀的教學模式,強調閱讀教學過程中的思維含量,突出思維過程的反思性。思辨性閱讀教學與一般閱讀教學存在一定關聯,同時又具有一定差異,具體而言,一般閱讀教學是思辨性閱讀教學的基礎,而思辨性閱讀教學是一般閱讀教學的升級,兩者的差異如下表所示(見表1)。

表1
綜上所述,思辨性閱讀教學可以理解為一種以學生深層次閱讀能力與思維能力培養為目標的教學模式,教師以培養學生主體思維意識為目的,在課堂上組織多樣化的教學活動,鼓勵學生對文本的批判、反思、質疑、論辯等,從而實現對文本的理性解讀。
二、高中文言文思辨性閱讀教學的實施路徑
1.因文而異:巧于因借析語境
高中教材中的文言文涉及多種不同類型的文章,表達了不同的情感和觀點,由于寫作的目的和情境不同,文本呈現出的內容、邏輯也不盡相同。在思辨性閱讀教學中,基于不同文章的不同特征,要從寫作歷史背景以及文化特征著手去分析語境,再分析文本的語言特征及意義的表達,結合具體的語境理解作者為什么這么寫。
以《鴻門宴》的思辨性閱讀教學為例。在對文章基本內容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分析史傳類文章寫作的特征,以“史傳”的視角來解讀文章。首先了解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的寫作態度,其次強調史傳寫作“秉筆直書,書法不隱”的原則,再介紹史傳寫作“直敘其事”的寫作方法,讓學生了解史傳文學與普通文學的主要差異——客觀真實、嚴遵史實。在此基礎上,再來理解《鴻門宴》,司馬遷并未“勝者為王”地一味歌頌劉邦,而是將其項莊舞劍時被刺的危機、伺機落荒而逃的狼狽等都展現了出來,這種寫法是符合史傳寫作原則的。在教學中要從司馬遷當時的寫作環境和史傳寫作原則出發,不能脫離歷史背景將其僅當作文學作品進行鑒賞。又如《答司馬諫議書》的思辨性閱讀教學。與《鴻門宴》的文本類型不同,《答司馬諫議書》作為一篇“駁論文”,王安石作此書的主要目的是針對司馬光的欲加之罪展開逐條反駁,在寫作中,王安石需要在做到有理有據地進行反駁的同時強調自己變法的決心,因此《答司馬諫議書》的寫作具有非常強的目的性。在初步理解文章內容的基礎上,理性分析王安石的寫作目的,再基于寫作目的去梳理王安石辯論的邏輯性,能加深學生對文章寫作邏輯和辯論邏輯的理解,也能讓學生養成“具體文章具體思考”的良好閱讀習慣。
不同的文言文由于寫作目的、寫作原則、歷史文化等寫作語境的不同,最終呈現出的寫作邏輯也存在一定差異,因此,在教學的過程中,要因文而異地引導學生賞析不同文本的寫作思想和寫作模式,將文章放在具體的語境中讓學生巧于因借地思考,可以將文章放在“歷史情境”中,體現出文言文歷史性與文學性兼具的特征,培養學生的思辨性思維。
2.順勢而為:尋根究底解文情
文言文是我國千百年來歷史文化的沉淀,目前我們對文言文的理解也是后人在闡釋的過程中形成的結論,但結論并非定論,思辨性閱讀教學鼓勵學生的合理質疑。在教學的過程中,可能學生已經接觸到了各種解讀與評論,這些都會影響學生對文章的主動探索與理性思考,因此可以引導學生從了解到的“信息”入手,不必刻意去質疑,而是“順勢而為”,從現有的觀點和思想出發,尋根究底地展開探索,避免在受其他評論影響的情況下“結論先行”,引導學生在論證過程中“質疑”既有認知。
文言文中有不少典型的標簽化人物形象,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這些人物在人們心中已經形成了固有的形象,在教學中要引導學生突破思維定勢的束縛,尋根究底,客觀全面地對歷史人物做出評價。以《燭之武退秦師》的思辨性閱讀教學為例。燭之武在歷史上被貼上了“愛國者”的標簽,教師要引導學生保持審慎態度,通過大膽質疑、小心分析來“驗證”這一結論。可以提出問題:“如果簡單地將燭之武的形象歸結為‘愛國者’是否合理?”引導學生基于“請見”“請從”“老而無能”等詞來窺視作者并未描述的燭之武的內心,進而得出結論:如果簡單地將燭之武看作一個“愛國者”并不全面,也不深刻。質疑和再思考并非全盤推翻原有結論,而是在現有結論的基礎上展開合理論證與細節分析,從文字背后挖掘出更全面的人物形象特征。在這樣的教學過程中,學生透過文字看到的就不僅僅是“愛國者”燭之武這樣的標簽化人物,而是能深入到人物內心,結合人物所處的復雜環境感受其內心矛盾,理解他為國出使的偉大與決心。學生對人物形象進行重構的過程其實也是對文章進行全面分析的過程,教師還要引導學生順著“燭之武退秦師”這件事了解與其相關的歷史,討論燭之武這一人物的“豐滿血肉”,探索其個人言行的合理性。
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幫助學生學習的重要輔助,同時也會成為阻礙學生自主思考的“攔路虎”,因此,教師要引導學生學會“利用”現有結論,以其為“跳板”,順其思路進行深入思考與論證,在此過程中完成自主探索,以客觀、全面、審慎的思考態度下結論。
3.縱橫交融:統整歸一釋文思
對文言經典展開思辨性閱讀教學,不僅要關注其形式和效果,關注其思想與目的,同時還要具有全局意識,站在一定高度對文本進行思考與評價,推敲其寫作邏輯,從文字的具體表達邏輯出發,引導學生主動思辨,對文本進行統整思考,以實現對文章邏輯思路和思想觀點的“全局思考”。讓學生站在全局的高度去判斷、去評價、去發現,相對于單純學習文學知識而言,學生思維層面的提升更具價值。
以《六國論》的思辨性閱讀教學為例。在完成基礎教學之后,對文章的結構、提及的信息以及語言材料等展開全面的統整歸一,在理順邏輯的過程中重構其內部關系,以體現文章的內涵與思想。蘇洵對“六國滅”的論證從 “賂秦”和“不賂秦”兩方面展開分段闡述,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可引導學生對每一段的主題句、論點、論據等進行分析與統整,構建信息鏈條。在對每段內容整理的基礎上,形成全文的信息統整,比如將文中與“賂秦必滅亡”相似的觀點進行整合,分析作者是怎樣在不同段落、不同分論點中統整地論證這一觀點的。從全文的結構層面分析可知,作者開篇便提出了“賂秦”的議題,在此基礎上將六國分為“賂秦”與“不賂秦”兩種,展開對比論證,在這種寫作模式下,“賂秦”與“不賂秦”兩者之間存在的復雜的內在關聯便清晰地突顯出來。在此基礎上,分析作者是怎樣通過正論、駁論、假設論證來論證自己的觀點的。通過對全文內容的統整,學生能以全局的視角構建清晰的文章思維鏈條,深入理解作者的觀點,捋順作者的推理過程。
統整性的全局思維是學生全面思考問題、理性分析事件的重要基礎,同時也是學生思辨性思維形成的重要元素,思辨性閱讀教學除了關注細節、挖掘作者的觀點和心理,更應統整全局,清晰再現作者的推理邏輯,并從中有所啟發,這對學生的日常閱讀與寫作能起到良好的引導作用。
三、結論
經典文言文的思辨性閱讀教學或推敲詞句、或推理邏輯、或對觀點進行審慎辨析,可實現對學生分析、綜合、推理、比較等思維的鍛煉,強調學生的理性質疑、思維調控等思維過程,實現對學生思考習慣的培養,這一方面實現了有效落實新課標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滿足了高中生思辨思維發展的客觀需求。因此,在課堂上針對文言文展開思辨性閱讀教學,強調思維的過程,強調因文而異、情景交融,是培養學生思辨能力的應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