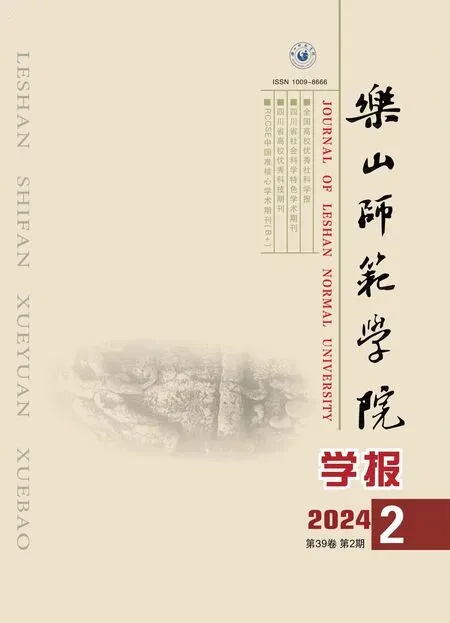蘇軾案例、判例中的法理探討
彭林泉
(眉山市人民檢察院,四川 眉山 620000)
林語堂先生在《蘇東坡傳》一書中寫道:蘇東坡是“心腸慈悲的法官”。這句話經常被引用,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其實,作為法官,蘇東坡既有仁慈的一面,也有嚴肅、嚴格執(zhí)法和能動司法,甚至法外用刑、刺配的一面,以追求實質的正義和維護秩序,由此構成了蘇東坡的側面。案例、判例是實踐中的法律和法理,也是司法經驗的總結與司法智慧的體現。蘇軾(蘇東坡)是一個在詩詞賦散文、書法繪畫等文學藝術領域中的全才,也是一個法學家。在他長期在地方(多地)任職期間,辦理了一些司法案件,留下了一些判詞,體現了不一樣的法理,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頁。當我們把他的法律與文學、政治結合起來思考、研究時,猶如進入一個多彩的法律世界。本文以蘇軾所辦案件和判詞為基礎,結合相關的資料,從以下四個方面對蘇軾的案例、判例中的法理進行詳細分析,以展現蘇軾法治的側面。
一、蘇軾刑事案例中的法理
“法理”一詞在宋代之前已經多次出現。據陳景良教授考證,“法理”一詞在宋代的判詞及宋人的案例編撰中也不斷地出現。它有多重含義:有時指法律條文,有時指天理、國法,有時指法律的價值或法意。該詞的內涵與現代的“‘法理’仍有一定的差異,但其運用的普遍性及其包含的價值意蘊足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宋代法學的成熟”[1]144。雖然蘇軾當時未使用“法理”一詞,但在所辦案件和判例中體現了“法理”,彰顯了應對案例的知識與能力,折射出司法、法理智慧。
蘇軾所辦的刑事案例包括密州的盜竊和兵卒斗殺案、徐州的盜賊案,以及穎州的尹遇等人掠劫案和孫貴、張全等人貪污、盜竊案。
如關于尹遇等人掠劫案,蘇轍所作的《墓志銘》和《宋史·蘇軾傳》都有簡要的敘述,而蘇軾兩次較為詳細地敘述了本案的事實和結果,特別是他引用法條、考之法意和“說話算數”,在李直方設法捕獲尹遇等人后,奏請朝廷酬獎李直方,令人難忘。
元祐七年(1092)正月,知潁州的蘇軾在《乞將合轉一官與李直方酬獎狀》[2]3451中敘述了尹遇的犯罪事實,有的還有細節(jié),歸納起來,主要有三:一是與陳欽等人結伙殺掠搶劫,時常與捕盜官兵相對抗,漏網逃脫。二是不思悔改,繼續(xù)糾集陳欽之弟陳興、鄭饒、李松等數人,搶劫民戶,導致鄉(xiāng)村人害怕,即使被劫殺,也不敢申報,甚至被殺者的父母妻子也不敢聲張舉哀。百姓蔡貴、莫、董安三人,只因偶然提到尹遇等,就立即被殺,其中董安還被尖刀割斷腳筋,其余割取頭發(fā),以及被殺傷者不可勝數。三是尹遇等人在一起商量,準備與壽州界內的強賊呼應,居民憂心忡忡。壽州界內的強賊搶劫了魏家、謝解元、施助教等家,并在市鎮(zhèn)上搶劫。嚴格地講,主要是有二筆即前二筆犯罪事實,后一筆盡管造成居民的憂懼和無行為和結果。可見,有的比較詳細,有的比較概括,論其性質是殺人搶劫案,蔡貴、莫、董安三人被殺,屬于命案。
對此,蘇軾及時采取了措施。他考慮到事情的緊迫,立即派遣官員監(jiān)率捕盜官兵,限期捕獲。他派遣限期捕獲的是李直方。他敘述了李直方的情況、為人和抓獲尹遇等人的經過和結果。李直方是汝陰縣尉,進士及第,母親已九十六歲,母子二人相依為命,平素就很有才干,自己拿出錢財,募人作為耳目,查出了賊人老窩所在。其中尹遇住在壽州霍丘縣成家步鎮(zhèn),比陳興等人的窩藏地點還要遠二百里路,是眾賊之中最為狡猾的,難以捕獲。李直方安排手下的人去捕獲陳興等人,自己親領五名弓手,直接去成家步捉殺尹遇。臨出發(fā)前,與母親泣別,往返五百多里,累死一匹馬。李直方步行一百多里,裝作一名販牛的小販,到達目的地后,眾人都畏懼不前,只有弓手節(jié)級程玉等二人與李直方持槍大呼,破門而入。尹遇驚起,抓起一張弓準務射箭,李直方跨前一步,親手將其刺倒,眾弓手這時都擁了進來,才把尹遇擒獲。在其他人捕獲陳興等人九天后,捕獲尹遇。遠近之人對此無不拍手稱快。
之后,蘇軾為李直方能捕獲強惡賊奏請依照《編敕》第三等酬賞。《編敕》節(jié)文:“諸官員躬親帥眾獲盜一半以上,能分遣人于三十日內獲余黨者,通計人數,同躬親法。”他引用了這一摘要,結合李直方在捕獲尹遇的表現,作了闡述。這個法條有兩層含義:官員親自率領眾人捕獲盜賊的數目或比例,以及分遣人員捕獲余黨的人數及時限。李直方符合第二個條件,不符合第一條件。本案中共抓獲四人,李直方親自率領眾人捕獲一人,分派人員捕獲三人,從數目的比例來看,不到獲盜一半以上。但蘇軾認為李直方忠義正直,把除掉惡賊放在第一位,無暇計較恩賞問題,所以,親自長途跋涉,專捕尹遇一人,以致所派的弓手,卻先將陳興等三人抓獲,遂與上述規(guī)定不相符合,與獎賞的要求稍有出入。但“考之法意”,顯然是這個說法不太完善。請求朝廷詳加斟酌,因為李直方先公后私,致使先后捕獲的數目與先后與敕令的規(guī)定不盡吻合。想請求比照上述規(guī)定,總算一下人數,允許按照親自抓獲的獎勵辦法予以獎賞,為第三等獎。希望圣主考慮到,尹遇等人如不及時捕獲,必然要聚集起來為害,而李直方本是一個讀書人,卻能奮不顧身,忠義精神可嘉,特下達指示。
蘇軾又考慮到朝廷會吝惜這個恩賞,唯恐今后妄加援引。按規(guī)定蘇軾應該轉升為朝散郎,但他情愿自請轉,將這個恩賞賞給直方,按規(guī)定獎勵。在蘇軾看來,因李直方的母親已九十多歲,只有一子,因為他的督促,才泣別而行。如果萬一被賊人所害,使其老母無所依靠,他豈不愧見僚吏?因此將應轉的官職給直方作為獎賞,不但稍可以酬報其辛勞,也使他今后還能夠使喚人,不是盡說空話。對于蘇軾也是莫大的幸事,而且免得后人援例,朝廷也容易施行。
但這一請求未被采納。后來朝廷下達意旨,只給李直方免試。這個恩賞輕微,與李直方的成效顯然不相稱。蘇軾的心里裝著此事。過了幾個月,已經升為兵部尚書的蘇軾,于元祐七年十一月初四日又上書,在《再論李直方捕賊功效乞別與推恩札子》一文中,再次陳述李直方的功勞,認為因為選官免試,恩賞很是輕微,這中間以毫發(fā)微勞得到者有很多,恐怕不是用來激勵為國捐軀除患之士。懇請圣上特賜審查他的先前奏議,重新給予恩賞,仍允許他不再使用轉朝散郎一官,而將此官給李直方,免得后人妄加援引。
這揭示了蘇軾對法條的理解和運用,特別是考究或推敲法意,在個案中的具體運用。從本案來看,也折射出原規(guī)定的不完善。對主犯捕獲的價值遠勝于從犯,李直方也可以按照規(guī)定去辦,獲得相應的獎勵,但他沒有,而是派遣手下的人去捕獲從犯,自己親自率領眾人去捕獲主犯,奮不顧身,親手持刀,刺倒尹遇,將其抓獲。在蘇軾的筆下,李直方是一個地方官員,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也是一個忠義正直、有勇有謀和先公后私的人。用蘇軾的話來說,李直方“忠義激發(fā),以除惡為先務,而不暇計較恩賞”,“直方儒者,能捐軀奮命,忠義可嘉”。在他看來,雖然李直方進士及第,母子二人相須為命,而能以忠義相激勵,親手擊刺盜賊,為一方百姓除害,這與一般的捕盜官吏,偶然抓獲十幾個饑寒之民充作劫賊的行為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他們還能得到獎賞,而李直方如果不加以特別的獎勵,則不能鼓舞忠義膽決有方略之臣。更難能可貴的是,李直方先公后私、身行,能夠“拿出家財,緝知余黨所在,分遣弓手,前后捕獲,功效顯著”。蘇軾提出恩賞李直方,可謂體現了真正的法意。對這件刑事案件或殺人搶劫案,是蘇軾組織查辦的,成功捕獲后,他奏請獎勵有功之臣,本是職責范圍的事,為此闡述理由,列舉法律依據,希望比照執(zhí)行。在文中,蘇軾進行對比,一方面是列出各賊兇惡的事實,另一方面敘述李直方奮不顧身的情形。蘇軾說,有城鄉(xiāng)老百姓617 人到他這里申訴,訴說各賊兇惡,為害多年,人們敢怒不敢言,如果不依法嚴加懲處,萬一免死而流放,就會逃回后聚嘯山林,為害更加嚴重。蘇軾由此知道各賊狡猾兇狠,眾人畏懼。結合李直方的上述行為,可以發(fā)現,他指出此案危害性的目的在于闡述為什么要恩賞李直方的原因。
而蘇軾的奏請彰顯其“說話算數”,只要自己認定的事,會堅持辦,直到辦成。這體現了蘇軾不貪功、不推諉的品格,與他在知徐州時招沂州能人程棐前來緝盜,后盡力兌現自己的承諾是一脈相承的。
二、蘇軾民商事案例、判例中的法理
據(宋)何薳的《春渚紀聞·卷六》東坡事實記載:
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制扇為業(yè),適父死,而又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制不售,非固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制扇來,吾當為汝發(fā)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夫絹二十扇,就判筆作行書草圣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即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逾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后空而不得者,空懊恨不勝而去。遂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3]173-174
這是蘇軾在知杭州時處理的一件制扇商人負債案件。我國學者認為:“蘇軾的處理頗為精彩,集中體現了擅長書畫的蘇軾精于理政的鮮明特點,流傳甚廣。”[4]206本案沒有原告與被告的具體情況,僅有簡單的案件事實和蘇軾的詢問,以及最后的處理。
本案的基本事實是杭州有個制扇的商人拖欠綢緞款不還,數額達到兩萬錢。案情并不復雜,且事出有因,被告陳述了沒有還款的原因:他是一個制扇賣扇的商人,近日其父也去世了,但是今春陰雨連綿,天氣寒冷,導致扇子滯銷,所以無力償還。承認他確實欠錢了,但不是故意不還的。換言之,遇到父死和陰雨兩大特殊因素。這方面的證據有被告的控告、被告的陳述和未賣出的扇子,等等。蘇軾傳喚被告后通過對其詢問,了解到他為何欠錢不還的真相。
宋代對于負債不如期歸還有較為詳細的規(guī)定,據《宋刑統(tǒng)》卷二十六《雜律》“公私負債”條:
諸負債,違契不償,一疋以上,違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疋加二等,百疋加三等。各令備償。
如果欠賬長達百天,則要徒一年。當然,債主一也不能因為債務人欠債務而自己強行私力救濟,如果強拿債務人的財物而不告官,則要以坐贓論罪。
根據熙寧年間實行青苗法時所記錄的物價,當時一匹絹對應的價錢大概在一千二百錢到一千三百錢左右。[5]6054-6055參照這個物價,這個案子中被告所欠的錢數,在十五匹絹左右。
那么,債務人拖欠的時間有多長?文中沒有說,有論者認為,既然債主已經告上法庭,債務人又有“連雨天”的陳情,想必拖欠的時間也不會短于二十日,至少達到了笞二十的最低起刑標準。[6]232這是合理的推測,沒有證據支持。
如果嚴格依照法律判決,那么作為被告的制扇商人將面臨責打,或最少笞二十的刑罰。這也是最直接、簡便的處理方式。可是蘇軾沒有這樣做,因為他意識到,依法將被告責打一頓,并不能妥善地解決糾紛。蘇軾可以采取規(guī)勸雙方再進行協商的方式,從而息訴。但延期償還,會使債權人蒙受一定的利益損失,也會增加債務得不到償還的風險,如絹扇會因連日陰雨、氣候潮濕而發(fā)霉。[6]232也可以當庭判決被告還錢,或根據情勢變更,給被告一個還錢的寬限期,就算結案盡責了。但蘇軾沒有這樣做。在權衡后,他作了選擇,利用自己的書畫才能,讓被告將自己積壓的團扇取來,在二十柄團扇上題寫了行書、草書,或畫了枯木竹石,很快銷售一空,使小商人賣了扇子履行了債務,使債主拿到了錢實現了債權,維護了法律的尊嚴,體現了他的法律觀“以法活人”。
從此案中可以看出,當時杭州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好訟”和利益多元化,以及債權人的維權表現,這些是宋代社會私有制深入發(fā)展和利益多元化在司法上的必然反映,所彰顯的是宋代社會“好訟”之風的形成及宋代司法傳統(tǒng)由倫理型向知識型的轉變。在這一案例中,體現了執(zhí)法者的積極能動性,“盡量在法令與人的積極能動性之間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從而使法令的施行更加靈活、合理與人性化。”[7]54-61而此案的處理,是在法令有明確規(guī)定的情況下,面對兩難的問題,通過執(zhí)法者的積極能動性,作了法律藝術化的處理,即妥善化解了糾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蘇軾利用了其書畫的才能,或者說超逸絕倫的藝術才情,這是其他法官難以做到的。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表面上看,蘇軾似乎是在“以情代法”,實際上是在融天理、國法與人情于一體,守法度、維護國法之權威,情系百姓,在嚴肅執(zhí)法中關心百姓疾苦,幫助被告還清債務,保護原告的利益。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司法為民,傳遞司法溫度。蘇軾的處理是精彩的,留下了一個故事和一頁法文化,難怪杭州人民念念不忘“蘇公判牘”。
三、蘇軾行政案例中的法理
這類案例包括三件案件:杭州顏章、顏益涉稅案,貢生吳味道逃稅案和顏幾科考舞弊案。
據【宋】何薳的《春渚紀聞》記載:
東坡先生出帥錢塘,初視事,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xiāng)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銜,封呈京師蘇侍郎宅。公訊其卷內何物,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忝冒鄉(xiāng)貢,鄉(xiāng)人集錢為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紗,得三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竊計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惟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遂假先生名銜,緘封而來;不知先生臨鎮(zhèn)此郡,罪實難逃。”公熟視,笑呼掌牋吏去其舊封,換題新銜,附至京東竹竿巷;并手寄子由書一紙,付之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明年味道及第來謝,公甚喜,為延款數日而去。[3]173
蘇侍郎指蘇轍,因任門下侍郎,故稱。根據宋人筆記記載,蘇軾在此期間還辦理了貢生吳味道逃稅案,有的稱之為欺詐、偷稅案[8]295-296。因為冒名的目的在于逃稅,過去也經常使用偷稅罪這一罪名,但后來法律作了修改,如現行的刑法第201 條規(guī)定了逃稅罪及其處罰,以及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及其例外的規(guī)定,罪名就是逃稅罪。所以,將吳味道的行為定性為逃稅是準確的,在這里使用逃稅案。
本案的事實是:南劍州(今福建南平)鄉(xiāng)貢舉人吳味道,進京參加來年的禮部進士考試,因家中貧困,沒有川資路費,臨行前,他的鄉(xiāng)鄰親友為他籌來一百千錢,購買了兩百匹本地名產建陽紗,帶到京城變賣作盤纏。可是從南劍州帶到汴京,沿途抽稅,等到了京師恐怕一半也剩不下了,于是冒用蘇軾的名義逃稅。他久聞蘇軾兄弟的大名,也了解官場風氣。二蘇素有樂于獎掖后士、提攜寒士之名,他的這點小花招即使敗露,想必他們也不會見怪。不知蘇軾已任職杭州,自知罪實難逃。
本案的處理結果出人意料。蘇軾聽了他的陳述,同情這位窮書生,笑著叫人揭去其包裹上的舊封,親筆寫道:蘇某封寄至京東竹竿巷蘇學士。隨后又給蘇轍寫了一封短信,交給吳味道,說:“先輩這回你就是帶到皇帝面前也沒有什么關系。”第二年,吳味道中第后前來道謝,蘇軾十分高興,還邀請他到家里小住了幾天。
這似乎有違法處理之嫌。有論者認為,蘇軾此舉其實是對違反關稅政策的吳味道的包庇,并不符合其朝廷官員的身份立場。而對于不合理的經濟政策,蘇氏兄弟輾轉地方任職期間,往往作出“因法以便民”甚至“陽奉陰違”之舉,或者予以光明正大地撤銷,或者以正當程序拖延。[6]220但在這個案件的背后,卻透露出蘇軾的判案體現了仁政司法,用今天的話來說,是體現了人本主義的法律觀,體現了司法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展現了宋代士大夫的人文關懷,關心民間疾苦和同情百姓遭遇的情懷。結合前述制扇商人債務案件的斷案,因此,不難理解他被林語堂先生稱為心腸慈悲的法官。
宋人周輝在《清波別志》中對此也有相關的記載,給予積極的評價,“倘遇俗吏苛刻,必斷治偽冒,沒入其物,還有此氣象乎”。也有的認為:“他總是在極為慎重地處理民間訴訟,盡可能做到國法與人情兩相兼顧。”[8]298在司法實踐中,蘇軾亦經常屈國法而伸人情,此處所言的人情概指某種“事實”。它可表示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現實情況,也可表示行為舉止合乎相應的倫常要求。[4]206在筆者看來,蘇軾對法律的理解不是紙上談兵,也不是就案辦案,機械司法,而是考量法、人情和理,依法妥當地解決糾紛或案例。這體現了他在《刑賞忠厚之至論》中闡明的一生所遵循的仁政思想,以及民本思想。他說,民者國之本也;他強調義,認為興利聚財應符合義,否則會動搖國本。
我國學者認為,蘇軾對法律仍抱有一定的實用主義心態(tài),斷之以法并非解決問題的終極目的,用蘇軾自己的話說:“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4]209這不無道理。在筆者看來,蘇軾并不是一味地寬,還有嚴的一面。這使得“蘇軾在法律表達與司法實踐中存在一定的張力”[4]208。如在知杭州時,他查處了杭州顏章、顏益涉稅案。
元祐四年(1089)八月,蘇軾在《奏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一文中說,在查明案件事實后,他判處顏益、顏章兄弟二人刺配本州牢城。并闡述了理由,即顏益、顏章“欲以眾多之勢,脅制官吏,必欲今后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大革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2]3250。這里的“情理”,如何理解?從情理上講,他們是大蛀蟲,情節(jié)嚴重,這不僅涉及交納者、攬納人與夏稅官吏、州衙門的關系,還涉及地方與朝廷的關系。他在判詞中指出:“顏章、顏益家傳兇狡,氣蓋鄉(xiāng)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脅制監(jiān)官。蠹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2]3250這是蘇軾文集或所辦案件中少見的判詞,盡管是片斷,不完整,但已經揭示了其給革除稅收之積弊帶來嚴重損害,或者說危害到稅收改革的進行,蘇軾認為難以用常法判決,一個“獨”字顯現出個性和態(tài)度,對法律秩序的維護。有論者認為,從杭州顏氏案的處理中可知,蘇軾具有較高的法律自覺,在其法外刺配之后,上書朝廷待罪。從側面證明,蘇軾認為在常規(guī)情況下應斷之以法,或“情法兩平”,也力圖做到[4]202-203,但在部分“事關利害”的情況下,他還是會根據具體事實而進行判斷、處理。所以,不能簡單地以“知法違法”來理解蘇軾的判決。
在其法外刺配顏氏兄弟后,蘇軾上書朝廷待罪。蘇軾的作法被御史論為不遵守法律,最后,朝廷還是依法放免了顏氏,但也沒有追究蘇軾。他提出“所有臣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亦乞重行朝典”的建議,未被采納。
我國著名法史專家徐道鄰先生認為,《奏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這一文件,不但充分地透露出東坡的敢作敢為,同時也證明了他對司法權的運用,有熟練的手腕。顏氏兄弟,雖然是犯了稅法罰則,而由司理院依法予以行政處分。但是東坡卻因為他們鼓勵暴動、威脅地方的安寧,就“便宜從事”的“法外”予以剌配。同時認為自己的行為,超出一般地方官的權限,接著就向朝廷認錯請罪。但是這確是一時權宜之計,朝廷哪有不免罪之理。這樣爽快利落的行為,不是自認為對于法律的制度和精神,有充分認識的人,誰敢去作?他在《杭州謝上表》中,有“法吏綱密,蓋出于近年守臣權輕,無甚于今日”兩句話。就是在今天,凡是有經驗和肯負責地方長官,讀了也不免同聲一嘆也。[9]403在筆者看來,蘇軾之所以這樣做,在于顏氏兄弟招供在交納稅收之前,確實有所預謀;在交稅過程中,顏氏兄弟交納的絹多被揀退,于是挑起事端,沖擊州政府。這是考慮到稅收改革特別是本案對社會秩序的危害而處理的,是例外。將顏章、顏益二人“法外剌配”,似乎是不嚴格執(zhí)法,其實,這秉持他的政治哲學和對法律的熟悉,以及再次的能動執(zhí)法。作為北宋士大夫之一,蘇軾具有很高的法律素養(yǎng)、法律經歷和司法經驗,可謂“文學法理,咸精其能”。
四、蘇軾涉外案例中的法理
這類案件主要有徐戩非法交易案。關于此案,我國學者在分析杭州高麗僧案時,從案件背景、案件起因、案件審理與立法建議等四個方面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4]203-206,實際上把它作為杭州高麗僧案的一部分,或者前案。換言之,除簡要敘述對徐戩案的審理和處理外,重點是對杭州高麗僧案的審理與建議。客觀地講,兩者(徐戩案與我國學者筆下的杭州高麗僧案)存在關聯,不過,在筆者看來,真正稱得上司法案件的是此案中的徐戩案。因此,筆者將著重分析徐戩非法交易案及其中的法理。
是時,蘇軾知杭州,多次地以奏狀的形式向朝廷上報此案,從中可見案情、處理經過特別是依法處理的理由。
元祐四年(1089)十一月三日,蘇軾在《論高麗進奉狀》一文中說:
今月三日,準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
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甚眾。訪聞徐戩,先受高麗錢物,于杭州雕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于海舶載去交納,卻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奸細,何所不至。兼今來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戩本謀。臣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即當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奸民猾商。[2]3260-3261
在這里,蘇軾敘述了徐戩的犯罪事實和將其上枷后押送、調查的情況。徐戩是福建泉州人,是福建狡詐的商人,專門擅長勾結高麗人,以便從中牟取暴利。主要是先接高麗人的錢物,然后在杭州刊印注釋的《華嚴經》,費用浩大,印板既成,公然裝入海船前去交割,卻受其國厚重的賞賜。這次還招來高麗僧人,即擅自在海船內運載高麗僧統(tǒng)義天手下的侍者僧壽介等人。“今月三日”,蘇軾已命令秀州差人把徐戩押來,已查實其犯罪事實,請求法外重行,即嚴加懲處,以戒福建全路的奸民猾商的行為。
元祐四年(1089)十二月三日,蘇軾在《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2]3278一文中,又提及此案。徐戩是杭州僧人靜源的門徒,在靜源故去后,想要繼續(xù)與高麗人交易牟利,便帶領壽介等人來杭州祭奠。蘇軾已經按照朝廷旨意,允許壽介等人到來杭州,致祭亡僧凈源。完畢之后,派人用船將他們送到明州,搭載便船回國。可見,朝廷同意了蘇軾之前的建議。對于壽介等人要求祭奠,蘇軾已命令本州有關部門送到承天寺安頓,選派職員二人,士兵十人,嚴加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又選派道行高尚深暗經典的僧人與他們討論,定量供給,不讓其走失外,已將事情經過及處置的辦法,奏請朝廷完畢。只許致奠,其余尋師學法出入游覽之類,一概不許。并限日送至明州,令其搭乘便船只歸國。這是蘇軾所采取的處置措施,帶有限制性。
元祐五年(1090)八月十五日,蘇軾在《乞禁商旅過外國狀》一文中,對此案又說:
檢會杭州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泉州百姓徐戩公案,為徐戩不合專擅為高麗國雕造經板二千九百馀片,公然載往彼國,卻受酬答銀三千兩,公私并不知覺,因此構合密熟,遂專擅受載彼國僧壽介前來,以祭奠亡僧凈源為名,欲獻金塔,及欲住此尋師學法。顯是徐戩不畏公法,冒求厚利,以致招來本僧搔擾州郡。況高麗臣屬契丹,情偽難測,其徐戩公然交通,略無畏忌,乞法外重行,以警閩、浙之民,杜絕奸細。奉圣旨,徐戩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2]3329-3330
上兩狀月日分別為“十一月三日”“十一月十三日”,這里的“十一月二十三日”可能有誤,疑為“十一月三、十三日”。在這里,蘇軾本人將此案稱為徐戩公案,并對徐戩案的事實作了進一步的敘述。載明徐戩不應該擅自為高麗國雕造經板二千九百馀片,并公然運到高麗,接受報酬為白銀三千兩,再次提出請求朝廷對其“法外重刑”,因為增加了朝廷招待賞賜的費用和地方接待的費用。同時,高麗的使者所到之處,到處繪制地圖、購買書籍,這與契丹有關,甚至在背后操縱。有識之士,深以為憂。徐戩緊密勾結,又擅自運載高麗僧人壽介前來,以祭奠亡僧凈源為名,欲獻金塔,以致招來該僧搔擾我地方,這是違反國法,貪圖厚利的,奉圣旨將徐戩流放到千里以外的州、軍管制。這也是蘇軾提出的建議,被采納。我國學者認為,在對徐戩的處理中,蘇軾再次提到了“法外重刑”,亦可見在處理情理與國法的關系時,蘇軾確有屈國法而伸人情的情形。此處的“情”則是指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國家利益的損失和對地方統(tǒng)治秩序的破壞等實際情況。[4]206這不無道理。蘇軾在過去《論高麗進奉狀》《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三首》《乞禁商旅過外國狀》的基礎上再次提及涉外關系,與高麗、契凡的關系。因此,上述商人徐戩、王應升、李球之流,得售其奸,現在必須更改。請求三省與樞密院商量后裁定,一律按照慶歷和嘉祐年間的《編敕》執(zhí)行。
在此奏狀中,蘇軾提及的王應升、李球,實為在徐戩非法交易案發(fā)生之后的王應升等人的案件和李球非法交易案,認為李球案與徐戩公案在性質上是相同的。他說,高麗使者李資義等269 人先后到達明州,仍然是客人李球于去年(元祐四年)六月內,拿到杭州市舶司公司通行證前往高麗國做生意,因此替高麗國先帶到密封的書信一封,以及捎帶松子四十布袋前來。本司審定,顯然李球因往高麗與之相熟后勾結在一起,替他們作向導,以求厚利,與去年所奏徐戩的事情是一個性質。也就是與高麗非法交易,以謀求厚利。
在以上奏狀中,涉及徐戩非法交易案的處理,涉及海外貿易和國家安全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蘇軾對“聯(高)麗抗遼”策略的反對。他反對宋神宗推行的高麗政策,主要有以下具體理由:財政上耗資巨大、軍事上泄漏機密、外交上麗、遼“陰相計較”。此外,高麗已成契丹的藩國,其通好宋朝,恐為契丹向宋刺探情報之嫌。[10]317-318換言之,蘇軾這樣做,是從政治、經濟、軍事利害進行考慮,注重國家安全,依法處理相關事務,是事出有因。宋神宗曾想聯絡高麗對付契(遼),所以對高麗持招徠的態(tài)度。蘇軾認為這是不現實的,故主張冷卻此種國事來往。不過,對于一般正常交往和文化交流,蘇軾也不反對。
在徐戩非法交易案的審理中,事關兩國之間的交往,蘇軾并沒有擅自決斷,而是將相關情況與處理意見上奏朝廷,顯現蘇軾對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十分敏感,而且之后還他根據慶歷、嘉祐以來有關客旅通商的編敕,就商賈與高麗的頻繁溝通,提出立法建議,足見其對法律的嫻熟。處理徐戩案的方式,更是集中體現了法與情。
對于徐戩,蘇軾將他枷送司理院審判,并上奏朝廷,建議對其進行法外加重處理,程序合法。對處理徐戩擅自與高麗貿易牟利、并策動高麗僧人來華的行為,蘇軾應對得當。一方面,對于壽介等人要求祭奠,蘇軾已采取前述的措施,合乎情理,還派凈慧禪師思義為館伴,以便監(jiān)管探查壽介等人;另一方面,對于壽介等人提出的祝壽朝貢的請求,蘇軾退還書狀,以朝廷管得嚴格,我不能擅自做主為由,提出處理的建議,并奏報朝廷請旨、施行。尤其是在建議由他代表州一級地方政府進行拒絕的同時,蘇軾說,他們所帶來的二所金塔,據壽介等人讓中方陪同人員前來告訴我所說的,恐怕帶回本國,將受重罰。“臣已依元奏詞語判狀,付逐僧執(zhí)歸本國照會,及本州即時差撥人船乘載壽介等,亦將來面蠟燭之類隨官餞送。”[11]3279這種狀況少見而珍貴。對于這起涉外案件,蘇軾根據不同的要求,分別采取相應的措施,并依法提出處理的建議,闡明理由,體現了獨到的法理。可以說,蘇軾融“天理”“國法”與人情為一體,從查處、流放徐戩,達到殺一儆百的效果,到遣返壽介,妥善維護宋與高麗關系,蘇軾均依法處理,并考慮了理與情,處置得當,為人所稱贊。
結合蘇軾的其他案例、判例來看,蘇軾不僅依法打擊盜竊、搶劫、殺人和貪污犯罪,對涉稅并危害社會秩序的涉案人甚至法外剌配,同時關注民生,體現百姓的訴求,重視老百姓的財產權益,尊重百姓的生存尊嚴,追求司法的公平、效率的價值,崇尚儒家的教化作用,體現了其正當性和合理性,也體現了蘇軾的法理,特別是實踐的法理,與哪些律學家相比,具有豐富性、多樣性和獨特性的特點,因此廣為流傳。
蘇軾案例、判例中的法理與北宋社會轉型時期的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密切相關,體現了蘇軾對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看法,如人與法并行,因法以便民、禮法融合等,并付諸實施,以解決當時的社會危機。他是一個來自西南的溫和的變革者,與王安石激進的理想主義不同,與保守的司馬光也不同。
總之,蘇軾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也是一個法學家。蘇軾在地方任上或為官期間,先后辦理過不少案件,留下過一些判例。體現了不一樣的法理,走完從文本中的法、到心中的法、再到行動中的法的過程。不是作為知識形態(tài)的法理,更多的是社會轉型時期實踐性的法理,在中國古代司法史上作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至今仍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