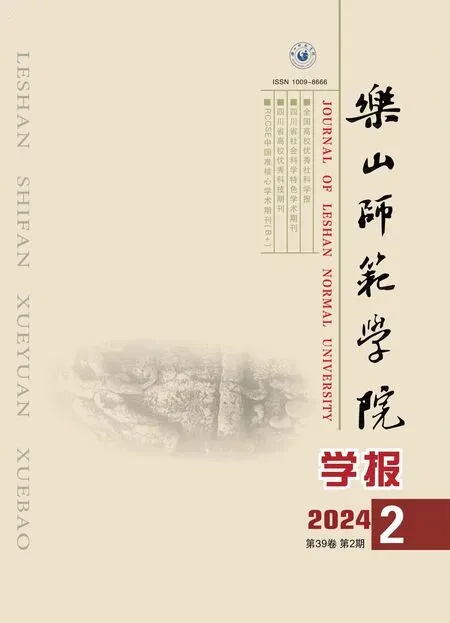移動短視頻社區中的視覺人類學新特征
王玉坤
(貴州民族大學 傳媒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視覺技術的發展尤其是攝影術的發明,開啟了現代視覺人類學研究的大門。20 世紀四五十年代,依托民族志紀錄片(Ethnographic Film)這一媒介載體,能夠讓人們看到讓·魯什(Jean-Pierre)的《夏日記事》[1]。20 世紀70 年代,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徳(Margaret Mead)將電影與人類學相結合并延伸出“Visual Anthropology”的概念,國內大多將其譯為“視覺人類學”或“影視人類學”[2]。學者朱靖江曾著重闡釋了自己對于“Visual”的觀點,他認為應建立以影視人類學、影像人類學與視覺人類學為分支學科三個層次[3];鄧啟耀則傾向于將群體性圖像信息、視覺符號和視覺文化行為納入視覺人類學研究的視野[4]。為了本文論述清晰,特別使用含義較為廣泛的“視覺人類學”概念,不但有觀察層面的“視”,還有心理層面的“覺”。將可視化的短視頻納入統一的視覺空間,認清影像不只是具有“文本人類學”的記錄功能,還擁有“視覺人類學”的可視化和沖擊性。
媒介技術的發展促進了拍攝的平民化,拍攝工具的多元化帶來了影像的極大繁榮,拍攝的主體不再是具有獨特身份的攝影師、記者、人類學家。國內以抖音、快手、嗶哩嗶哩為代表的短視頻社區讓視覺的平民化表達變為可能,新的媒介生態環境也將改變傳統視覺人類學的拍攝工具和手段、田野調查的方式以及研究模式的轉變。學者余點認為,新媒體的發展有利于詮釋和保護世界文化、解決跨文化交流的障礙和帶來影視人類學學科的發展。“新媒體語境下,影視人類學發展機遇與困境共存。”[5]應該借勢新媒體的發展,重新闡釋學科的人文精神,豐富影視人類學的生產和傳播。朱靖江也論述了以快手、抖音為主的短視頻社區所產生的主位影像表達和由此帶來的社區認同和商業變現模式[6]。這些學者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擲于視覺人類學在新媒介環境下的變遷,但總體而言不夠深入和具體,本文繼續聚焦不同于以往傳統人類學視角的移動短視頻社區所引發的新蝴蝶效應,在關注短期大環境引起學科變化的同時,用長遠的眼光來看待學科未來的發展和由此帶來的利害關系。
一、當代媒介技術發展帶來視覺影像轉向
視覺人類學的基礎理念是“文化是可視的”,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理念,使得視覺人類學研究的范圍大大拓展了。王海龍認為,大多數的人類學家荒唐地摒棄了在照相術發明以前對自史前人類開始繪畫以及用圖像記載文明時期所有視覺材料的研究及以此來探討-傳承文明的所有努力及其實踐活動,這是錯誤的。他認為,視覺人類學是用圖形、圖像來闡釋和研究人類文明、文化的學科,是一門全景性的學科,不僅涉及電子媒介時代的影像記錄,還可以包含攝影術發明之前的圖騰、符號、文字、繪畫、雕塑、建筑等諸多能納入人類視覺范圍并與人的生產發展密切關聯的人文藝術[7]。遠古時期的結繩記事反映了先民們記錄生活的美好愿景,結繩的繁瑣性與材料的的易腐性使得就地取材的石刻與陶繪成為新的記錄方式和視覺符號,而文字的誕生則開啟了人類進入文明世界的大門,兩河流域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及中國中原地帶的甲骨文都是將原始符號與契刻結合起來,形成了早期圖文并茂的原始文字。原始先民將自己的所思所想“編碼”留存于可以永久保留的巖石、龜甲、獸骨上,清晰地記錄了人類早期的生活方式與漁獵實踐,現代人類將其“解碼”并發現其中奧義,使得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更具完整性。正是由于文字的靜態性和隱晦性,增添了其解碼的難度和時長。同時,人類的文化認知是一個不斷糾偏發展的過程。“司母戊鼎”因其“司”不符合青銅器銘文規范而更名為“后母戊鼎”,原因是“后”字在古時有“君王”“領袖”的含義,亦可延伸為“王后”“母后”之意[8]。如果說文字人類學的發展與研究需要進行編碼與解碼,而繪畫、雕塑、建筑等具象化的圖形則使得譯碼的難度大大降低或者說能夠以更直觀原始的視覺將思想展現在人類面前。一方面,繪畫誕生的初期是為了記錄客觀對象和對同質物體加以區分,人們看到的內容就是畫面本身的結果,不需要思維的二次運作和加工;隨著時代的發展,繪畫不僅僅是早期的“寫實主義”,視覺作品依托時代大背景和藝術家的個人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擁有自己獨立的主題、思想、風格和靈魂,經歷了一個從原始到現代、從現實到浪漫的演變過程,視覺語言的變化彰顯著人類對于自身所處時代和環境的思考,是人類文化自覺和自省的重要體現。
19 世紀早期攝影術的發明,一般被當作是現代視覺人類學發展的原點。快門的按下大大縮短了繪畫所需記錄的時間,并且以高保真和高還原度再現社會場合和人文風貌。攝影術在19 世紀四十年代傳入中國,那時的中國人將照相機視為異物唯恐避之不及。執掌照相機的人也仿佛有了權力與規訓的話語,看與被看在這樣一種場景中被建構,并且擁有多層次的復雜關系,“跨文化觀察”成為人類學田野調查的一種常態。被譽為中國視覺人類學先驅的紀實攝影家莊學本早年在進行游歷和社會考察時拍攝了大量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影像,兼具藝術和人文價值,為視覺人類學關于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如果說照片的拍攝是一個凝固時光的過程,而攝影機的發明將人類社會的動態性保存在電子存儲介質中,人類文明影像以“比特”的形式活躍在各類電子媒介,完成了靜態的照片到動態影像的視覺轉換,更是成為人類學影像記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和表現方式。早期的人類學影片以羅伯特·弗拉哈迪德《北方的納努克》和M·庫珀和舍德沙克(Coper,Schaedsaek)拍攝的民族紀錄片《草地》為主要代表[9],形塑了人類學影片的基本態勢和民族志紀錄片的風格,20 世紀30 年代,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把拍攝的影像素材用電影的制作手法和呈現方式與人類學研究結合起來,創作了具有電影風格的人類學影片[10]。20 世紀70年代,視覺人類學學科獨立發展。近十年來,伴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媒介傳播手段的多樣化,傳統的膠片攝影、DV、磁帶、錄音機等媒介設備已不足以支撐學科未來發展的需要。智能手機等移動終端的普及和拍攝器材的廉價化讓視頻拍攝的門檻大大降低,而第四代、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更是讓短視頻的廣泛傳播成為可能。其中,拍攝者、被拍攝者、我看人、人看我、我看我、我看人看我都變得復雜而多元,社會中的“他者”身份界限變得模糊不清,人類學家的田野分為“現實田野”和“虛擬田野”兩個部分,新媒介環境下尤其是短視頻平臺中的視覺人類學新現象值得人類學者關注和反思。
二、視覺人類學視閾下影像創作新特征
移動短視頻的發展消解了人類學影像紀錄片的專業性,但不同時段不同地域多元生成的短視頻大大豐富了人類的影像資源庫,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視覺人類學田野調查的難度和成本。數以萬計的用戶在平臺分享自己與他人的點點滴滴,又數以萬計的人們觀看和聆聽“他者”的觀點、意見和想法,新的“虛擬田野”拓展了視覺人類學研究的場域,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新景象。
(一)自我與“他者”界限消弭
自然界中的生靈大都囿于環境的限制,偏居一方。人們受制于自然條件、社會水平和學識認知,將與自己秉性相同或相近的同類畫進自己的圈子,形成族群或建立部落和國家,而將不同于自身的“異類”排斥在外,形成了“我們”與“他者”(異類,the other beings)的對立。如果說上古先民劃分他者是出于自身的生存意識,那么現代社會對大眾他者的區分則是基于客觀意識,用一系列的評價指標和文化標簽將“異類”加以區分,形成不同的意識形態、文化圈層和民族性格。傳統的視覺人類學者進行田野調查時,扛著攝影器材進入異域,仿佛自身就擁有著特權與話語。“我”已不再是原始意義上的我,而是賦予了背后的意識形態、身份認同、價值觀念。當“我”作為媒體人而存在時,其背后所倚靠的是國家力量和傳媒話語,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大眾的利益與訴求,社會效益與傳播價值應該是記者在進行拍攝時放在首位考慮的;當“我”作為一名攝影師而拍攝時,其所考慮的更多的是影片所拍攝的藝術性或其所能產生的商業價值,光線、構圖、色彩、影調都要得到合適的彰顯,后期的剪輯、拼接都需要在中期拍攝時做好規劃;而當“我”真正作為一個人類學者、民族學家來拍攝時,更多考量的是其背后的學術價值和民族情感,將拍攝對象置身于人類發展的歷史的脈絡中,來考量拍攝的內容與要義,反應其背后的哲學思想、宗教信仰、文化觀念、族群歷史、社會制度、生產方式等。作為自身的拍攝主體“我”也不是要置身于被拍攝的“他者”之外,而是要熔鑄于他者的生活方式,將“我”看成“他者”,以進一步消弭二者之間的界限,形成角色轉換和價值對位,在平等對話與合作互信中以一種“不打擾”的狀態完成視覺的形塑。
移動短視頻的拍攝就是以這樣一種“不打擾”的情形拍攝完成的,拍攝主體可以在私密的空間中完成錄像,不必再有采訪時畏懼鏡頭的拘束感,拍攝內容可以是即興的、表演的,也可以是精心策劃安排的。視頻錄制完成后拍攝者可以依據自身喜好對影片進行剪輯和拼貼,使之符合自身特定審美與情感需要,最后經由高速互聯網絡上載至大眾媒介完成發布,短視頻社區平臺會根據特定機制對內容進行二次分發與傳播,實現流量的最大化。在這一過程中,讓·魯什的“共享人類學”(Shared Anthropology)思想得到彰顯并放大,拍攝主體不僅僅是拍攝對象同時還能主動錄制和剪輯,既是視頻的生產者又是視頻的消費者,實現了移動短視頻的“產銷合一”(Pro-sumer model)。自身作為“產銷合一者”(Prosumer),在利用視頻媒介自拍時攝影機看我,完成了“我”向“他者”的轉換,當把短視頻上傳至社區之后,拍攝者的“我”又即刻換回被拍攝的主體對象。而作為拍攝主體的“我”看待被拍攝的自身時,實際上是在觀看被技術宰制后“異化”的自己[11]。拍攝者利用媒介技術完成了自我的“審美”或“審丑”式的形塑,在拍與被拍、看與被看中自我與他者的界限蕩然無存。此外,視頻上載于社區之后,不計其數的網友或者人類學者可以對社區的內容進行虛擬的田野考察,觀察其背后的拍攝地域、民族性格、語言服飾、觀念情感等。在對拍攝視頻點贊、留言、轉發、分享時,實際上與實地的田野考察中的人際交往并無二致,都是一種互動與認可,并實現了人際間的交流。人類學者在社區觀看視頻是一種我看他者的姿態,當他們在社區留言互動后,拍攝者依據反饋做出回應,就是所謂的“我看人看我”,此時的評論者(人類學家)就轉換成了短視頻社區外來的“入侵者”。這種“入侵”不是一種侵略性質的進攻,而是一種介入與參與。雙方在短視頻社區中的這種互動模式下,完成了我與“他者”身份的相互轉換,自我即是“他者”,“他者”亦是自我。
(二)系列拍攝形成視覺“接力”
新媒介環境下的信息具有碎片化的特點,網絡移動社區中的短視頻也不例外。一方面是短視頻平臺對視頻拍攝時長的限制,最初的抖音平臺規定用戶只能上傳15 秒的視頻,而早期的微信平臺的視頻號也只允許上傳1 分鐘之內的短片;另一方面是用戶拍攝的碎片化,普通用戶的非專業性導致拍攝效果欠佳,由于個人拍攝的喜好不同和自身所處時空的限制,拍攝的時長、格式、穩定性、清晰度等都不盡相同。這種碎片化的創作結構使得新媒介環境下的短視頻影像“微”不足道,“不足以展示人類學宏大的整體觀、變遷觀和深層的文化意蘊”。短視頻的拍攝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其拍攝的手段和呈現的方式也不盡相同,如果以短期的視角來評述某一現象對視覺人類學學科的影響的話語也是不夠全面和客觀的。前文已經提及,不僅要關注短期大環境對視覺人類學學科的影響和變化,同時要把這種變化對學科的影響放置于整個時代大背景和人類社會發展的脈絡中來把握。短視頻的碎片化特點不可否認,但某些情況下它又具有一定的視覺“接力性”。
一種是系列式的拍攝。系列式的拍攝與記錄類似于連續的影像短片,單一的短片記錄往往不能夠講清楚故事的成因結果、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若將各個短視頻片段連接起來,也具有宏大的敘事和整體性,其背后的拍攝環境、語言、人物面貌、使用工具等都可見一斑。由于拍攝主體和被攝對象的發展性,其拍攝的內容與題材也具有連續性和漸進性,人物的思想觀念、物質條件、工具技能等處在一種動態的發展變化之中,這些條件的變化帶動著拍攝內容的更新與發展。同時,拍攝內容的漸進變化,也側面反映出被攝對象的物質生活水平與人物精神風貌。二者是一種相互完善、協同進步的開拓式發展,視覺的漸進發展,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好印證。
另外一種是“圍觀”式的拍攝,這種拍攝集中表現為拍攝主體的“在場”性。生產實踐或故事(事件)的發生被在場的“圍觀者”記錄,形成一種全景式的拍攝,對于被拍攝者來說,自身仿佛處于一種被觀看的“全景敞視”(Panopticism)的“監獄”之中,圍觀者就像是監獄外圍筑起的高墻,而具身的攝錄設備就像是無數個攝像頭,實時記錄著正在發生的一切[12]。這種無意的或是獵奇式的在場記錄,也許每個人拍攝的角度、時長、焦點都不相同,也正是這種拍攝的多樣性,促成了視覺“接力”的可能性。人類學者可以將這些視頻片段整合拼接加以重構,實現“虛擬田野”的調查,這種無數個短視頻的接力就是人類社會視覺的合集與傳承。
(三)群體影像重構民族敘事
在攝影術發明之前,人們依靠文字來記錄本民族、本族群或本地區的歷史,出現了所謂的“民族志”“縣志”“鄉村志”等。其中記錄了民族的起源發展史、鄉土的風貌與鄉村的變遷等,這些文字讀本對于文本人類學研究的重要性如同照片、視頻之于視覺人類學研究的重要性。以往的視覺人類學影片主題較為特定和單一,往往只能反應其固定的人群、民族、地域的風貌,無法再現與時代相關的整體歷史風貌與人文情。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納努克》被世界公認為視覺人類學紀錄片的經典之作,再現了愛斯基摩人漁獵和建造冰屋的情景,但是這種再現是家族式的個案,且囿于時代、技術的限制以及資金、人才的匱乏,無法完成對北美地區整體狩獵方式和房屋建造的記錄,更無法較為完整地展現當時當地的生產力狀況和同期的社會歷史發展水平。不同于現代短視頻時代下全景式的拍攝與展現,人人都是“攝影師”,人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能發聲,人人都能記錄并分享著身邊發生的一切。媒介作為人的器官的延伸,以及其所具有的“具身性”(embodiment)使得視覺記錄的空間大大拓展。
“全民參與”式的拍攝和記錄,給視覺人類學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充盈的影像資料。拍攝者個人的記錄或許是基于自身的情感態度價值觀,沒有目的性,但是無數人的共同記錄就會形成一種影像的合力,這種合力是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人與社會精神風貌的集中展現,也是社會生產力的集中表達。視頻記錄的是個人的故事,而視頻的合力則訴說著時代的發展,成為人類學者研究整個時代的影像民族志。20 世紀三四十年代,莊學本作為紀實攝影師在中國西南地區拍攝時,也未曾想到其所拍攝的具有國家民族意識的照片竟對整個視覺人類學或民族志攝影具有無法估量的價值,甚至其本人都不認為自己是人類學者。反觀新媒介環境下的短視頻發展,也許短時期內無法凸顯其自身擁有的人類學、社會學和民族學價值,但是在數十年乃至百年以后,這些影像不再是個人當下生活的簡單樸素的實時記錄,而是成為了整個時代影像合力的一部分,未來的人類學家一定可以依靠這些紛繁復雜的影像發現屬于這個時代發展的印記和規律。
(四)視覺技術發展賦能學科創新
視覺人類學的發展和研究離不開影像的記錄,傳統影像在拍攝錄制時囿于技術和器材的單一,常常表現為固定機位、角度單一,且敘事文本不夠靈活,互動性不足,無法表現出民族志影像的整體風貌,在視覺人類學研究中具有局限性。視覺技術尤其是短視頻平臺的出現和各類移動剪輯App 的誕生,極大地改善了拍攝手段、提高了拍攝效率。在后期的剪輯方面也呈現出專業性向普適性的過度,普通用戶等非攝影師、非人類學者也能輕松駕馭。
高速移動互聯網絡(5G)和移動短視頻平臺(抖音、快手、視頻號)的發展帶來了全民影像的狂歡,手持云臺的拍攝為移動短視頻、Vlog 的拍攝增強了穩定性,也帶去了視覺觀看上的舒適。Dji Osmo Mobile 的短片拍攝軟件生態更是為用戶提供了拍攝的模版,在拍攝完成后自動生成視頻短片,無需剪輯一鍵配樂即可上傳至短視頻社區。相較于傳統的攝錄設備的笨重,Dji Osmo Pocket 以其小巧便攜但又功能強大值得視覺人類學者關注。同時還有無人機、穿越機拍攝提供的新視角,普通的攝像機一般保持在與人等高的位置,而無人機的拍攝提供了一種“上帝視角”,用俯瞰的“眼光”觀察村落的地理位置、形態樣貌和族群分布等。這些新的媒介拍攝方式不僅為短視頻社區的分享提供了便利化和可觀賞性,同時也為視覺人類學整個學科“賦能”。
此外,還能利用AI 技術為老照片、黑白影像上色。例如利用AI 上色修復的1936 年德國老城德累斯頓的紀錄片,再現了20 世紀三四十年代歐洲的街區和人物風貌;還有利用AI 與聲像合成技術將一段拍攝于20 世紀20 年代的北京市井百姓生活的影像資料還原成符合現代視覺觀感的案例,原本黑白分明、模糊不清的黑白影像在經過人工智能修復合成后色彩明快,清晰度高,透過視頻可以看到那個時期人們的生活方式(遛狗、剪辮、喝茶)、交通出行(馬車、轎子)、穿衣服飾(長袍馬褂,青灰土衫)以及禮儀社交(作揖、跪叩)等,彼時的人們對于攝像機這樣的“異物”依然是帶著凝視和怯懦的目光。CG(Computer Graphics)技術的應用,也打開了還原珍貴歷史影像資料的大門。如果說AI 能夠對現有的影像進行色彩修復,CG 則能夠對已經消逝的文化進行還原,其動畫和特效能夠對于還原歷史事實和增添視聽魅力提供強大技術支持。
人類學者在面臨這些新技術、新變革時切忌充耳不聞,應緊隨時代步伐,學習新媒介技術尤其是視頻拍攝與剪輯的相關知識與技能。“我們需要這些新媒體、新技術作為視覺人類學研究中的重要手段和力量,這也是這一學科區別于其他學科的優勢所在。”[13]在器材使用上,掌握傳統的攝錄設備使用方式,也要關注新興的媒介記錄產品;后期剪輯方面,在專業的電腦剪輯軟件和適應上傳短視頻社區的手機移動剪輯App的使用上齊頭并進;同時還要關注“虛擬田野”中的大眾媒介生活方式的變化,在新興領域挖掘出相關學科屬于人類視覺影像的獨特魅力。
三、問題與展望
新媒介技術的發展帶來了記錄載體的便捷化,也帶來了信息傳播的最大化。人們利用新的視頻平臺和社區記錄、分享著身邊發生的一切,使得人類社會的影像的豐盈程度前所未有。視覺的“靜向”向“動向”逐漸過渡,但是這種動態的影像不會取代靜態的照片和繪畫,二者同時存在互為融合發展。新的影像表達和呈現方式,對于視覺人類學的考察和研究也提供了新思路、新視角和新要求。傳統的田野調查變為“虛擬的田野調查”,觀看與被觀看都是一種相對的視角,自我與他者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沒有絕對的他者也沒有絕對的自我;短視頻的記錄見證著這個時代的發展與變遷,相信在時間的沉淀下注定會成為后來的視覺人類學者考察現有大眾媒介生活的重要手段;也許當下每一個個體的記錄“微”不足道,但是全民參與式的記錄就會形成這個時代視覺的合力,傳承著時代的物質與精神風貌。
在關注視覺影像呈現新業態的同時應該注意到,隨著AIGC(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技術的崛起與應用深化,如Sora 這樣的先進模型正對視頻生產領域產生深刻而重要的影響,技術的變革進一步加劇了短視頻社區內影像的紛繁復雜性。其自動化和大規模生產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著視覺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科學性、嚴肅性、客觀性。同一視頻在不同平臺反復上傳,這無疑給視覺人類學者篩選具有學術價值的研究素材增添了大量潛在的無效冗余信息。另外,由AIGC 技術支持所催生的新型娛樂化表達方式,其內容創作往往傾向于迎合大眾趣味和瞬時吸引,對于思想深度和嚴肅議題的關注程度則有待進一步探討。尤其當這些技術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美顏、換臉、拼貼、合聲合成以及VR、AR 等被廣泛運用于視頻制作以模糊現實與虛擬界限時,實際上可能正在侵蝕視覺人類學堅守的真實性原則基礎。面對這一形勢,學科在積極接納和利用新興媒介技術的顛覆式創新時,必須審慎地界定技術與學科研究邊界,精準評估技術融合帶來的效度變化,防止因過度依賴或不當使用而導致研究偏差與精神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