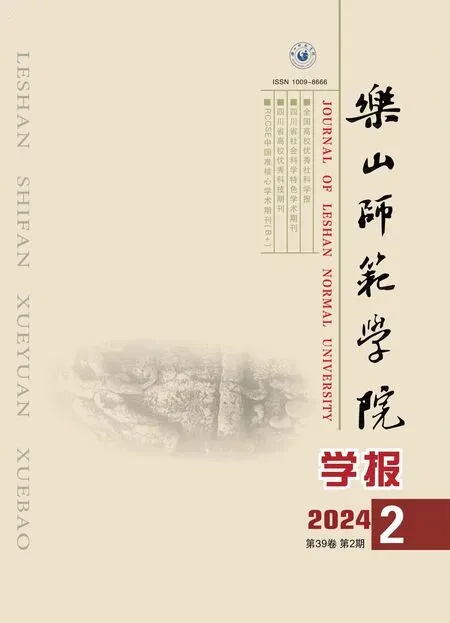唐代士宦矛盾發展態勢與士人選擇
徐樂軍
(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 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507)
唐代士宦矛盾承秦漢以來社會觀念影響,多是政治生態發展的結果,是唐代社會痼疾中持續最久、影響極大的社會動蕩因素。其發展態勢緊隨政治形勢變化和士人群體輿情,士人人生觀感和仕進選擇均可多方位呈現。具體說來,唐代宦官群體引人矚目始自玄宗時,經過代德二朝的發展,已漸成尾大不掉之勢,至憲宗之死達到第一次高潮;再延至穆、敬、文三朝,宦官集團屢釀血案,至文宗甘露之變發展到極致。晚唐時強藩崛起,權力很難再過多集中于朝廷之手,權宦們的影響力自然有所下降。士人們據時而動,雖有一些抗爭和不屑,但依然難逃權宦的打壓。這樣,恐懼和疏離成為士人們的主要選擇;當然也會有個別趨附之徒,士林的口誅筆伐使得這小部分異類聲名狼藉。
一、高力士發跡與“脫靴”形象演繹
秦漢以降,宦官為禍不絕于史。唐初鑒于此,便積極防微杜漸。《新唐書》載:“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閣守御、廷內掃除、稟食而已。”[1]4473又《資治通鑒》載:“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興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余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即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后宦官稍增至三千余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2]1360玄宗敢于突破祖制,重賞宦官群體,關鍵在于高力士等宦官忠心不二,在其奪位過程中立了功。登基后,玄宗需要高力士這樣的近侍維護皇權,而且與外朝士大夫和宗室相比,近侍宦官對皇權的依附性高,威脅性小,是最佳的不二人選。由此宦官集團逐漸成形,有了統一的利益訴求,逐漸發展成一股不可小覷的政治勢力。
高力士發跡情形,諸書記載頗多,此處不予復述。有意味的是,其作為當時宦官集團的頂流人物,與士人李白同時且曾共侍玄宗。在唐代士宦矛盾不斷發展的態勢下,二人無論有無真實交集,作為士宦雙方的流量明星,被后世推到前臺作為交鋒的標志性人物看起來都是不可避免的,而最精彩處莫過于“脫靴”這一焦點情節的演繹。李白同時代或稍后文獻均無記載,據考,應屬杜撰。[3]此事最早見于《唐國史補》:“李白在翰林多沉飲。玄宗令撰樂辭,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后對御引足令高力士脫靴,上命小閹排出之。”[4]163此書作者李肇是憲宗朝官員,書作于穆宗長慶年間,正是憲宗不明不白地死于宦官之手后。此前士宦矛盾略有一段緩和之時,但憲宗之死使其重新繃緊起來。士人們恐懼和憤怒兼俱,卻又無法戰勝權閹,只能在詩文雜記中稍抒郁悶。選擇高力士這一舊時巨宦作靶子,風險小,再加上李白的名氣和放蕩不羈的形象,正好作為替士人發泄憤懣的代言人,至少也能用文字打擊一下宦官們的氣焰。
上文中,李肇所記“脫靴”一事發生時,玄宗態度果斷,脫靴動作尚未發生就將李白叱出,避免了高力士的難堪。對“脫靴”情節有進一步發揮的是段成式《酉陽雜俎》一書。該書前集卷十二《語資》:“李白名播海內,玄宗于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亡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為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4]644此書中的李白形象有了提升,不再是前書中被趕出的狼狽樣,而是一派仙風道骨,連玄宗也為之傾倒。善于察顏觀色的高力士也就失了威勢,面對李白的突然指示,竟然無暇思考就快速完成了“脫靴”動作。事后雖有玄宗通過貶低李白來安慰力士的話,但名士御前羞辱權宦這一經典流傳文本已告完成。
至唐末,高力士作為權閹形象基本成型。李濬《松窗雜錄》詳載李白為玄宗和貴妃進詩后,高力士讒之:“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于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烏皮六縫為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頗深然之。上嘗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4]1213這里已將“脫靴”當作真事自然寫來。李濬生活于咸通后,懿宗、僖宗朝權宦當道,其頭目田令孜更挾持僖宗奔蜀,士大夫群體痛恨不已。書中將高力士描述成一個睚眥必報且又能成功陷害賢良士人的權閹巨宦,影射之義明顯,也表達了作者內心的不平。高力士這一唐末形象也可從其他詩人作品中得以證實,如貫休,雖為僧人,卻頗具儒家入世情懷,《古意九首》其八:“常思李太白,仙筆驅造化。玄宗致之七寶床,虎殿龍樓無不可。一朝力士脫靴后,玉上青蠅生一個……”[5]361,直言“脫靴”發生后,李白受人讒害,如同白玉生蠅。可見到了唐末,以高力士為代言的宦官群體形象在士人筆下已萬劫不復,士宦矛盾趨于無解,宦官被強藩盡誅之后也就更不可能翻身。宦官這種在士人筆下固化的臉譜式形象深刻影響了士人的仕進選擇,對宦官的恐懼和疏離成為終唐之世的主流做法,也成了絕對的政治和道德正確,敢于接近者有可能成為人生污點,膽敢攀附者則更有可能身敗名裂。
二、士宦交往與碰撞的時代選擇
宦官掌權雖自玄宗朝,但高力士并非擅權之輩,其與士人矛盾并不突出。安史之亂后,一切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北夢瑣言》云:“唐自安史已來,兵難薦臻,天子播越,親衛戎柄,皆付大閹。”[4]1858這是總其情形,《新唐書》論之更詳:“肅、代庸弱,倚為捍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慓士奇材,則養以為子;巨鎮強籓,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于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弒殞,文以憂僨,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于天祐。”[1]4473此段將安史亂后宦官專權分為兩階段,肅、代之時,雖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權力極大,但還未能完全掌控軍權;德宗因叛亂陡生,官員萎弱,軍將離散,不得不委信宦官掌禁軍。而從實際效果看,宦官們還真的能擔此重任,不僅成功招撫軍將平叛,還能對皇帝忠心不二。這樣,德宗的親身感受便是:士大夫群體在悠關朝廷生死存亡之際是無能的,更無法保護皇帝的安全,真正值得信任的還是身邊這群家奴。這一認知改變了整個中唐以后政治格局:士宦矛盾由于有了皇帝的成見,宦官集團掌握了很大的權力,士人群體則一再避讓。所以直到唐末,屢屢見到的是權宦高舉的屠刀和士人慘痛的記述,盡管有文宗君臣試圖誅除權宦的努力,結局卻是招致報復而慘不忍睹。
唐之士宦矛盾核心問題在于權力分配,在當時的政治制度下,基本是個死結,但二者并非一直是水火不容,在達到某種平衡時是可以緩和的,甚至還會有些交往。貞元十三年(797),韓愈作為宣武軍節度使董晉幕推官,奉命作《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稱贊俱德才兼備,能為國分憂,受人敬仰。此文后世論者多非之,認為是在媚附權宦,為個人前途鋪路。蔣凡通過辨析,認為此文不過是一般送行程文,且主要是奉恩公董晉之命所作,其與俱并無過多交往。[6]50-54此論確是。德宗朝,宦官立功于朝廷為顯見事實,士人群體不得不承認和接受,無謂地激化矛盾不僅無濟于事,反而會招致帝王的厭棄,更何況也沒有挑起矛盾的政治土壤。俱文珍個人功績頗著,不能因為其是宦官就認定其必定是惡人,這與史實是嚴重不符的。唐代宦官來源復雜,并非全是不學無術之徒,且宦官自小入宮后還能夠接受教育,忠君愛國思想的灌輸是應有之義。退一步說,如果說權宦們全都是攫取了權力的無能之輩,又如何能成為滿腹經綸的士大夫群體之強勁對手?再回到韓愈本身,在八年后的永貞革新當中,他是反對二王的做法,并與友人柳宗元意見對立,但這并不表明其贊同權宦俱文珍等人的做法,在編《順宗實錄》時,他直書禁中罪惡,還惹怒了宦官。可見韓愈對待宦官態度,是在德宗朝士宦矛盾發展態勢相對緩和的情況下就事論事的選擇,這種求真務實的精神才是難能可貴的。與韓愈類似情形的還有元稹和王建。元稹拜相往往被認為是攀結權宦才得以上位的非正常結果,實為冤枉。據咸曉婷考,元稹與宦官崔譚峻和魏宏簡的交往,不過是正常的工作往來,但由于其無端陷入與裴度的個人恩怨之中,被李逢吉巧妙利用加以挑拔,才招致物議。[7]112-117這也從一側面反映出士宦矛盾哪怕有些許緩和,但基本對立態勢是不可能改變的。這一態勢也反映在王建與大宦官王守澄的交往上。王建與王守澄聯宗,兄弟相稱,按當時王守澄權勢完全可能提拔王建驟登高位,但據賀忠考,王建實際上不過是與之閑談宮中瑣事并為創作宮詞提供素材而已,并未在仕進上占多大便宜。在王建心中,宦官本不應有多大權力,并在王守澄面前言及東漢黨錮之禍,引起王守澄不滿,王建只好以《贈樞密》詩自解,好在最后得以全身而退。[8]531-535
德宗朝宦官有救駕之功,憲宗朝宦官有擁立之功,穆、敬、文三朝帝王也都是宦官主導下繼位,所以帝王對宦官的態度直接影響士人的選擇。在文宗朝甘露之變發生前,士宦矛盾盡管暗流涌動,但還不至于撕破臉皮。士人為了個人仕進或者權位,與宦官虛與委蛇也好,傾心交往也罷,都在表面上維持了雙方起碼的體面,內心的不平有時委婉地通過詩歌創作抒發一下,這樣也不會引起宦官集團的太大反感。如韓翃著名的《寒食》詩,以漢之“五侯”喻今之新貴,就有諷刺德宗過分寵信宦官之意。白居易感“宮市”傷民,作《賣炭翁》等詩諷之。這樣的過招顯然是溫和的,在帝王仍然寵信宦官的背景下,士宦矛盾呈現的并不激烈,發生正面沖突還為時過早,士人們的選擇可以理解。
中唐士宦矛盾在德、憲、穆、敬四朝雖未到激烈碰撞程度,但發展態勢明顯,宦官集團由專權、弄權直至廢立皇帝,士人群體的憤怒也在不斷增加。文宗大和二年(828),制舉賢良方正科試,士子劉蕡策文直指朝政腐敗和宦官專權問題之嚴重:“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接著直斥宦官竊取權柄,弄權亂政:“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于今日,此宮闈將變也。”[9]7720這無疑給朝政投下一枚炸彈,引發士宦矛盾從幕后走向臺前,激烈程度也臻于空前。文宗雖由宦官策立,但一直想有所作為,此次親試制舉,就是想選拔才德士子為己所用,以圖掌控實權,振興朝綱。劉蕡此文,實合文宗之心,但對于文宗來說,實在是太早了,他還未找到可用之人為其效力。
中唐士宦矛盾發展態勢表明,二者之間矛盾的緩和是暫時的,甚至只不過是人們的愿景;雙方的較量才是真實的,劉蕡的策文適時撕去了雙方的偽裝,碰撞的到來不可避免,結果就是“甘露之變”這樣慘劇的發生,給了人們無法接受卻又不得不接受的殘酷答案。至此,士人群體由震驚、恐懼慢慢陷入心如死灰般的沉寂,以白居易為中心的東都文人群體更是在錯愕之中開始明哲保身,李商隱仍用其晦澀手法表達自己的傷痛,杜牧、張祜等人的反思和吶喊也顯得曲高和寡。確實如此,碰撞之后勝負立分,全身遠禍才是此時此刻人生第一要義。
三、攀附權宦者的個人考量及仕途影響
清人趙翼言唐之宦官為禍情形,可謂痛心疾首:“東漢及前明宦官之禍烈矣,然猶竊主權以肆虐天下,至唐則宦官之權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弒君、廢君,有同兒戲,實古來未有之變也。”[10]383身處中晚唐這樣的時局中,士人們在追求個人仕進時,不得不把這樣的背景考慮其中,特別是在宦官能夠影響到自己的前程時,是堅守底線還是順勢而為?唐代社會士宦矛盾明顯,大部分士人在追求仕進時出于聲名考量,一般不會主動去攀附權宦,但這是在沒什么把握的情況下。如果現實的誘惑就在眼前,攀附成功就會有直接的收益,那可能就另當別論了。
后世論唐之權閹,為禍最巨者莫過于仇士良。此人甘露之變中屠戮四宰相和數百朝官及士子,并在武宗登基后仍能殺楊妃、安陳二王,可謂勢焰熏天。可就算做下如此惡行,他仍能善終,身為朝官的鄭薰為其撰《內侍省監楚國公仇士良神道碑》,諛之曰:“舉策畫若應神明,閱簿書無逃心目。而又精鑒,冠絕當時。門館賓僚,薦延功行,必求明德,用輔圣朝。則有秉忠正之心,荷匡贊之任,才表正佐,出為國楨,康濟群生,輝華四海者矣。”[9]8273這樣一個惡宦,竟被吹捧成忠心國事、方正賢德之輩。仇死于武宗朝,武宗顧念其擁立之功,當時并未窮究其惡,鄭薰如此下筆,自然有配合朝政之意。何況唐人有諛墓之風,這樣寫也不算什么大錯,哪怕仇死后翌年就被削爵藉家,但從后續發展來看,鄭薰仕途并未受到多大影響。
甘露之變是唐代士宦矛盾發展到極點的標志性事件,自此至唐末朱溫盡殺宦官時,士宦矛盾便再沒有緩和的時候。士人多對宦官痛恨,只是未找到下手之機。宦官群體深知外朝士大夫的仇視心理,為求自保,更加劇了擅權作惡的步伐,并再出現田令孜這樣掌控皇帝的巨閹。當此之際,仍有士子為求仕進,不惜名節而攀附之,在士林中留下罵名。《唐摭言》卷九有《惡得及第》條,錄于梲、裴思謙、黃郁、李瑞四人。關于于梲,筆者詳考,認為其乃咸通宰相于琮之侄,也就是著名詩作《貧女》作者秦韜玉。其攀附權閹田令孜,誰知弄巧成拙,陷于人事紛爭久不得登第,一直到僖宗為田令孜挾持到四川后才特賜及第。[11]24-27裴思謙依恃仇士良登第,其囂張之狀令人生厭:“高鍇侍郎第一榜,裴思謙以仇中尉關節取狀頭,鍇庭譴之,思謙回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明年,鍇戒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階下白鍇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巍峨,鍇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詞貌堂堂,鍇見之改容,不得已遂禮之矣。”[4]1656這一段描述,既見權閹勢大,也見朝臣俯首,亦顯裴強奪狀元的無賴相。不過其后來官運平平,但也無甚大惡,倒是黃、李二人,攀附田令孜,雖都登第,卻在文德年間“俱陷刑網”,應該是未得善終。攀附田令孜的,《唐語林》卷四《企羨》記有五人:“又‘芳林十哲’,言其與宦官交游,若劉曄、任江洎、李巖士、蔡鋌、秦韜玉之徒。鋌與巖士各將兩軍書題,求華州解元,時謂“對軍解頭。”[12]而《唐摭言》載沈云翔、林繕、鄭玘、劉業、唐珣、吳商叟、秦韜玉、郭薰八人,接著道:“咸通中自云翔輩凡十人,今所記者有八,皆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入內故也。然皆有文字,蓋禮所謂君子達其大者遠者,小人知其近者小者,得之與失,乃不能糾別淑慝,有之矣。語其蛇豕之心者,豈其然乎?”[4]1658這兩段對于“芳林十哲”士子的記錄,目的就在于錄其攀附交結權閹行為,并作為士林恥辱來警戒其他士人,但出語尚有分寸,并不認為這些人是十惡不赦之徒。
攀附權宦者為士林所不恥,體現了晚唐特別是咸通后士人群體對宦官為禍唐王朝數百年的痛恨,進而形成了逢宦必反的心理態勢。這樣的社會輿情,有時也會傷及無辜。《唐摭言》卷九有《誤掇惡名》條,就是載其烏龍之事,涉及士子有華京、劉纂、楊篆三人,由于引文較長,故概述之。華京曾在大梁時與監軍宦官面熟,后二人在京師相遇,拱手招呼一下,竟引起士林非議,仕途受阻。劉纂與一醫者比鄰而居,醫者時貧,劉常周濟之,不知道其是權宦吳樞密使門人。醫者后為京兆尹診病,言及劉纂未第之事,頗有不平之意。京兆尹知醫者是這位權宦門人,認為是權宦意,解送時將劉纂取為解元。沒想到事情傳出,主司惡之,多年難以登第。劉篆在淮南幕,游水失衣,為監軍宦官李全華所知,即送來華衣,后來登第為官后,此事竟被同事揭發,不僅貶官,一生都仕途不順。[4]1652這三人本未攀結權宦,只是誤打誤撞與之有了莫名其妙的關聯,竟也招致士林非議,可見唐末士宦矛盾的尖銳程度。
四、結語
要之,唐代士宦矛盾的基本面無本質改變,對立乃至沖突時有發生。雖有表面上的緩和之時,也不過是風雨來臨前的小片晴空。中唐之時,二者的交往和碰撞既是試探,也是勢力的較量和再平衡。晚唐甘露之變打破了這一脆弱的局面,士人群體損失慘重,盡管大部分士人仍能堅持節操不向權宦妥協,但仍有部分士子為了仕進而不惜攀附,這樣的行為自然招致士林抨擊,但由于宦官勢力的強力存在,他們的仕途似乎也沒有全然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