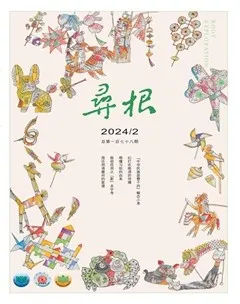一個晚清士大夫的政治圈子
趙廣軍



張佩綸,河北豐潤人,人稱張豐潤,同治十年(1871年)中進士二甲第十九名,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擢侍講、起居注官。他曾一度左右朝野輿論,是風頭最健的清流人物。某種程度上說,晚清言路之開,始于光緒三年(1877年)張佩綸帶頭上書言事,敦促清廷廣開言路。張佩綸可謂為近代清流黨、清流現象做了一個最典型的注腳,也是數千年來主掌言路的清議現象最終止于晚清大變局、讓路于民間報刊等新輿論媒介的一個典范。
張佩綸一生之起合,絕不亞于其孫女張愛玲筆下的小說人物。這樣一個末世王朝的士大夫,若從其被野史時論所評,對比其日記、書信、詩文等文獻所表露出的抱道忤時、易言僨事、身世之感、家國之故等心路歷程,可以映照出近代復雜的人物關系與晚清各種勢力膠著的政治生態。
鄰居圈:張佩綸與吳可讀、陳寶琛
張佩綸出身官宦、士人家庭,曾祖、祖父均為縣學生。6歲時,張佩綸之父死于安徽按察使任上,年幼的張佩綸隨家人轉徙各地,備嘗艱苦,甚至在13歲時親手埋葬了死于兵亂的五姐。最終,張氏在江蘇海門漁村寓居,與沈氏為鄰居,生活逐漸穩定。
沈家是舉人之家,有古書千卷,良田百畝,代有秀才,一度有父子兩人同時被舉孝廉方正,而此父子兩人又均累辭不就,于是被地方高看。張佩綸與沈家子弟一同就學,結識了人生中難得的友人沈熊。13歲時為了能夠多看書,他時常到沈家借書,回家手抄,由是詩筆頓進,練得一手好字。
23歲時,張佩綸入直隸應順天試,并與其侄張壽曾一起考中舉人,叔侄同捷,一時傳為佳話。24歲,他中進士,改為翰林院庶吉士,開始自己的京官生活。后作為散館人員,張佩綸受到了同治皇帝的引見,被授職編修,這一年張佩綸27歲。
在翰林院,張佩綸借助師門、同年、同鄉等逐漸構建起自己的人際圈,圈子里的人多是有功名者,與這些人的交際多通過詩歌的唱和、為長輩撰寫壽序等文化活動來維系。從張佩綸的一生政治活動來看,此時,他獲得了人生最為真摯的兩個朋友,與兩人的交往除了有傳統意味的交際途徑,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交際途徑——鄰居。兩人中,一個是與慈禧太后較真而死的吳可讀,一個是馬尾海戰失利后福建籍京官攻擊張佩綸時處處為張辯護的福建人陳寶琛。
光緒三年九月,張佩綸上《請廣開言路折》推動清廷開言路。也正是從該折起,張佩綸開始發揮言路之權,成為這個白簡搏擊時代的宿主,民生、吏治、洋務、時議等折片漸多,尤多彈劾。對于張佩綸之起,張曾揚在《澗于集·序》中稱:“君之為講官,當光緒初紀,方內定而外患日熾,君與同直諸君奮起言事。”掌控朝政的孝欽皇太后聽政,虛衷采納,后擢典譯署,籌內治外交諸策等國家大計,而張佩綸所“論奏尤以上下交儆,黜邪去蠹為圖治之要,危言急論,彈劾不避權貴,朝右震悚,自二三同志外,多側目視之”。張佩綸成為清班中以最敢言著稱,主持讜議,儼然為清流黨要角。
剛入都為翰林時,張佩綸對其姐夫稱:“京秩無不高寒,而敝署尤為清苦,俸錢最薄,鹽關津貼近俱未復。惟同年世好友外任者,相率為饋歲之舉,美其名曰炭敬。上至宰相御史大夫莫不恃此敷衍,冷官滋味豈復可耐。”五年后給其師夏如椿信中仍稱“京華薄宦,忽忽五年,乞米典裘,進退維谷”,并且“家計拮據異常,俸薄官閑時嗟仰屋”,連赴京應試的老師也招待不起住宿。赴福建之前,生活面臨支了俸祿后多人湊錢飲酒的情形:“名士醵錢聊縱飲,冷官支俸許澆愁”,曾作《移居用膳姜韻》自謂“閉門肯書乞米帖,賞音誰解回帆撾”。
張佩綸每月在家坐等翰林院小吏到家送俸米俸票,獲錢后則喜邀同好共酌。如其《簣齋日記》所記,光緒四年(1878年)十月初七,午后院吏送俸米票來,晚上即偕友人找吳可讀等人同酌。其日記中記載京居時期最多的就是交游、宴飲、肆購等活動。幾乎每日均有招飲、小酌、小飲、集宴等,吃喝中構建起張佩綸的清流交際圈子,這是晚清政治背后的人際生態。
張佩綸與吳可讀“恨結鄰遲”。在安慰因上書言辭戇直而降職調用、返里主講蘭山書院的吳可讀時,張佩綸率諸同好為之餞行,并互贈詩歌相慰。張佩綸作《柳堂先生言事謫官歸主蘭山書院賦詩為別》等十二首詩送別,規勸吳可讀“時疏狂”“瀝膽真能伏闕陳”的同時,也表達了對于言路之開的信心,“早晚朝廷求直諫,就家或更問春秋”,這使得頗具清望的吳可讀“樂甚”。30歲時,翰林院侍講、起居注官張佩綸已獲得專折上奏的權力。居京不易,屢屢遷徙賃屋而居,而立之年,張佩綸擇居南橫街一帶,與吳可讀為鄰。吳可讀起廢復出,又來京師,仍舊住在其南橫街舊宅,與張佩綸宅僅一墻之隔。共同的志趣,往往雅集同人,以詩和酒表達心緒。張佩綸與吳可讀的詩和漸多。
光緒五年(1879年),同治帝下葬,吳可讀懇請主持遷陵的恭親王奕將他派到惠陵襄禮。梓宮奉安后,在返回京師途中,吳可讀自盡于同治帝陵墓旁馬神橋的一座小廟內。在小廟里,吳可讀閉門具疏,寫了一聯剖明心智:“九重懿德雙慈圣,千古忠魂一惠陵。”
吳可讀的死激起在京讀書人無限悲壯激越之思,吳也被譽為“鐵石一儒冠”,躍躍欲試的清流乘勢而起。被諫的慈禧也譽其“孤忠可憫”,吳可讀尸諫事件無疑成為撬動張佩綸等清流群體興起的杠桿。吳可讀的那份奏折成為千古絕唱,他的死對張佩綸影響巨大。
同治帝大葬,張佩綸扈從而行,十七日從陵上歸來,人甚“疲荼”,更為折磨的是又遭“柳翁之變”(即吳可讀“尸諫”),意興闌珊,久久無心日課。另外,生母及內人朱班香同時病倒,一時間張佩綸終夜不得安枕,悶急之至。張佩綸自稱“余自東陵歸,用世之志銳減”,想回南方奉養,但是苦于“菽水無資,不能自決耳。枯坐冥想,萬念奔馳”。四月六日,生母亡故。五月五日,妻朱班香去世。
張佩綸日記對吳可讀身死的細節記載,可以補充一些史料:閏三月初,“柳翁疏入奏,旨令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議具奏”。正在清廷征求朝野諸臣意見的時候,初五日晚上吳可讀即自盡身亡,張佩綸記載的細節:“柳翁初五日卯刻仰藥自盡,讀其廟中周道五紙上有血跡,蓋初擬自刎,復擬自縊,以白綾三尺余環結,書十四字,曰:‘九重懿德雙慈圣,千古忠魂一惠陵。旋以無梁可懸,一板庋門上,動搖易墜,恐有聲致救,乃服洋藥以終。可謂百折不回矣。”
十八日,有人投書于張佩綸門內,署名“粵東布衣古銘猷”,文稱要伸吳可讀其未伸之志,“非公而誰”?要張佩綸“會議時但當據理直言,不可稍有惕疚,以失朝野之望,以辜皋蘭(指吳可讀)之知,天下幸甚,士林幸甚”。還稱自己人微言輕,又不認識張佩綸,因此冒昧投書。這天是張佩綸大女兒的彌月,張羅好午間的客人后,下午,張佩綸出門見李鴻藻,在李鴻藻處見到了吳可讀那篇奏疏。友人紛紛從外地寄書信來,以詩哭吳可讀。居京的同好,互相談論的主題仍舊是“論柳翁疏”。吳可讀死后,張佩綸等一干友人,忙于其葬事,有三河縣查某愿意舍地十多畝,為吳可讀葬地。
光緒六年(1880年),吳可讀子將其臨命前所作家書裝成卷冊拿給張佩綸看,張佩綸泣跋數行。
28歲時,張佩綸在翰詹大考中列為一等,擢升為翰林院侍講,不久又充任起居注官。此時居京師南橫街與北半截胡同之間的張佩綸,結交了居住在丞相胡同西的新鄰居陳寶琛。兩家所居的兩條巷子相連,兩人一南一北過從甚密。兩人同歲,仕途經歷幾乎相同:中進士、選翰林、擢侍講、充起居注官,最相似的莫過于兩人都因中法戰爭遭彈劾。
兩人情誼相投,交稱莫逆,居京時期,幾乎每日相往,做了十年鄰居。陳寶琛是張佩綸一生的至友,友誼也維持一生。即便是張佩綸戍邊之后,兩人交情始終不渝,榮瘁無間。張佩綸被慈禧調往福建戰場時,至友陳寶琛在張佩綸出都前一晤,觀察到他“以氣類太孤為憂”,發自內心地為張佩綸的性格和前途擔憂。后來在馬尾海戰中張佩綸的所為,幾乎被陳寶琛語中。
馬尾海戰失敗后,朝野將張佩綸推至風口浪尖,極盡嘲諷,由于戰敗,幼翁在福建輿論中被譏為只會在閨房中畫畫眉毛的“張敞”。將張佩綸與福建大員何、何如璋、張兆棟放在一起作詞諷刺:“兩個是傅粉何郎,兩個是畫眉張敞。”意指其粉飾無實際用處。野史描述則十分鮮活,說張佩綸兵敗出逃,一夜狂奔三十里,頂著個銅臉盆以躲避炮彈,餓了則大嚼豬蹄,狼狽之狀,斯文喪盡。未戰之前,張佩綸常作大言,好言而無識,曾經說過,失敗了當以三錢鴉片殉難,于是產生了尖刻的聯語:“三錢鴉片,死有余辜;半個豚蹄,別來無恙。”當敗之時,何如璋督福建船政,也是敵至不戰,敗了就跑,跑到彭田鄉依張佩綸,張佩綸怕敵人偵察到,把他騙走。時人有聯諷二人云:“堂堂乎張也,悵悵乎何之?”當時閩人有“兩何莫奈何,兩張沒主張”的說辭。還有一聯諷刺兩張、兩何四人:“堂堂乎張也,是亦走也;倀倀其何也,我將去之。”
作為好友,陳寶琛曾為張佩綸辯護,也被譏諷。好事者作一聯:“八表經營,也不過山西禁煙,廣東開賭(張之洞在山西巡撫任上謝恩折有“職限方隅,不敢忘經營八表之略”的話);三洋會辦,請先看侯官(指陳寶琛)降級,豐潤充軍。”嘲笑陳與二張。輿論聲浪之猛,也使得張佩綸感覺到自己“詩名官謗遍東南”。
張佩綸馬江失事后,陳寶琛正丁母憂,挽聯相慰:“狄梁公奉使念吾親,白云孤飛,將母有懷嗟陟屺;周公瑾同年小一月,東風未便,吊喪無面愧登堂。”
張佩綸之逝,陳寶琛作《入江哭簣齋》:“雨聲蓋海更連江,進作辛酸淚滿腔。一酹至言從此絕,九幽孤憤孰能降!少須地下龍終合,孑立人間鳥不雙。徒倚虛樓最腸斷,年時期與倒春缸。”又有《檢簣齋手札愴然有感其二》云:“君才十倍我,而氣亦倍之。等閑弄筆札,時復雜怒嬉。”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下南洋募集鐵路股款的陳寶琛脛腫復作,在病痛中仍然夢見張佩綸:“魂何來此豈其仙?駕海乘風路萬千。地下相思應更苦,天南獨客有誰憐?余生病歸猶及,窮歲幽憂死儻賢。三島十洲粗一覽,與君恨不冊年前。”張佩綸故于南京,陳寶琛特地千里唁之,時為湖廣總督的張之洞邀其游廬山,而陳寶琛稱“吾為吊喪來,非游山也”,直言力辭,可知張陳之交。張佩綸墓志也由陳寶琛撰寫。
陳寶琛稱張佩綸生平希慕蘇軾,“遭際復相類”,其“一身之升沉榮瘁,實為人才消長、國運榮替所系”,身世與國勢相系,實為確論。所謂“與君生不幸,值此時事艱”。
政治圈:張佩綸與張之洞
清流言官中,以張佩綸、張之洞兩張勢頭最盛。清人李慈銘說:“近日北人二張一李(指張之洞、張佩綸、李鴻藻)內外唱和,張則挾李為重,李則餌張為用。”清流諧音為“青牛”,牛頭指李鴻藻,是為精神領袖;張佩綸、張之洞為青牛的雙角,犀利好斗,專門用來觸人。歐陽昱記載:“同治、光緒間,御史翰林參劾內外官,聲名赫赫者,有陳啟泰、孔憲谷、鄧承修、張佩綸、陳寶琛五人,時稱為‘五把刀,又加張之洞、周德潤、何金壽、黃體芳,內尚有一人,予忘之。共五人,為十友。”另外還有所謂的“松筠十君子”“十朋”“清流六君子”“翰林四諫”“四大金剛”以及御史言官“五虎將”等稱呼,其中多將兩張列入。在時論中風頭最健者,是張佩綸,甚至一度被認為是主盟。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稱:“朝士多持清議,輒推佩綸為主盟。”他“得名最遠,招忌最深”。對此張佩綸并不在意,自詡其諫諍氣魄“往還五千里,咒罵十三家”。
初入政壇,張佩綸以新進少年的銳氣,奮發言事,有澄清之志,彈劾庸吏,以實現“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愿。張佩綸侍講任時,過往密切的多南方人,如狀元洪鈞、林則徐三子林拱樞、榜眼黃自元、吳大等,其中不乏以清流著稱者。而對于直隸同鄉則相交不多,即便是同鄉公餞延約時,對于座客談笑,張佩綸深感“甚鄙”。自幼在南方長大的張佩綸無疑骨子中具有南人情結,這也是張佩綸與南北清流諸人交往的感情基礎,與北清流交往可憑籍里之便,與南清流交往則以寓居浙江的身份。與張之洞的交往則具有多重圈子意義:直隸同鄉、清流身份。
公事之余,張佩綸與張之洞一同游廠肆賞鑒選購書畫文獻以及閑談遣悶之事,籌商修建畿輔先哲祠和編纂《畿輔先哲錄》。
從31歲開始,張佩綸奏折中彈劾折子的數量和影響力驟然擴大,此時也正是其與吳可讀、陳寶琛、張之洞關系最為密切的時候。光緒五年初,嶄露頭角的張佩綸被李鴻藻約話多次,每次多叫上張之洞,日記中未言約談內容,但是約談后多有重要事件和奏折出現。
作為清流兩牛角,兩人行事風格不同,張之洞的奏疏對事不對人,而張佩綸則直接對事對人。好搏擊的張佩綸彈劾之策是善于攻擊人身,對人不對事,而張之洞則“但談時事,不是搏擊”,對事不對人。清流時期,張之洞上奏折、附片共39件,沒有彈劾他人,多是因事陳言。同時期的張佩綸則無一不是彈劾諸官。張佩綸的搏擊最易陷入政治派系爭斗,彈劾的命中率較大,也最易得罪人。連張之洞也在光緒四年十二月十五日邀飯時對張佩綸稱“疏太辣,亦頗稱其膽”。兩人的關系一直很密切,光緒六年,張佩綸收張之洞12歲的兒子為弟子。張佩綸一直尊稱張之洞為“前輩”。在送張之洞補授山西巡撫任時,張佩綸作《送張孝達前輩巡撫山西》,表達自己與之的關系,“公昔朝陽應鳴鳳,居廬初解承明從”。張之洞山西之任是其漸漸隱退清流身份的開始,地理空間的隔絕逐漸淡化了兩張之間的關系。
馬尾戰前,張佩綸共上彈劾和直諫折片31件,聯銜折片8件,為宦則不善迎逢、不善任事。張之洞則不以參劾為能,劾人的折子僅有董恂、崇厚寥寥數片而已,上陳時務者多,表現出長袖善舞、細致任事、工于宦術的本領。赫德對出任總理衙門的張佩綸的看法:“這人曾力主對俄作戰,倡言以殺頭嚴懲崇厚的罪狀等等,鋒芒必露,不畏權勢,很有骨氣,這是驕矜、無知和中國式的愛國主義——中國人的中國——的產物。這位先生經過培養和適當駕馭,一定可以成為出色的新人物。”正當朝野、中外看好張佩綸仕途時,張佩綸的人生發生了逆轉。
光緒十年(1884年),張佩綸倚仗自己了解一點洋務和軍務,年初上疏建議朝廷武科改試洋槍。四月十四日,奉旨會辦福建海疆,被推向了戰爭前線,同時被賦予了專折奏事的特權。一時間,頻發議論的清流陳寶琛會辦南洋,吳大會辦北洋,張佩綸會辦福建。
兩張之間的關系自兩張外放京外開始逐漸疏離,戍邊期間兩人偶有書信。釋戍后,張之洞邀請其主持湖北鐵廠、槍炮廠、織布局等三廠,張佩綸拒絕了。張佩綸來南京定居時,兩人身處同一個城市,此時的張之洞官至代理兩江總督,而張佩綸是宦海潦倒,成為備受時論尋疵的閑人。陳寶琛撰《張佩綸墓志銘》稱,張之洞幾次提出要見張佩綸,皆遭拒絕。但另一種說法是張之洞此時代理兩江總督,深知西太后憎惡張佩綸,為了避免嫌疑,曾經派人向張佩綸暗示,愿意為他修理蘇州的拙政園,請他搬到蘇州去住。張佩綸非常惱怒地說:“我固被議之人,奈何南京亦不容許我住?他不來看我,隨他!”直到半年后張之洞微服來拜訪,一對清流故人才得一見。張之洞細數張佩綸之際遇,四目相對時稱:“就談身世,君(張佩綸)累郗不已。”談到往事,張之洞大哭而別。張佩綸自嘆“孑然孤立,一無倚著,清流以為淮戚而疏之,淮戚又以清流而遠之,清流不成清流,淮戚不成淮戚”。
張佩綸逝后一年,張之洞作《過張繩庵宅四首》稱:
北望鄉關海七昏,大招何日入修門?
殯宮春盡棠梨謝,華屋山邸總淚痕。
廿年奇氣伏菰蘆,虎豹當關氣勢粗。
知有衛公精爽在,可能示夢儆令狐。
親戚圈:張佩綸與李鴻章
張佩綸有三任正妻,27歲在京為翰林院編修時娶朱學勤女朱班香為妻,而朱學勤與翁同交好。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十八日兩人成婚時,翁同因與朱學勤友誼往賀。但是朱學勤似乎并未給這個中意女婿太多蔭庇,成婚五個月后,朱學勤就去世。朱學勤是咸豐三年(1853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出身,家有結一廬藏書樓,搜羅甚富,有宋元明版及舊抄校本千種之多。而這些圖書多為張佩綸獲得,也算是青年翰林人生的一大財富。朱班香與張佩綸相處時論史、和唱,朱班香的論史之作也輯為《班大家集》。朱班香喜好讀史,朱班香的舅舅便將珍貴的宋本《漢史》作為其嫁妝。光緒五年三月四日,朱班香“震將”,九月忽然吐血升余,委頓殊甚。長女出生后朱班香患有兒枕痛,有時號叫徹夜。五月五日,朱班香因病劇去世,張佩綸將朱班香的靈櫬暫寄佛舍。兩月后長女也殤。加上剛剛去世的生母毛氏,三月內頓失三個摯親。朱班香死后,張佩綸不得已出下策,將兩子寄于朱班香娘家,每月給十兩白銀的生活費用,張佩綸則扶柩南下蘇州。七月下旬出都,十月初回到北京,在朱宅賃其東院,接回兩兒團圓。
張佩綸的第二任妻子是邊寶泉之女邊粹玉。邊寶泉是漢軍鑲紅旗人,同治二年(1863年)進士,官至陜西、河南巡撫,閩浙總督。邊寶泉是同治十年辛未科的同考官,故張佩綸以“潤民師”相稱。在張佩綸謫戍次年丙戌,久患肝病的邊粹玉病故于北京府中。生離死別,傷悼彌深。
張佩綸的個體命運、清流的集體運數與大清國易于變臉的政治均在光緒十年發生了轉折。馬尾既敗,張佩綸為眾惡所歸,聲名狼藉,朝士切齒,人們認為“喪師辱國之罪,張佩綸實為魁首”,最終在朝野輿論的彈劾下,張佩綸戍邊張家口等地三年,成為“朝是青云暮逐臣”的失落人。釋戍后,北京居所已經變賣無法回京,也無臉面回京,躊躇之時,洋務大佬李鴻章向其伸出援手,安排其到天津的北洋大臣幕府。張佩綸又有了“淮戚”的形象。
陳寅恪《寒柳堂記夢未定稿(補)》中推測:“馬江戰敗,豐潤因之戍邊,是豐潤無負于合肥,而合肥有負于豐潤,宜乎合肥內心慚疚,而以愛女配之。”《近代名人小傳》也稱張佩綸與李鴻章婚姻成事的原因也是因為馬江戰役:“佩綸初數彈鴻章,鴻章以五千金將意,且屬吳汝綸為介,張李遂交歡。及閩事敗,實由于鴻章,至是乃以女妻之。”
事實果然如此嗎?李鴻章因馬江愧對而許親,確否?事實上,人們混淆了政治和生活的邊界。張佩綸是李家之婿,在李家往往是閉口不談政治。張佩綸的最后一次婚姻——入贅淮門,使其招致時論打擊,也最終使其失去政治參與熱忱,遠離政治,最終以詩人終老。兩家結姻不像輿論所議的突兀,而是與兩家的世誼關系和李鴻章長期的生活庇護有關。
在御史臺任職時,李鴻章曾贈張佩綸舊乘馬車,就戍時缺資的張佩綸賣車以充資用,將馬留在京師,但是無力資養,于是將馬又歸還李鴻章。事實上,早年張佩綸父親客死浙江時,李鴻章資助其扶靈回籍,并為其撰墓表;庶母李太恭人從蘇州遷葬豐潤老家,李鴻章又資助白銀千兩作為營葬之需,張佩綸稱“先世交情之耐久如是,孤兒真感德銜悲也”,這是多大的恩情,而這一切早期均得于李鴻章與張父早歲在剿太平軍時的“并馬論兵,意氣投合,互相激厲勞苦”之誼。后半生的李張關系則有政治因素摻入,自稱閱人無數的李鴻章為何著力贊助,與張佩綸的關系則直接影響其余生。張佩綸曾對李鴻章稱:“師門父執而知我者,僅公一人。”這是為婿之前兩人的師門、父執、知遇關系,但是在政治立場上,此時的張佩綸有獨立的政治判斷。而終其一生看,無論政治利益博弈如何影響著人際關系的變化,李鴻章對張佩綸的支持始終不易。由于政見有別,張佩綸力拒了李鴻章的舉薦,保持著清流門面。張佩綸曾對李鴻章說:“清流須清到底,猶公之談洋務,各有門面也。”李鴻章與張佩綸之間通信六百多封,在關于朝廷政治的各個方面都有深刻的溝通,但是張佩綸仍表現出政治的獨立性。
光緒四年,居京的張佩綸為李鴻章母親作壽文。對于與李鴻章的關系,張佩綸也未曾避諱,甚至專門夜請陳寶琛來宅,將所作的《合肥太夫人壽序》一文拿給陳寶琛請正。光緒五年三月初九日,李鴻章甚至登門造訪,張佩綸答拜。兩人頻頻書信交流政治意見、家事。年底,張佩綸托李鴻章為其父張印塘擬寫墓志。對此,李鴻章稱:“鄙人與尊公為患難之交。承以表墓相屬,奚敢以不文辭?”希望與張佩綸當面再商量。光緒六年二月五日歸葬父親骨骸返豐潤途中,在天津李鴻章約談,詢問海防問題。三月返京時在天津至李鴻章衙署,討論北洋軍務,李鴻章也親自造訪其住處,如三月六日上午張佩綸應邀到北洋大臣署拜訪李鴻章,下午李鴻章來住處回拜,次日晚上李鴻章又來拜談,三月十日李鴻章約其到電線房,十一日晚李鴻章來訪,十三日、十四日、十六日、二十日、二十三日又來。在天津23天的時間里,兩人互訪談話十余次,張佩綸欲返回北京,又被挽留三天。在天津時張佩綸也多與李鴻章幕僚交往,參觀大沽炮臺、機器局等。李鴻章問其對朝廷大臣意見,張佩綸則稱不可妄言天數,但是又建議李鴻章趕快擬奏折上奏,以阻浮議,李鴻章將此事委托于他。李鴻章這次主動邀請丁憂的張佩綸來天津近距離觀察北洋軍務。此后,張佩綸對李鴻章的稱呼也改稱為“肅毅師相”,待之以師,尊其為相。光緒六年九月在游歷了塞北各處回到北京后,張佩綸又來天津,李鴻章邀談,這次李鴻章干脆招其到府中居住。
光緒七年(1881年)八月二十八日,依例丁憂期滿的張佩綸起復,又出任翰林院侍講,十二月八日復任起居注官。因為長期不居京師,張佩綸丁憂間與清流的來往要少于與李鴻章的來往。復任后回到北京則又與清流維護起舊誼。
光緒十四年(1888年)五月,張佩綸結束了流放生活,離開張家口戍所,李鴻章為他支付了二千兩銀子的流放費用。十一月十五日,張佩綸與比自己小十七歲的李鴻章女李菊藕結婚。這種老少配、門第懸殊的婚姻一時間讓世人咋舌。局外各種議論紛沓而至。
有人作聯曰:“老女嫁幼樵,無分老幼;東床變西席,不是東西。”
有人作詩曰:“簣齋學書未學戰,戰敗逍遙走洞房。”
有人作對曰:“搖尾來北洋,贅婿妻嬌嫌夫老;辱國幸身全,欺世飲罪滿軍臺。”
后來有人戲為張佩綸作挽聯稱:“三品功名丟馬尾;一生艷福仗蛾眉。”
有人演繹出小說的情節:張佩綸在李家作菊藕的家庭教師,由此擦出愛情火花。
有稱張佩綸入都會試,李鴻章為主考,發榜后到李宅謁師,李鴻章喜其才華,說:你的才氣與我的小女相同。張佩綸即跪地稱婿,李鴻章也不能推辭,于是許其婚姻。
這些都與史實大相徑庭,其他野史記載多類此,為了更具戲劇化,因此極盡諷刺“淮戚”之意。
張佩綸夫婦婚后住在天津直隸總督衙門,有時也給李鴻章出出主意。到了甲午戰爭爆發,李鴻章之子李經方企圖出任前敵統帥,為張所阻,郎舅竟成水火,當時有“小合肥欲手刃張簣齋”之說。李經方旋運動御史端良彈劾張佩綸,獲上諭:“著李鴻章即行驅令回籍,毋許逗留!”這樣,張佩綸不得不偕妻南下,定居金陵。
對此婚姻,張佩綸非常滿意,曾在李鴻章夫人的祭文中表達知遇之恩,稱:“光緒十四,我來自邊,謗滿天下,眾不敢賢,夫人相攸,亦具深識,申以婚姻,毅然勿惑,始終無間。”光緒十八年(1892年)六月,李菊藕生母趙夫人過世,臨終前未有一言,回頭看張佩綸“若有所囑”。再者,李菊藕的才情、相貌無雙,《孽海花》稱她“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賢如鮑、孟,巧奪靈、蕓”。
同樣,李鴻章對張佩綸,既有欣賞的成分,又有籠絡的考慮。張李之間的跨代友情似乎持續頗久。李鴻章死后,張佩綸撰《祭外舅李文忠公文》,自稱“門生、子婿”,贊其“創二千年未有之宏規,通商、惠工、選兵、厲械,百廢俱舉”,但是獨于外交備受讒謗,受讒謗似與自己身世類。
張佩綸稱其父孤軍轉戰,始識李鴻章于廬肥,患難定交。他指出自己是以翰林身份拜謁李鴻章,李鴻章喜故交有后,“乃深責其來遲”,但是兩人坐談天下事時,張佩綸自述自己少年意氣畢呈:“年少氣盛,侃侃而進危辭,流俗所不能堪者,公雖變色欲起,旋溫然而易怡。賓僚燕見,或及不肖姓氏,輒嘆賞。其瑰奇東陵道上評騭當世人物,雖盛名或見鄙夷,已而拊吾背曰:子之于我大體相似,然而磽磽者易缺,皎皎者易緇,尚其斂剛銳之氣,忍辱負重。”釋戍后,李鴻章仍規勸其養晦:“當日若肯耐事,不駐馬江,乃無謫戍之累,總由忍辱二字未做到。今愈忍愈辱,何補于事耶。”張佩綸此時并未理解李鴻章點到為止的勸說。戍邊之災,張佩綸明白了“養晦而待時焉”,而此時張佩綸則已“謗滿天下”。
光緒十年盛昱評騭當朝人物時,就“力詆張幼樵(指張佩綸)一‘巧字”,指斥其政治的投機性,翁同對賦予張佩綸“巧”字深以為然。之后,為人詬病的清流張佩綸最終入淮系李鴻章幕、贅淮系為婿,被視為政治投機性的表現。在天津寄居籬下的生活,張佩綸非常在意自己的身份,甲午戰爭中絕口不論兵事,唯一能夠為李鴻章做的是彌合李鴻章與李鴻藻、張之洞之間的關系,很難恢復當年為皇帝開講筵的氣概。對于李鴻章的安排,張佩綸以“非隱非吏”“非主非客”的尷尬來表達自己的感受。離開督署的張佩綸攜家人由水路離開天津,遷居南京七灣。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又遷居張襲侯舊園為終隱地。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七日,在清流與淮戚的尷尬身份中,張佩綸終老南京,時年56歲。
史學界所謂的南北之爭、清流與洋務的對立等論斷似乎并不能解釋張佩綸的政治圈子,晚清的政治生態也不像我們理解的那么簡單,而是呈現出更為復雜的人際狀態。
—————————————————————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