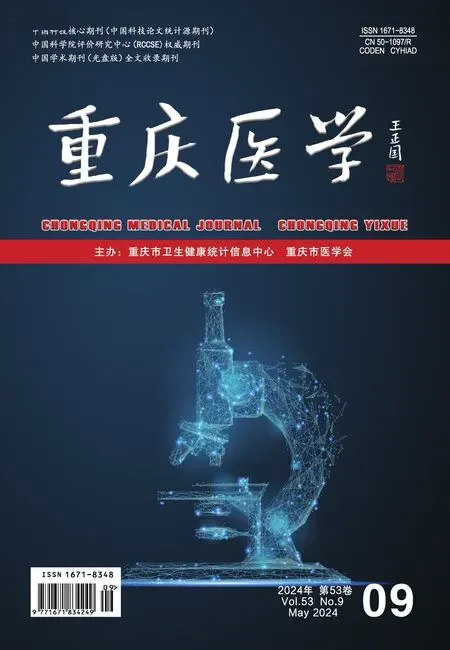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營養狀況及免疫功能的臨床觀察*
葉 婷,羅雪清,黃美金
(右江民族醫學院附屬醫院:1.營養科;2.超聲科3.感染性疾病科,廣西百色 533000)
肝硬化患者普遍存在營養不良,而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營養不良的發生率則更高,達44.1%[1]。營養不良與肝硬化的病情進展及預后密切相關[2],是肝硬化患者預后不良的獨立預測因素。而有研究發現,大部分肝硬化患者都會出現細胞免疫功能下降,免疫功能與肝硬化的發生、演變及進展關系密切[3]。本研究采用營養風險篩查 2002(nutritional risk screening 2002,NRS2002)評分對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進行營養風險篩查,評估其營養風險,分析其營養狀況及免疫功能,為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的下一步營養干預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 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在本院住院的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132 例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患者失代償期肝硬化的診斷符合2020年版《肝硬化診治指南》[4]。排除標準:(1)神志不清、不能站立,不能測量身高、體重等指標的患者;(2)肝性腦病、肝衰竭患者;(3)3個月內輸注人血白蛋白及血漿的患者;(4)合并惡性腫瘤、心腎功能不全的患者;(5)合并內分泌及代謝疾病者。病因:乙型病毒性肝炎91例,丙型病毒性肝炎22例,酒精性肝炎19例。本研究方案獲得本院倫理委員批準(審批號:YYFY-LL2024-226),所有研究對象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測量身體數據
測量患者的身高(m)、體重(kg),根據身高、體重計算BMI。其中BMI 18.5~<24.0 kg/m2為正常,<18.5 kg/m2為消瘦,24.0~<28.0 kg/m2為超重,BMI≥28.0 kg/m2為肥胖,以上測量均在早晨起床排空二便后,赤足進行測量;測量患者肱三頭肌皮皺厚度(TSF)、上臂圍(AC)、上臂肌圍(AMC)。TSF的測量方法:在患者的右側上臂肩峰至尺骨鷹嘴窩中點處提起患者皮膚和皮下組織,于其下約1.5 cm處用皮褶厚度儀測量皮褶厚度,測量3次,取平均值。AC的測量方法:用皮尺在上臂中點測量3次,取平均值。AMC的計算方式為AMC=AC(cm)-3.14×TSF(cm)。以上評估和測量均由經過培訓的醫護人員在患者入院后24 h內完成。
1.2.2營養風險評估及分組
采用歐洲腸外腸內營養學會推薦的NRS2002評分[5]評估患者營養風險,NRS2002評分由疾病嚴重程度評分、營養狀況受損評分及年齡評分3項評分的總和組成。NRS2002評分為0~7分,其中≥3分為有營養風險、<3分為無營養風險。NRS2002評分≥3分的患者再分別根據NRS2002評分3~<5分和5~7分分成低營養風險和高營養風險兩個亞組。132 例研究對象中,高營養風險組19例,男16例,女3例,年齡21~72歲,平均(46.58±17.63)歲;低營養風險組53例,男48例,女5例,年齡19~69歲,平均(51.57±9.43)歲;無營養風險組60例,男51例,女9例,年齡19~69歲,平均(50.23±11.76)歲;3組患者性別、年齡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3 收集指標
入院后次日早上6:00點抽空腹靜脈血送檢。采用希森美康se500全自動血球分析儀(日本希森美康株式會社)檢測血紅蛋白(Hb);cobas c702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德國Roche公司)檢測清蛋白(ALB)、前清蛋白(PA)、視黃醇結合蛋白(RBP)、總膽紅素(TBIL)、膽固醇(TC)、甘油三酯(TG)、IgG、IgA、IgM。希森美康cs5100凝血儀(日本希森美康株式會社)檢測凝血酶原時間(PT);采用BD FACSCantoTMⅡ全自動流式細胞儀[美國BD公司,試劑管為碧迪醫療器械(上海)有限公司產品]分析CD4+T細胞百分比、CD8+T細胞百分比、CD4+T細胞百分比與CD8+T細胞百分比的比值(CD4+T/CD8+T)。根據患者ALB、TBIL、PT、腹水及肝性腦病的情況評估肝功能 Child-Pugh 分級。記錄患者臨床并發癥發生率(包括消化道出血、腹水、肝腎綜合征、肝性腦病、自發性腹膜炎)。
1.4 統計學處理

2 結 果
2.1 3組人體基礎指標比較
各營養風險組的人體基礎指標BMI、TSF、AMC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高營養風險組的BMI、TSF、AMC低于低營養風險組和無營養風險組,低營養風險組的BMI、TSF、AMC低于無營養風險組,組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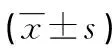
表1 3組人體基礎指標比較
2.2 3組營養指標比較
各營養風險組的實驗室營養指標Hb、ALB、PA、RBP、TG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高營養風險組和低營養風險組Hb、ALB、PA、RBP、TG均低于無營養風險組,高營養風險組的ALB、TG低于低營養風險組,組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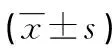
表2 3組營養指標比較
2.3 3組免疫指標比較
各營養組的免疫指標IgG、IgA、CD4+T細胞百分比、CD4+T/CD8+T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高營養風險組和低營養風險組的免疫指標IgG、IgA高于無營養風險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高營養風險組和低營養風險組的CD4+T細胞百分比、CD4+T/CD8+T均低于無營養風險組,組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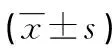
表3 3組體液免疫和細胞免疫指標比較
2.4 3組Child-Pugh分級情況比較
各營養風險組Child-Pugh分級構成比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85.374,P<0.001)。高營養風險組的Child-Pugh B級、C級患者比例高于無營養風險組,低營養風險組患者比例高于無營養風險組,組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高營養風險組、低營養風險組的Child-Pugh A級患者比例低于無營養風險組,組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3組Child-Pugh分級情況的比較[n(%)]
2.5 3組臨床并發癥發生率比較
各營養風險組并發癥消化道出血、腹水、肝腎綜合征、肝性腦病、自發性腹膜炎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高營養風險組消化道出血、腹水、肝腎綜合征、肝性腦病、自發性腹膜炎發生率高于無營養風險組,低營養風險組消化道出血、腹水、肝腎綜合征發生率高于無營養風險組,組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5 3組臨床并發癥發生率比較[n(%)]
2.6 NRS2002評分與營養指標和免疫指標的相關性分析
NRS2002評分與BMI、TSF、AMC、Hb、ALB、PA、RBP、TC、TG、CD4+T細胞百分比、CD4+T/CD8+T呈負相關(P<0.001),與IgG、IgA、IgM呈正相關(P<0.001);與CD8+T細胞百分比無關,見表6。

表6 NRS2002評分與人體基礎指標營養指標和免疫指標的相關性分析
2.7 失代償期肝硬化NRS2002評分與人體基礎指標、營養指標、免疫指標的多元回歸分析
以NRS2002評分為因變量,以BMI、TSF、AMC、Hb、ALB、PA、RBP、TC、TG、IgG、IgA、IgM、CD4+T細胞百分比、CD8+T細胞百分比、CD4+T/CD8+T為自變量,進行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結果發現TSF、AMC、Hb、ALB、RBP與NRS2002評分存在線性回歸關系,見表7。

表7 失代償期肝硬化NRS2002評分與人體基礎指標、營養指標、免疫指標的多元逐步回歸分析
3 討 論
蛋白-能量營養不良(PEM)是肝硬化的一個關鍵特征,營養不良可以預測肝硬化的嚴重程度,是影響患者生存的關鍵因素[6]。營養不良也可被視為肝硬化的并發癥,因為它對疾病進展和結局有負面影響。營養不良可導致肝硬化患者生活質量降低,腹水和自發性腹膜炎等并發癥的發生率增大,是患者不良臨床結局的重要預測指標[7]。有研究表明,隨著肝硬化的進展,患者細胞免疫功能明顯降低,易被病毒、細菌侵染[8],與肝硬化失代償期自發性腹膜炎、內毒素血癥及菌血癥的發生密切相關。因此,對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進行準確的營養評價,盡早發現營養風險及營養不良,早期給予合理的營養支持治療對改善臨床結局具有非常重要的臨床意義。
NRS2002評分是一種用于評估住院患者營養風險的有效工具[9],在肝硬化患者中亦能靈敏地反映患者的營養風險[10]。有報道顯示,68.42%的肝硬化患者存在營養風險[11]。BMI可用于判斷營養不良及其程度,還可用于動態監測患者營養狀態變化,是臨床判斷營養狀況的基礎指標之一[12],但由于大多數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存在水鈉潴留,有腹水和下肢水腫的癥狀和體征,因此,測量所得的BMI往往要比實際偏高。研究發現,隨著營養不良風險的增高及營養不良嚴重程度的增加,BMI水平明顯下降[12]。而TSF、AMC 因不受水鈉潴留的影響,是適合所有肝硬化患者的營養評價指標。患者的脂肪貯備情況主要用TSF評價,AMC則用于評價肝硬化患者的總體蛋白水平,兩者綜合在一起,能較好地評估患者體內皮下脂肪和蛋白儲存,以及消耗程度[13]。由于TSF不受水鈉潴留的影響,是人體測量數據中最有效的參數,與肝硬化嚴重程度呈正相關,與肝硬化的病死率也相關[14]。陳向東等[15]研究發現,有營養風險的肝硬化患者的BMI、TSF、AMC低于無營養風險的患者。本研究中高營養風險組的人體基礎指標BMI、TSF、AMC低于低營養風險組和無營養風險組,低營養風險組BMI、TSF、AMC低于無營養風險組,組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NRS2002評分與BMI、TSF、AMC呈負相關(P<0.001)。
肝硬化患者存在營養攝入不足和吸收不良等情況,而消化道出血、腹水、電解質紊亂等并發癥進一步加重了肝硬化患者的營養不良。肝硬化貧血的主要原因是缺鐵,貧血與肝硬化的臨床表現和肝功能異常存在密切的關系[16]。由于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食欲下降、消化吸收功能障礙,肝細胞壞死導致蛋白合成不足是ALB、PA、RBP等血清蛋白水平降低的主要原因。因此,ALB、PA、RBP不僅是反映機體蛋白營養不良的可靠指標,而且是反映肝功能的重要指標[17]。指標半衰期越短,對評估患者的營養狀況和判斷營養支持的療效越有價值。三者的半衰期分別為21 d、1.9 d、12 h,故PA、RBP是反映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早期蛋白營養不良的敏感指標[18]。鄭健蓀等[19]研究表明,RBP、TC、TG等指標可有效評估肝功能損傷的情況,與Child-Pugh分級密切相關。TC、TG下降對判斷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患者病情嚴重程度具有重要作用[20]。高營養風險肝硬化患者肝功能儲備功能差,因此肝功能 Child-Pugh 分級高及營養不良的比例也高[21]。本研究高營養風險組和低營養風險組的營養指標Hb、ALB、PA、RBP、TG均低于無營養風險組,高營養風險組ALB、TG低于低營養風險組,組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高營養風險組的Child-Pugh B級、C級患者比例高于無營養風險組,低營養風險組患者比例高于無營養風險組,組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相關研究結果一致。NRS2002評分與Hb、ALB、PA、RBP、TC、TG呈負相關(P<0.05)。高營養風險組的消化道出血、腹水、肝腎綜合征、肝性腦病、自發性腹膜炎發生率高于無營養風險組,低營養風險組消化道出血、腹水、肝腎綜合征發生率高于無營養風險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多元線性回歸提示,Hb、TSF、AMC、ALB、RBP與NRS2002評分存在線性回歸關系。
免疫球蛋白主要由漿細胞合成,具有較強抗體活性,可誘發抗體形成,使補體活性增強,起到免疫效應。IgG、IgA和IgM 是人體中重要的免疫球蛋白,三者均能反映肝損傷的情況。金宇等[22]發現免疫球蛋白與肝硬化進程有關,肝硬化程度越嚴重,免疫球蛋白水平越高。張靜等[23]研究發現,血清IgG、IgM、IgA異常高表達與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預后不良存在密切聯系,三者聯合檢測可增強預測患者預后的能力。張銳[24]發現,血清IgG、IgM、IgA可作為臨床診斷肝硬化的指標,對判斷肝功能受損程度,評估疾病的預后有重要價值。本研究高營養風險組和低營養風險組的免疫指標IgG、IgA高于無營養風險組,組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NRS2002評分與IgG、IgA、IgM呈負相關(P<0.05)。
細胞免疫在肝硬化進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慢性肝炎進展至肝硬化與細胞免疫功能有密切的關系。劉欣等[25]認為,T細胞亞群比例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肝硬化患者門靜脈高壓病情發展情況。李欣等[8]認為,隨著肝硬化病程的進展,患者細胞免疫功能加速減退,Child-Pugh C級的患者CD4+T細胞百分率、CD4+T/CD8+T較A、B級明顯減少。提示Child-Pugh C級肝硬化患者機體更新CD4+T細胞的能力降低,患者細胞免疫功能明顯降低,導致患者易被病毒、致病菌感染,這與肝硬化失代償期自發性腹膜炎的發生密切相關。本研究高營養風險組和低營養風險組CD4+T細胞百分比、CD4+T/CD8+T均低于無營養風險組,組間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NRS2002評分與CD4+T細胞百分比、CD4+T/CD8+T呈負相關(P<0.05)。
綜上所述,高營養風險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的營養狀況及免疫功能均較低營養風險者差。NRS2002評分簡單易于實施,因此,在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的診治中盡早地進行NRS2002評分評估,篩選出高營養風險患者并及時進行營養干預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