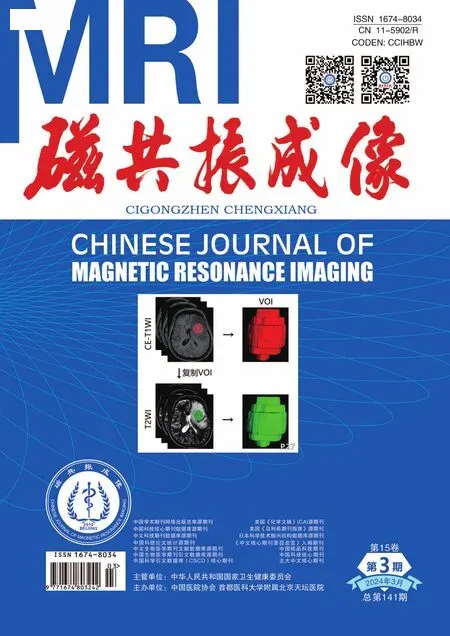經前期焦慮障礙相關情感回路異常的腦功能成像研究進展
陳思睿,徐小雯,趙陽,肖磊,陳振宇,廖海
0 引言
經前期焦慮障礙(premenstrual dysphoric disorder,PMDD)是女性獨特的情感障礙性疾病,發病率約占育齡期女性的3%~8%,其特征是在黃體晚期出現周期性情感、行為及軀體功能障礙,其中以情感功能障礙為主,主要表現為情緒不穩定、易怒、抑郁和焦慮等癥狀,常伴有明顯功能受損,其特征性表現為上述癥狀發生于月經周期的黃體晚期且月經出現后不久癥狀消失[1-2]。PMDD 在最新的美國精神障礙診斷統計手冊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V, DSM-V)中被認為是一種與激素相關的抑郁癥,該疾病嚴重影響女性的身心健康,重度患者被視為自殺的高危人群[3]。目前PMDD 的病理生理機制尚不明確,現有研究認為PMDD 的發病與卵巢激素水平的波動以及神經遞質異常等有關,而卵巢激素對突觸傳遞的調節作用主要影響涉及情感和認知功能的大腦回路[4-6]。眾所周知,PMDD 的主要癥狀為情感障礙,參與情感和認知功能相關腦區的異常是PMDD 發生的關鍵因素,因而情感回路障礙可能是PMDD 重要的神經病變機制[7-8]。情感回路主要位于前額葉皮層-邊緣系統-紋狀體-丘腦-基底節等區域[9-10],其中由“前額葉、杏仁核及邊緣系統”構成的神經回路在PMDD 情感調節和傳導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腦功能成像是研究腦回路的重要手段,其是一類非侵入性的神經功能活動測量-成像技術,主要包括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和單光子發射計算機斷層掃描(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SPECT)以及功能性近紅外光譜(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等技術。近年來,隨著醫學影像技術的迅速發展,功能神經成像技術已成為研究PMDD中樞神經機制的重要手段,尤其是fMRI,已廣泛應用于女性月經周期相關腦活動研究,在PMDD的研究中具有巨大應用前景。
因此,本文旨在通過綜述近年來PMDD相關情感腦網絡功能成像的研究發展現狀,加深對卵巢激素作用下神經功能異常改變的理解以及對未來研究方向進行展望,為尋找PMDD的病因機制提供科學依據和支持。本文擬基于腦功能成像技術對PMDD 情感功能障礙所涉及的腦區及其功能連接進行系統闡述。
1 前額葉皮層
前額葉皮層(prefrontal cortex, PFC)是額葉的聯絡皮質區,接收與之互相連接的丘腦背內側核投射的皮層,位于額葉運動和前運動皮層的前面,主要分為眼眶、內側和外側三個區域,在計劃和執行、情緒和行為方面發揮作用,是最早被發現與情感障礙激活的相關區域之一[11-13]。
研究發現,背外側PFC 對PMDD 中受影響的情感功能最為重要[14-15]。BALLER等[16]首先采用PET結合fMRI 技術證實,PMDD 患者背外側PFC 激活異常增加的程度與癥狀嚴重程度呈正相關,并提出背外側PFC 功能障礙為PMDD 病理生理學的關鍵因素。GINGNELL 等[17]研究發現PMDD 患者與健康對照組相比,在黃體期面對負面情感刺激時PFC 的反應性顯著增強,且孕酮水平與背外側PFC 對積極情感刺激的誘導反應呈正相關關系。同樣地,一項利用任務態fMRI 對比分析44 例PMDD 患者和42 例健康女性情感刺激前后腦部神經活動狀況的研究結果提示,PMDD 患者在誘導情感刺激任務下的PFC 反應性顯著增強[18]。目前,fNIRS 作為腦成像方法應用于大腦活動狀態的評估,有研究借助fNIRS 通過測量PFC中氧合血紅蛋白水平的變化,發現患有經前綜合征(premenstrual syndrome, PMS)(一種比PMDD 更溫和的綜合征)女性在黃體期負面情感的增加與負責情感認知功能的PFC 的血流量減少有關[19]。這些研究證實了PFC 功能異常與PMDD 中情感認知功能的紊亂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另外,首次使用18F-2-氟-2 脫氧-D-葡萄糖(fludeoxyglucose, FDG)-PET 測量PMDD 大腦葡萄糖代謝情況的研究發現,PFC 和小腦區域共同參與情感的處理,從卵泡期到黃體晚期患者小腦活動升高,并且與情緒惡化呈正相關。此外,PMDD 患者背外側PFC 與小腦小葉的活動增加,代表調節情感功能的大腦-小腦反饋回路共同激活,是影響PMDD嚴重程度的關鍵腦回路[20-21]。
2 前扣帶回
扣帶回是邊緣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包含4個解剖區域:前扣帶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中扣帶回、后扣帶回、扣帶回壓部。不同解剖連接和功能的扣帶回區域具有不同功能,胼胝體膝部腹側的ACC皮層與情緒行為的調節有關,且ACC與杏仁核及其他PFC 區域高度聯通,構成ACC-杏仁核環路[22-24]。GINGNELL 等[25]研究發現,與健康對照組相比,黃體期PMDD 患者ACC 對社會刺激的反應性減弱,且ACC反應性減弱和連通性受損與抑制情感反應相關。全腦分析發現,PMDD患者在黃體期具有較低的ACC激活,提示情感誘導的扣帶皮層激活受損,并且證實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基因型參與了PMDD患者黃體期ACC的情感加工[26]。另外,基于15O-H2O-PET 技術測量PMDD 患者靜息局部腦血流量(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rCBF)的研究發現,PMDD 患者在暴露于雌二醇和孕酮條件下的膝下ACC靜息rCBF降低,具有顯著的激素相互作用,且單獨使用亮丙瑞林和黃體酮條件下靜息rCBF的變化與ESC/E (Z)基因表達具有相關性,ESC/E (Z)復合體是一種重要的卵巢類固醇激素調節基因沉默復合體,從而提示膝下ACC 可能是參與PMDD情感調節的神經解剖學位點[27]。
以上研究發現表明,黃體期的PMDD 患者出現了情感回路腦區網絡的異常改變,其中背外側PFC和ACC 是PMDD 患者情感功能障礙的重要神經位點,提示情感神經回路功能異常可能是PMDD 患者情感癥狀或缺乏情感控制的重要病因機制。然而,目前尚不清楚這些腦區的功能改變是如何導致神經回路水平上的特定情感相關癥狀出現,其回路功能障礙的病理生理機制亟待進一步研究。
3 杏仁核
杏仁核是大腦邊緣系統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情感產生和處理方面有著重要的價值[28]。杏仁核參與自下而上的情感刺激的檢測、過濾、編碼和檢索,也參與情感刺激的感知、記憶、獎賞功能,并通過調節對外部情感刺激顯著參與認知功能[29-31]。在健康女性中,負面情感狀態與杏仁核和腦島的反應性增強以及投射到杏仁核的ACC區域的反應性減弱有關[32-33]。此外,有文獻報道,杏仁核和腦橋與其之間連接的改變是焦慮和抑郁等負面情感狀態的特征[34-35]。有研究借助SPECT 檢測重度抑郁癥(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腦活動代謝,通過分析與漢密爾頓抑郁量表中癥狀嚴重程度評級之間的相關性,發現抑郁狀態的嚴重程度與左側杏仁核、豆狀核和海馬旁回的rCBF 呈負相關,焦慮嚴重程度與右側前外側眶額皮質的rCBF 呈正相關,并證實了MDD綜合征中焦慮和抑郁負面癥狀與杏仁核等特定腦區的相關性[36]。盡管PMDD 患者在黃體期存在嚴重焦慮、抑郁的精神狀態以及對社會刺激的敏感性,但在PMDD 中杏仁核反應性的研究結論并不盡相同。PROTOPOPESCU等[37]采用fMRI 研究PMDD患者在情感控制任務背景下的神經反應時發現,與對照組比較,PMDD 患者在黃體期的杏仁核對情感誘導下的反應性增加。與先前的結果相似的是,有研究發現在具有高度焦慮傾向的PMDD 個體中黃體期誘導下杏仁核對情感面孔的反應性增加,說明PMDD 患者的杏仁核更容易被激活;該研究團隊還發現左側杏仁核在黃體期比卵泡期表現出更高的反應活動,且此反應與孕酮水平變化有關,支持了PMDD 中孕酮敏感性增強會影響社會情感的皮質邊緣處理的假說[25,38]。在最新一項對大腦情感刺激的反應相關研究中,PMDD 受試者在月經周期黃體晚期的情感處理網絡關鍵區域(即杏仁核、海馬)與對照組相比觀察到更明顯的活動反應[39]。
此外,情感調節的神經網絡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基底核-杏仁核等邊緣系統,通過編碼刺激的情感屬性及對不同類型的情感進行評價加工,進而產生情感反應;另一方面是利用額葉功能來執行對情感刺激的識別、評估及監測的控制[40-41]。PFC-杏仁核連接被認為是情感調節中重要的神經回路,是月經相關的情感障礙的神經特征[42],觀察PMS 患者與健康對照之間的功能連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差異,發現PMS 患者具有更強的杏仁核-PFC 連接性,右側杏仁核與右側中央前回、左側ACC 和內側PFC之間的連接性與患者的癥狀強度呈正相關。PETERSEN 等[15,43]通過比較PMDD 與健康對照組的執行控制網絡(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ECN)、默認模式網絡(default mode network, DMN)和杏仁核的內在連通性發現,與卵泡期相比,PMDD患者黃體晚期的雙側杏仁核與DMN 的FC 明顯較弱,杏仁核與左側ECN 的FC 明顯增強,提示黃體晚期PMDD 患者在經前期調節負面情感的能力下降。由此可知,杏仁核相關腦網絡中的異常功能連接與PMDD 的情感障礙之間具有一定的聯系,但其腦區間對負性情感體驗的互相作用機制尚未明確,仍需更進一步研究探索。
由此可知,杏仁核是PMDD 患者情感功能調節的關鍵腦區,且由PFC-杏仁核構成的情感回路功能受損可能是PMDD重要的發病機制。
4 海馬
海馬體是邊緣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海馬接收來自海馬旁回、內嗅皮層和嗅周皮層的傳出神經,是情感控制邊緣回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與杏仁核、PFC 緊密的相互聯系反映了其在情感過程中的重要性[29,44]。杏仁核專門負責情感的輸入和處理,而海馬體對于情感記憶至關重要,在情感反應期間,這兩大腦區相互作用,將情感轉化為特定的結果[45-46]。由杏仁核、海馬、丘腦和腹側紋狀體組成的情感調控特定網絡與PMDD 負性情感的評價和表達密切相關[47]。PMDD 與海馬的腦結構和功能改變密切相關,通過對PMDD 灰質結構進行分析,發現PMDD 患者海馬皮質中的灰質密度顯著增加,這可能與PMDD 患者在黃體期對負性刺激的敏感識別和過激的情感反應有關[48]。在基因轉錄水平上對白香丹膠囊和氟西汀治療后及空白對照組的PMDD 模型大鼠分析海馬體中的基因表達譜,發現白香丹給藥組與對照組間具有基因的差異表達,這提示了白香丹治療PMDD 的可能以及海馬可能為PMDD 的病變機制的重要靶點[49]。一項對共病雙相情感障礙和PMDD(bipolar disorder with comorbid PMDD, BDPMDD)神經相關性的研究發現,BDPMDD 組的女性在月經周期中表現出更大的生物節律紊亂和更嚴重的亞閾值抑郁和焦慮癥狀,并且左側海馬體和右額葉皮層之間的FC增加[50]。
海馬是邊緣系統中情感處理的重要腦區,目前對于PMDD 與海馬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少且單一,但研究提示海馬與皮層區域之間的功能相互作用與負面情緒調節障礙有關,由此進一步開展以“PFC-杏仁核-海馬”為軸心的情感腦回路研究,將會為PMDD中樞病變機制研究提供潛在的神經病理學依據。
5 總結及展望
大量研究證實,情感功能障礙是PMDD 最主要癥狀表現,確定了其與PFC、ACC、杏仁核、海馬等相關腦區的功能改變密切相關,涉及PMDD 核心發病機制。目前PMDD 在相關的腦功能網絡研究取得了初步進展,尤其是fMRI 作為重要的神經影像評估手段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PMDD 的病理生理機制、診斷和治療等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影像學證據。在今后的研究中,以這些特定腦區為靶點,深入探索更細微的亞區結構的功能、連接關系與神經回路的綜合作用對情感障礙的調控機制,并在基于回路的神經生理學基礎上,為未來的治療策略提供新證據。
綜上所述,PMDD 的中樞機制尚未有明確定論,而本文僅對情感調節障礙的相關腦網絡功能進行分析,但PMDD 的病變機制不僅涉及中樞神經系統功能方面,還與其結構、激素、遞質以及基因等異常相關。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還須充分利用多種神經功能成像學技術、多模態影像等技術,對大腦分區進行更詳細的分析研究,建立更強大的神經功能模型,進而在PMDD 發病機制、精準診斷、治療和隨訪觀察等方面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通過整合大規模腦網絡結構、功能和分子神經影像學以及治療數據的研究,明確其神經調節機制,為臨床診治提供更精確有效的依據基礎,提高PMDD患者的生活質量。
作者利益沖突聲明:全體作者均聲明無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廖海設計本綜述的框架,對稿件重要內容進行了修改,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資助;陳思睿起草和撰寫稿件,獲取、分析本研究的綜述文獻;徐小雯、趙陽、肖磊、陳振宇獲取、分析本研究的數據,對稿件重要內容進行了修改;全體作者都同意最后的修改稿發表,都同意對本研究的所有方面負責,確保本研究的準確性和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