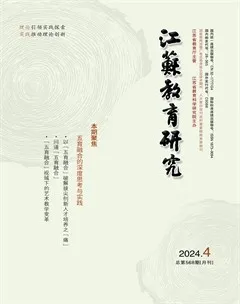從集團到共同體:集團化辦學的價值追尋與實踐探索
收稿日期:2024-03-05
作者簡介:李琳,南京市力學小學教育集團總校長,南京市力學小學黨總支書記,正高級教師,江蘇省特級教師。
摘要:集團化辦學是加快教育體制機制變革、推進基礎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的重要舉措。通過集團化辦學,可以構建教育共同體,有助于共建教育文化,提升集團校間凝聚力;能夠整合校際研究資源,推動教育研究成果的實踐轉化;能夠打造專業教師團隊,促進教師專業化發展;能夠遵循共享理念,尊重學生個性化發展的需要。南京市力學小學教育集團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回應社會關切,將集團校打造成學術共同體和成長共同體,通過文化熏陶、教科研引領、師生交流等多種形式,牢固樹立共同體的教育理念,打造一體化的高質量集團辦學格局。
關鍵詞: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集團化辦學;學術共同體;成長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G47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9094(2024)04-0036-06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教育,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發展素質教育,促進教育公平”,“加快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和城鄉一體化,優化區域教育資源配置”[1]。優質均衡發展是黨對義務教育辦學方向和目標的指引,為新時代基礎教育的高質量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集團化辦學是教育體制機制變革的新模式,各成員校在共同的辦學目標的引領下,合理配置人、財、物等教育資源,構建適切的組織結構及制度,促使集團化學校良性運營。集團化辦學既回應了黨和國家對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又符合學校建設和發展的根本需要。但集團校的建設不能僅停留在物質資源的集中上,還需要深入精神和文化層面,打造“教育共同體”。教育共同體能夠進一步釋放集團化辦學優勢,使教育資源從稀釋型輸送轉向積聚型規模化使用,激活集團每一所學校的內生辦學能力和活力。集團化辦學的理想境界,不僅要實現“一加一大于二”,而且最終應實現每個“一”通過集團化讓自己變得“大于一”,成為能夠不斷生長的活力“一”,實現共享共榮、共生共長。
一、集團化辦學背景下構建教育共同體的價值
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認為,“共同體”即“通過某種積極的關系而形成的群體,統一地對內對外發揮作用的一種結合關系,現實的和有機的生命組合”[2]。按照關系類型來區分,教育共同體包括文化共同體、教研共同體、師資共同體和生本共同體,分別關注集團整體發展、教師培養及學生成長。
(一)共建教育文化,提升成員校的凝聚力
教育共同體最大的特點就是關注發展中的人。人是一種精神的存在,這是人區別于其他非人類生命的道德優勢,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核心旨歸。教育是培養人、發展人、完善人的事業,是為國家培養建設者和接班人的公共事業,因而,教育集團區別于其他的企業和社會團體,強調對人的精神引領和情感熏陶。沒有精神和情感的教育集團,只能做到“集合”,無法做到“團結”。基礎教育實施集團化辦學,要更加強調教育指向人的根本特性,關注人作為精神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關注師生的成長和發展,關注教育行為相關者的利益訴求。
具有共同文化的教育集團中的各成員校不是基于某一研究課題或“因利而合、利盡而散”的臨時集合,而是具有共同的文化底蘊和情感基石的有機結合。教育集團的各成員校都有各自的辦學經歷,集團化的過程一定不是單個組織面對并遵守權力中心或上層指示的簡單過程,集團化發展的最終目的不應該也不需要構建“集權—從屬”的經營模式,而應該從無意識合作的選擇型和聚焦具體事務合作的聯盟型轉向共同文化作用下的高水平集團化辦學[3]。
為提升成員校之間的凝聚力,教育集團以及各學校的領導者和決策者應當有效利用校際共同文化打造教育共同體,使新的觀念與傳統的符號和結構要素進行創造性的結合,在文化建構的影響下發生質的改變。教育共同體能夠在原有集團化辦學的基礎上為教育集團賦予情感元素,打造集團校共有的文化標識和精神烙印。各成員校因共同的文化與情感確立共同的發展目標,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使匯聚在一起的師生不斷積聚發展的內生動力,形成發展的能量。
(二)整合校際資源,推動教育研究成果的實踐轉化
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要求教師不只是教書匠,而且是專業實踐者、課程研究者;教學不再是填鴨式灌輸,而是指向學科育人和核心素養培育。集團化辦學不應滿足于辦學規模的擴大,也不應一味追求教學硬件設施的建設,而是強調辦學品質的實質性提升。集團化辦學不僅能整合學校資源,實現多層次、多角度的教育研究,而且能將研究成果及時地在集團各成員校中推廣、應用,提高教育研究的影響力和有效性。課程與教學是學校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載體和抓手,也是彰顯學校獨特性的重要育人資源。打造教研共同體,開展課程與教學研究,有助于促進教育教學質量內涵式發展,使集團校的每一間教室都成為國家課程高質量實施的高地。
教育共同體中的教師既是理論研究的主體,也是實踐探索的主體。中小學教師的研究區別于高校的專職研究者,不僅在研究內容上基于教學實踐,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指向行動。教育共同體既能在研究資源層面給予教師最大限度的支持,使一項研究從多個成員校中獲得一手的數據,又能在研究成果推廣層面給予教師支持,使研究成果能夠在不同的教學境遇下獲得實踐檢驗。不同成員校的師資水平、生源質量、發展歷史等不盡相同,因此面臨著不同的實踐問題。教育共同體可以整合各成員校發展中的相同點和不同點,作為不同的案例供教師研究,從而更好地驗證教育理論,增強教育理論的說服力,推進教育理論創新。同時,一項教學改革或創新如果僅僅在某一環境下能夠發揮作用,是遠遠不夠的。教育共同體使教師的研究話語不再局限于某個班級、某個學校,而是能夠在整個集團中發揮效力,并通過不同的實踐檢驗研究成果的有效性。總而言之,教育共同體能夠使教師的理論研究與實踐反饋有機結合起來,把教育理論建立在教育實踐的基礎之上,最大化地啟發教師的實踐智慧,增強教師作為教育實踐者的理性自由,使其通過不斷的、多層次的、多角度的批判反思做出合理的教學實踐行為。
(三)打造專業教師團隊,促進教師專業化發展
學校建設的重點是培養人,不僅學生要得到發展,教師也應該實現專業成長,師生一起幸福成長是集團成為共同體的重要指征。教師是一所學校發展的核心。師資力量是人民群眾評價一所學校辦學質量的關鍵指標。優秀教師團隊的培養和建設,是集團化辦學的“牛鼻子”,也是辦人民滿意教育的核心追求,是實現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的根本保障。
“教師專業共同體是一個以學校為主要溝通方式的組織,通過合作討論和教學實踐學習,將信息反饋給團體,最終目的是實現集體進步。”[4]通過教師專業共同體的構建,教師能夠在交流與互促中完善知識建構、實現知識共享、提升效能感、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并生成學習動態環境[5]。作為教育共同體的集團校能夠建構名師領銜的師資共同體,更好地促進教師的專業化成長。好教師的培育須起于道德的成長。教育共同體能夠從集團層面培養一批師德高尚、熱愛教育事業、具有教育情懷的“四有好教師”,以此奠基集團師德精神底色。青年教師的發展指向當下,關涉未來,是集團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集團化辦學能夠集中優勢力量,以集團培育的名師為核心構建師資共同體,開拓青年教師的視野,給予青年教師更多的學習機會。師資共同體以青年教師的發展作為撬動教師隊伍整體建設的內生力量,整體規劃,系統建構,讓不同年齡段、不同專業段和職業成長期的所有教師都卷入其中,在共同的愿景、合作的文化、共享的機制、對話的氛圍中,促進全集團教師協同發展。
(四)遵循共享理念,關注個性化發展需求
集團化辦學的終極目標在于育人質量的全面提升。集團共同體的組成中,學生是人數最多的群體,也是最重要的受益人群。學生成長和人才培養是教育的終極目標。在集團化辦學背景下,各成員校學生也應深度融合,由“學校人”成為“集團人”,尋求無限的發展可能。從集團走向教育共同體,既遵循了“共享”的理念,也尊重了學生個性化成長和發展的需要。根據加德納的多元智力理論,每個學生在智力上的潛能分布是不同的[6]。為了激發學生身上極具個性化的潛能,學校要向他們提供差異化的教學,相應的,集團就必須為學校的差異發展提供發展空間。
“集團化辦學以一所名校為龍頭, 帶動區域內若干所學校共同發展,‘龍頭學校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足夠的支撐實力;‘拉郎配會導致‘削峰填谷,甚至會‘稀釋優質教育資源。”[7]教育共同體的建立就是在原有的集團化辦學的基礎上形成各校合作發展的新格局,尊重學生以及學校的不同發展需要,達成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局面。教學共同體強調的是合作,弱化了作為“集團”對統一的追求。教育共同體所遵循的辦學理念與學校管理文化,只是“影響”成員校的決策前提,并不替代或決定成員校的管理決策。教育共同體的文化理念是集團成員校的一種軟性的辦學資源,成員校要結合自身的辦學實踐來進行決策。教育共同體既使得集團的母體學校能夠輸出先進的理念、文化和管理方式,又使得各成員校有培育自己個性特色的空間,從而化零為整,平衡了集團化辦學統一要求與學生個性化發展的矛盾。
二、從集團到教育共同體的實踐探索
南京市力學小學教育集團(以下簡稱“力學集團”)從1999年成立以來,逐步發展形成南京市力學小學、南京市鳳凰花園城小學、南京市龍江小學、南京財經大學附屬小學、南京市復興小學、南京市力人學校(小學部)“一體六翼”集團化辦學共同體。在多年的辦學實踐中,培養人、成就人、發展人一直是集團化辦學的核心。力學集團始終強調共同體精神的引領,力爭以優質公平為追求,辦人民滿意的教育,促進教師和學生的創造性成長。
(一)文化共同體:從形式結合到精神共筑
集團化辦學是指“以行政指令為主,兼顧學校意愿,在某一所核心校牽頭組織下,區域內若干所學校依據共同的辦學理念和章程組建學校共同體(教育集團),在學校規劃、日常管理、課程建設、教師發展與學生培育等方面實現共享、互通、合作、共生,進而實現共同體內優質教育資源品牌的輻射推廣與合成再造”[8]。在集團化辦學的初期,雖然集團內部在學校規劃、日常管理、課程建設等領域實現了一致性,但是,教育集團的結合大多是制度引領下的形式化結合,缺乏共同的精神引領。
缺乏精神與情感引領的集團化辦學雖然在結構上形成了統一,卻難以實現集團化辦學的初衷。“集團化辦學的總體思路是通過政府行政干預,借力優勢資源校和優勢資源區的教育品牌和教育力量,改造并優化弱勢資源校和弱勢資源區的學校共同體。”[9]如果缺乏校與校之間的情感關聯,各成員校之間依然以自身的發展和利益作為辦學的優先考慮,則集團化辦學難以達成強校帶動弱校、校際均衡發展的目標。對優勢資源校來說,集團化辦學僅是政策影響下單方向的幫扶;對于弱勢資源校而言,集團化辦學僅是利用教育資源趕超其他成員校的途徑。各校雖屬同一集團,卻因價值導向不同,不能給集團的發展帶來持久動力。
構建教育共同體,能夠通過制度改善和價值引導,促使成員校在共同精神引領下協同均衡發展。以力學集團的辦學實踐為例,力學小學在創辦之初就奠定了基于學習本質特性的學校發展基調和辦學初心——“力學·報國”。將學習作為報效國家的基本途徑,強調學習知識的公共價值和原初意義。進入21世紀以來,“力學”校訓發展為“致力于學,學以成人”。之后,力學集團各成員校以該校訓為核心,在“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基礎上,形成了既具有歷史文化傳承,又凸顯社區資源和學校特色的精神標識。例如:南京市鳳凰花園城小學的“力學·尚綠”,南京市龍江小學的“力學·樂活”,南京財經大學附屬小學的“力學·力行”,南京市復興小學的“力學·美行”,南京市力人學校(小學部)的“力學·力人”。以“力學”為集團精神統領,“尚綠”“樂活”“力行”“美行”“力人”架構起綠色持續、身心協同、知行合一、向美從善、學以成人的教育共同體文化生態。集團校共有“力學”教育文化理念,在共同體內形成了一種對教育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共同理解[10]。在“統一+自主”的模式下,集團各成員校在融合中逐步實現集體認同,達到共享自治,實現了學校德育工作、管理工作和教科研工作的常態交往和日常互動,激發了集團校文化內生活力,各成員校共同打造力學集團的教育品牌。
(二)教研共同體:從分散課題到以研促教
在名校集團化辦學的過程中,很多人擔心名校這杯“牛奶”被稀釋,從而使原有名校的“含金量”降低。在集團化辦學的基礎上如何保證名校的教育教學質量,以優質學校帶動普通學校發展,就要回歸到教育集團的資源配置與互通問題。
集團化辦學的目的是使教育資源優質均衡配置。但是目前的教育集團因體量不同、中心校輻射力度不同、發展水平不同、社會認可度不一等原因,大多還存在一定的發展差異。教育資源均衡配置不是將辦學資源在集團學校之間進行簡單置換,甚至只從優質學校流向薄弱學校,而是構建教研共同體,依托教育、教學研究,將集團凝聚成各成員校可以相互借鑒、取長補短、共同進步的整體。
集團內各成員校的原有課題以各校為生長點,缺乏廣泛的調研和實踐轉化。教研共同體使中心校帶動成員校,既保證原有課題成果順利落地,又為課題的發展帶來新的生機。集團中心校發揮核心作用,可以用自己成功的辦學經驗帶動其他學校發展,還可以通過集團化辦學來檢驗、優化和完善成熟的辦學經驗。在教育共同體內,中心校并不直接輸出現成的教育科研項目成果,而是融合各校的原有研究成果,通過現場觀摩、深度參與、沉浸體驗課題研究過程的活動研討、課例展示,打造“學校主課題+教師子課題+學生小課題”全學段、全學科、全員性、卷入式教科研模式。力學集團通過共學共研、學術資源共享等方式,積極構建學術研究共同體。集團學術期刊《等你·讀吧——教育前沿學術研究速遞》收錄教育領域最前沿的學術研究、前沿理念和創新實踐,為教育共同體內各校的教科研提供統一的理論指導。在學術研究共同體的構建過程中,集團定期舉行讀書會,鼓勵多層次的學術交流與合作。集團校長中心組、行政領導學習團隊以及全集團教師讀書團隊共同參與,分享學術研究成果,啟迪創新思維。此外,教育共同體內部還舉行集團論文報告會、“力學杯”優秀論文評選以及學術論壇等活動,督促教科研成果的轉化和推廣。同時,教研共同體中的各成員校學習借鑒科研的方法路徑,確立自己的課題,研究自己的項目,形成自己的成果,“培植根”而非“嫁接枝”,探尋科研提升學校內涵質量的深層原因和過程機理。教育共同體通過教科研引領實現了集團化辦學“優質”和“均衡”的雙贏。教育共同體集中發力、集智攻關,打造集團總課題項目“集團大腦”,從“火車頭牽引模式”向“動車組管理模式”轉型,讓集團從集結走向了真正意義的教育共同體。
(三)師資共同體:從“偏安一隅”到流動共生
教師資源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是集團化辦學中難以共享的辦學資源。但是,優秀教師的教學經驗卻是能夠共享的。構建師資共同體,使優秀教師的教學經驗得到更有質量的提煉、更大規模的檢驗,從而將個人經驗轉化為集體經驗。同時,教育共同體能夠打破教師固化在某一個學段、某一個校區、某一個崗位的限制,通過角色身份的轉換,學段、崗位的流動和跨越,激發教師隊伍整體活力。
如果教育集團能夠升華為教育共同體,以全體教師作為共同體的辦學資源,以全體學生作為共同體的育人對象,就能打通不同成員校間教師流動的通路。教師的流動使來自不同成員校的教師分析各自的教學經驗,打破彼此的舒適區。這種流動不應停留在受益學生群體的輪換,而要走向優秀教師教學經驗的提煉與推廣,進而促進教育集團學校之間的共同生長,使專家型教師的經驗得以推廣,新手教師在更復雜的情況下能夠迅速成長。因此,如何發現、提煉、推廣優秀教學經驗,把優秀的教學經驗轉變成學校的辦學制度與教學流程,成為打造教育共同體的關鍵和挑戰。力學集團凝心聚力打造“三位一體”的師資共同體,即“師德成長共同體、教學互動共同體、教師協作共同體”,通過師德培育、集體共研和協同育人實現了教師的流動共生。以“師德成長共同體”為例,集團打造了展現師德魅力的師德報告會,以榜樣的力量鑄就愛國報國精神底色,播種力學仁愛師德師風。報告會上有一生堅守講臺的老教師,有一群愿意一輩子做孩子王的班主任老師,還有“十年磨一劍”的主課題攻關團隊……優秀教師的教育人生打動、感染、激勵、鼓舞著每一位集團教師。
(四)生本共同體:從封閉發展到集體共育
學生的流動和交互是集團化辦學的一大難點。即使學校能通過制度、獎勵機制等保障教師在集團內部流動,也很難在社會輿論壓力、家長擇校偏好、流動安全隱患等問題中找到學生在集團內流動的最優解。教育共同體能夠在保留學生原有學位的情況下,通過教師間的流動與教學經驗的共享打破成員校之間的壁壘,使學生即使不流動到其他學校,也能在教育集團內實現全面發展。教師的流動并不只是教師工作地點的變動,必然帶來教學經驗、教學理念、教學風格、教學智慧等在成員校之間的流動。教師間的交流勢必帶動學生間的交流,使不同成員校的學生以教師交流為載體不斷拓寬眼界、認識自我與他人,形成生本共同體。生本共同體內的學生不再是歸屬于某一成員校的學生,而是歸屬于集團的學生。生本共同體給學生帶來更廣闊的資源和舞臺,支持學生的個性化發展需要。力學集團通過“活動融合、課程融合、資源融合”三大融合讓集團所有學生深度交互、交流、交融,讓學生成為“集團人”。集團通過“小先生開講”“小先生講解團”以及“小學生—小先生—大先生”的成長機制,為學生的創造性成長賦能。以“小先生開講”為例,教育共同體內的學生跨校、跑班、走課研學,以兒童研究素養為核心打造由跨校學生組成的兒童研究團。集團校小先生們帶著自己的各門學科學習的小研究成果,跨越校區、年級,進行研學巡講,以此帶動集團各校學生展示自我、自主學習、主動成長、與伙伴共成長,構建童年生長新樣態。
參考文獻: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EB/OL].(2022-10-25)[2024-01-23].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2]林上洪.“教育共同體”芻議[J].教育學術月刊,2009(10):20.
[3]張爽.基礎教育集團化辦學的模式研究[J].教育研究,2017(6):90.
[4]馬晴晴.教師身份認同困境的表征、機制與出路[J].教學與管理,2023(36):14.
[5]時長江,陳仁濤,羅許成.專業學習共同體與教師合作文化[J].教育發展研究,2007(22):79.
[6]周彬.“名校集團化”辦學模式初探[J].教育發展研究,2005(16):86.
[7]鐘秉林.關于基礎教育集團化辦學的若干思考[J].中國教育學刊,2017(12):3.
[8]樓蓓芳.集團化辦學背景下的跨校聯組教研機制研究[J].教育,2024(2):15.
[9]孟繁華,張蕾,佘勇.試論我國基礎教育集團化辦學的三大模式[J].教育研究,2016(10): 44.
[10]齊格蒙特·鮑曼.共同體[M].歐陽景根,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7.
責任編輯:殷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