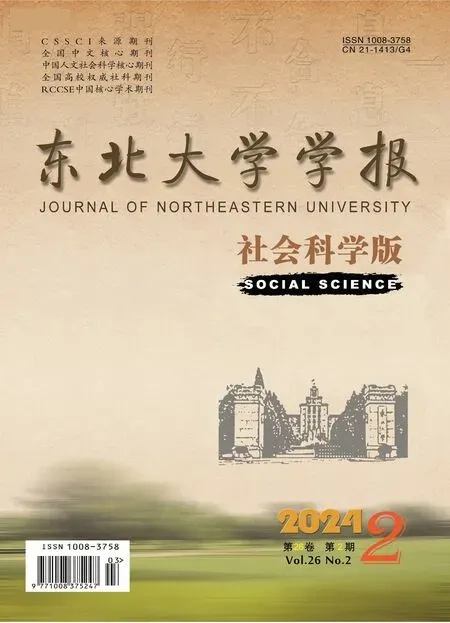《詩經》風詩敘事及其傳統
——《詩經》研讀筆記之二
董 乃 斌
(上海大學 文學院,上海 200444)
一、《詩經》風詩的敘事
研究《詩經》,除了其文本以外,可以利用的成果可謂汗牛充棟。從漢人開啟到此后歷代學者的注疏、專著,不勝枚舉(1)參見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現在除了許多單本的專著外,又有了一些注疏和研究著作的匯編本,如魯洪生主編的《詩經集校集注集評》、黃霖等主編的《詩經匯評》等等。
此外,多種文學史著作的《詩經》部分也是重要參考資料,因為它們綜合而又精簡地展示了《詩經》的研究成果,對《詩經》的內容、思想藝術、文學史地位等都有簡明扼要的闡述。
我們現在關注《詩經》風詩的敘事問題,首先要問風詩究竟涉及哪些事情,接著要問風詩是怎樣敘述這些事情的、有些什么特點、是否形成某種傳統等等。前人論述對此曾多有涉及,雖各有短長,均很有參考價值,當然最根本、最重要的還是《詩經》文本自身。這是我們的入手處,也是著力處。
《詩經》風詩,舊稱十五國風,總計160首。統觀這160首詩,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內容,也可以說風詩寫了四個方面的事情:第一是戀愛家庭;第二是農事生產;第三是戰爭徭役;第四是對統治者的美刺。這四大類包括不進去的,暫列為其他,數量僅占全部風詩的十分之一,涉及社會生活和心理的各方面,但數量稀少(2)有的文學史概括《詩經》內容,大分為六類:(1)祭祖頌歌和周族史詩;(2)農事;(3)燕饗;(4)怨刺;(5)戰爭徭役;(6)婚姻愛情。(見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一卷第一編先秦文學第二章《詩經》之第二節)其中一、三兩類內容在雅頌中,其余四類見于風詩。我們采用了這種說法,在具體介紹時按作品的多少排次并按實際情況對提法略做修改。。
戀愛婚姻家庭是風詩寫得最多的內容,全部風詩的一半以上屬于這個部分。
茲列舉篇目如下:
《關雎》《樛木》《螽斯》《漢廣》(周南)
《鵲巢》《草蟲》《行露》《殷其雷》《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何彼襛矣》(召南)
《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凱風》《雄雉》《匏有苦葉》《谷風》《旄丘》《簡兮》《泉水》《靜女》(邶風)
《柏舟》《桑中》《蝃蝀》(鄘風)
《考槃》《碩人》《氓》《竹竿》《芄蘭》《伯兮》《有狐》《木瓜》(衛風)
《中谷有蓷》《采葛》《大車》《丘中有麻》(王風)
《緇衣》《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遵大路》《女曰雞鳴》《有女同車》《上有扶蘇》《萚兮》《狡童》《搴裳》《豐》《東門之墠》《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鄭風)
《雞鳴》《著》《東方之日》《甫田》(齊風)
《椒聊》《綢繆》《有杕之杜》《葛生》(唐風)
《蒹葭》《晨風》(秦風)
《宛丘》《東門之枌》《衡門》《東門之池》《東門之揚》《防有鵲巢》《日出》《澤陂》(陳風)
《素冠》《隰有萇楚》(檜風)
《候人》(曹風)
《伐柯》《九罭》(豳風)
以上82首均屬婚戀家庭題材,除了婚戀,還包括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故數量甚多。除《魏風》缺席外,其余十四國風均有分布,而以邶、鄘、衛與鄭風為多。這顯示出此類詩歌反映的是《詩經》時代社會生活最重要的內容,也是民間歌謠最喜表現的方面。這些詩的主人公多半是女子,多以女子視角、女性口吻敘述,而所表現的感情則悲歡離合、喜怒哀樂俱全。《詩經》風詩的敘事因素,在此類詩中表現得集中而突出,像《邶風·谷風》《衛風·氓》雖抒情色彩極濃卻已相當接近敘事詩,其余所有作品的抒敘結合也均達到上佳水平。此類詩篇的數量居于風詩之首。
農事生產也是《詩經》時代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但《詩經》風詩中對之做正面敘述描寫的作品,其實不算太多,總共只有7首,就數量而言,只能算是風詩的殿尾。其篇目有《葛覃》《芣苢》(周南)、《采蘩》《采蘋》《騶虞》(召南)、《十畝之間》(魏風)、《七月》(豳風)。
雖然數量少,但僅《豳風·七月》一首即可一以當十百,其長度、所涉具體內容、寫法和總體分量足以與《大雅》的《生民》《公劉》《綿》等史詩相頡頏和媲美,使其在《詩經》整體中占據重要地位。從詩歌敘事的角度來看,《七月》也是極典型的代表作。
另兩類內容的作品,在《詩經》中分量比較接近,也都是《詩經》風詩的重要內容。那就是百姓美刺統治者的32首和戰爭徭役題材的21首。美刺類中,實以怨刺為主,美、刺之比是1∶3。若將戰爭徭役類中怨刺為主的詩篇加上,那么對統治者不滿的諷刺之詩數量就更多,這也是風詩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
下面仍列出各類的篇目,以方便討論。
贊美統治者的有《麟之沚》(周南)、《甘棠》(召南)、《定之方中》《干旄》(鄘風)、《淇奧》(衛風)、《羔裘》(鄭風)、《車鄰》《駟驖》(秦風)等8首。
諷刺鞭撻統治者的有《羔羊》(召南)、《新臺》《二子乘舟》(邶風)、《墻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相鼠》《載馳》(鄘風)、《黍離》(王風)、《南山》《敝笱》《載驅》(齊風)、《碩鼠》《汾沮洳》(魏風)、《揚之水》(唐風)、《終南》《黃鳥》《權輿》(秦風)、《墓門》《株林》(陳風)、《羔裘》(檜風)、《鸤鳩》《下泉》(曹風)、《狼跋》(豳風)等24首。
刺詩明顯多于美詩,敘事色彩也以刺詩較為鮮明,涉及階級矛盾、貧富懸殊和反抗意識的內容,這類內容歷來在一般文學史著作中都受到重視。
反映戰爭徭役的作品有21首,其中有少量凱旋之歌,更多的是戰爭徭役重壓下抒發悲苦傷痛之情的怨刺之歌。具體篇目有《卷耳》《兔罝》《汝墳》(周南)、《小星》(召南)、《擊鼓》《式微》《北門》《北風》(邶風)、《河廣》(衛風)、《君子于役》《揚之水》《兔爰》(王風)、《清人》(鄭風)、《東方未明》(齊風)、《陟岵》《伐檀》(魏風)、《鴇羽》(唐風)、《小戎》《無衣》(秦風)、《東山》《破斧》(豳風)。
最后是18首難以分入以上各類的作品。如同情孤獨者的《衛風·有狐》《唐風·杕杜》、贊美樂師舞者的《王風·君子陽陽》、流亡者之歌《王風·葛藟》、獵人射手之歌《齊風》的《還》《盧令》《猗嗟》(這三首似可列入農事生產,但較勉強)。還有《魏風》中憤于社會不公、憂慮時事的《葛屨》《園有桃》,《唐風》中嘆息時光流逝、諷刺吝嗇、批判傲慢、勸勿信讒、睹物思人的《蟋蟀》《山有樞》《羔裘》《采苓》《無衣》,以及外甥送舅的《秦風·渭陽》、書寫游子鄉愁與悲慨人生的《檜風·匪風》《曹風·蜉蝣》,乃至托物寄情的禽言詩《豳風·鴟鸮》,等等。這些作品的存在,說明風詩內容的豐富性。
對于風詩,也可按別的標準劃分組合,比如將怨恨諷刺統治者劃為一類,則上述戰爭徭役與怨刺統治者兩類便可歸并,以鞭撻怨刺統治者為標題。這樣做,亦有其合理方便之處。
此外,若對詩篇內容的理解、闡釋有分歧,則各詩分類位置亦會不同,此中爭議不可免。為討論方便,以上姑作試分,大體如是而已,盡可商榷調整。
上面將《詩經》風詩所涉之事,按我們的理解做了大致歸類,即婚戀家庭、美刺統治者、戰爭徭役、農事生產。這既是《詩經》風詩的四大內容,也是《詩經》風詩所敘事情的四大方面。這些事情都是各篇風詩所敘述的,雖然各篇的敘述方式、抒敘二者的含量分配有所不同,但它們都是一種敘述文本,只有通過詩人(作者)和事件中人物的敘述,讀者才能了解到其中的種種事情(3)中國詩歌,以《詩經》作品為代表,都可以稱作“敘述文本”,與西方文論習慣所分的“抒情文本”“敘事文本”“戲劇文本”不同。敘述文本是包含著抒情成分和敘事成分的綜合性文本,其抒敘結構則需要分析。。歷代研究者之所以對風詩文本有此基本共識,具體解說雖有小異,但大體方向并無捍格,關鍵在于風詩所敘、所涉之事的確就是這些內容。根據文本,人們從“事”與“情”兩方面對它們做出說明,結果大致便只能如此。
我們再讀前人對《詩經》風詩敘事的解說,又發現這些詩所反映和表現的內容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其事與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相聯系;一種則僅與無名大眾相聯系。因此,前者與歷史記載有關,其本事于史有證,可以考訂印證,可以比較切實地“詩史互證”。當然,因所指具體,也容易見仁見智而有所分歧。后者雖也是歷史(社會)生活的反映,但無本事可考,詩的史性弱于前者,對之施行詩史互證,只能在時代氛圍、社會心理或歷史趨勢等較大較籠統的層面進行。對于詩歌敘事學研究來說,這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作品,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是有差異的。我們擬分別討論之。
二、風詩與詩外之事
在風詩的上述四大內容中,美刺統治者一類里有較多與歷史人物相關的作品,《召南·甘棠》頌念召公仁政,《衛風·淇奧》頌美君子人格,據說指的是衛武公,《鄘風》的《定之方中》《干旄》贊美衛文公復興強國的事跡等。這類作品不多,多的是怨刺之詩。
如《邶風·新臺》和《鄘風》的《墻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是一組諷刺衛宣公及其后人荒淫亂國的歷史。相傳許穆夫人所作的《載馳》(屬鄘風),也與之有關(4)何楷的《詩經世本古意》認為《邶風·泉水》《衛風·竹竿》也是許穆夫人作品,魏源《詩古微》亦持此說。《詩經原始》和《詩經通論》中懷疑是許穆夫人妾媵所作。。
從《詩序》《毛傳》起,歷代研究者基本無異詞,認為這些詩對應于《左傳》的紀事以及衛國后續諸君的更替變換:
(桓公十六年)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取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5)《春秋左傳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758頁。
(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于熒(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6)《春秋左傳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787—1788頁。
司馬遷《史記·衛康叔世家》據《左傳》梳理敘述此段歷史,與上述諸詩有關的人物主要有衛宣公、伋(急子)、頑(昭伯)、宣姜、子壽、子朔(惠公)、戴公(名申)、文公(名燬)、許穆夫人等。
這里與詩篇有關的基本情節是:衛宣公為太子伋娶齊女為妻,見女美,乃于河上筑新臺,奪媳為妻,是為宣姜,生子壽、子朔。宣姜、子朔讒害太子伋,宣公亦欲廢太子,乃令伋出使齊國,安排殺手在界上伏擊。子壽獲悉陰謀,追救伋,被誤殺。伋后到,亦被殺。宣公卒,子朔立,為惠公。齊國強迫宣公另一子頑(昭伯)與宣姜同居,生三子二女。此后衛國動亂多年,國弱,以致被狄人滅亡。宋桓公接濟衛之難民,并立戴公為衛君。許穆夫人(頑與宣姜所生次女)亦欲前往奔唁,并為衛謀劃,受到許國大夫阻撓,心情激憤,乃作《載馳》。后在齊國幫助下,衛得以復國,戴公卒后,文公繼立。
以上簡述的情節是從史書得來的。《詩經》風詩的研究者以之為《新臺》《墻有茨》諸詩的本事。如《邶風·新臺》的《小序》云:“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的《小序》云:“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鄘風》的《墻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諸詩和《小序》《毛傳》也這樣敘述。《載馳》作者因有《左傳》明言,當然更無疑義。朱熹在《詩集傳》中對《小序》《毛傳》似不盡信,但仍稱其為“舊說”,并特地聲明:“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于詩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7)朱熹集注:《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27頁。總之,前人就這樣將風詩與史事聯系了起來。但正如朱熹所言,這些史事僅憑詩歌文本是無法考實的。
《新臺》詩云:“新臺有泚,河水彌彌。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新臺有灑,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漁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從詩的字面,看不出衛宣公奪媳為妻故事。籧篨,據朱熹注,本意是指竹席,人或編以為囷,其狀如人之臃腫不能俯仰,故借以比喻丑陋的形象(如雞胸、駝背之類)。戚施,朱注曰:“不能仰,亦丑疾也。”聞一多則認為“籧篨”與“戚施”都是癩蛤蟆一類丑物(8)參見聞一多:《天問釋天》《詩新臺鴻字說》,《聞一多全集》第二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2年。。燕婉之求,本想得到個理想的人,不想來了個丑怪物,真是事與愿違。詩中再三言之,可見大有切膚之痛。但如僅看詩內,其題旨便只能如高亨所說:“詩意只是寫一個女子想嫁一個美男子,而卻配了一個丑丈夫。”如此而已。可是如果考慮到此詩屬于《邶風》,邶、鄘、衛三風所寫皆為衛國衛地之人事,而其創作時限則在衛國被狄人滅亡之前(《載馳》才涉及衛亡),題曰《新臺》,與衛宣公在河上筑“新臺”以迎娶齊女事正合,故《毛傳》所云能夠得到公認。從《詩序》《毛傳》《鄭箋》《孔疏》到唐、宋至清與現代的《詩經》研究注釋者,如蘇轍、姚際恒、方玉潤、高亨、程俊英等均同意此說,看來并非無理。
就《新臺》詩而言,《毛傳》指出的《左傳》所載之有關史事,對于解讀詩意、說明詩旨是非常有用的資料,甚至可說是不可或缺的參證。雖然這些史實并未具體表現于詩內——詩的字面并未寫到,即并未直賦這些事——按其實際地位,它們應該稱為“詩外之事”。但這個“詩外之事”對于詩歌的解讀和敘事分析卻十分重要,應視為作品敘事之有機組成部分。
當然,絕非隨便找點什么歷史記載就可以充當這個“詩外之事”。“詩史互證”既有其成立的合理性,也存在發生錯誤的可能,故必須嚴肅縝密,使之可信可靠,才能具有說服力,并且應當允許質疑討論和證偽的可能。而一旦認定此事與作品確實有關,就不僅可將其作為詩歌創作的背景,甚至不妨將其當成詩歌內容的一部分,在對其做敘事分析時予以充分利用。
“詩史互證”可以說是《詩序》和《毛傳》的核心概念和基本方法,在此基礎上說本事、解詩意、揭題旨、析作法,可以說是《毛傳》對《詩經》研究的重大貢獻,也是后人研究《詩經》的一般思路和軌范。雖然陸續有人發現《詩序》《毛傳》觀點有牽強附會、說服力不強之處,但總體說來還是不能完全否定,只能零星具體地商榷或另立新說。在論《詩經》史詩時,《詩序》《毛傳》的價值已充分顯示,現在論風詩,又獲得再次證明。
既已發現并確信詩歌內容與某些詩外之事有關,古人自然據以闡釋詩篇。他們雖無敘事學之名,但實際操作有時卻暗合其理。如《毛傳》謂《新臺》系國人厭惡衛宣公奪媳為妻之事,故作此詩諷刺,將詩的內容與史實做了明確聯系,并認定此詩為衛國人所作,奠定了闡釋詩意的基礎。朱熹更具體論此詩為“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丑惡之人也”。沿此思路可知,《新臺》詩描述的主人公乃是初嫁衛國的齊女,詩的敘述者以齊女視角觀察感受,以齊女口吻敘述抒懷,詩面略過事實,直訴對婚姻對象的極端憎惡,狠狠諷刺咒罵了衛宣公其人其行,這種闡釋一直傳承至今(9)值得注意的是,《新臺》女主人公是無法掌握自身命運的古代女性、無辜的受害者,該被同情。但她后來成了宣姜,衛宣公死后又與宣公次子頑(昭伯)同居(據《左傳》記載,此事與齊國唆使誘迫有關,或與當時父死子繼的婚制有關),成了衛公室亂倫荒淫的參與者,也成了《墻有茨》諸詩的諷刺對象。古今之人不齒于此,今人更從階級意識批判之,皆無可厚非,但宣姜作為一個女性的不幸卻很少被考慮。請參閱黃霖主編:《詩經匯評》上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第118—121頁。。
《新臺》是一首本事可考的風詩,但具體本事在詩外(只能算是此詩的背景),詩歌所表現的不是有關的故事(即所賦非故事),而是故事女主人公的一腔怨恨之情(即所賦為情感)。因此,這是一首抒情詩、一首包含敘事因素的抒情詩,確切地說,是一首詠事詩。在詩與事關系密切程度的等級(含事、詠事、述事、演事)上,可列第二級(10)關于詩與事關系疏密遠近的不同及其區分,請參閱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后世的詠史詩與之有一脈相承的關系。
這種情況在《詩經》風詩中相當普遍。《邶風·新臺》頗為典型,且無意見分歧。但像《邶風·二子乘舟》,詩面僅有掛念遠行者之意,《毛傳》引《左傳》桓公十六年事為說,解為“思伋、壽也”,就有很多人并不相信。
《鄘風》的《墻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情況與《新臺》相同。當初產生時是對社會現象的諷喻,后世看來,則為詠史。這三首詩也是以衛公室故事為背景的抒情詩。由于“詩史互證”法的局限(不確定性帶來證偽的可能),以及“不淑”一詞的不同理解(不善抑或不幸),《君子偕老》的題旨就有多種說法。
《齊風》的《南山》《敝笱》《載驅》諷刺齊襄公亂倫荒淫,魯桓公未能采取有力措施阻止,以致被害,后來魯莊公亦未能防閑其母。此事見于《左傳》桓十八年、莊二年的記述(齊襄公與嫁給魯桓公的妹妹文姜私通,并因此而謀殺了魯桓公。魯莊公繼位后,未能設法阻止,文姜繼續與齊襄公晤會)。
《秦風·黃鳥》的有關史實見于《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司馬遷《史記》也有記錄。
《陳風》的《墓門》《株林》二詩分別與陳國的君主桓公、靈公相關。《左傳》桓公五年載,陳桓公之弟佗,殺太子自立為君,國人因之作《墓門》,批評陳桓公不能早除陳佗。《左傳》宣公九、十年載,陳靈公及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夏姬(大夫夏御叔之妻)淫亂,夏姬之子夏征舒殺靈公自立,楚出兵誅夏征舒,立靈公之子,是為陳成公。
以上諸詩所詠之事皆有歷史文獻可考,涉及的人物有名有姓。但這些詩歌本身并不是直接敘述其中某個歷史事件,而多是以其事為背景而發表議論或抒發情感的。對這些詩歌進行敘事分析,離不了“詩史互證”和從史籍考證所得的“詩外之事”,也離不了讀者(研究者)將詩面內容與詩外之事通過充分聯想所進行的綜合分析。在這里必會產生不同意見,所以為證偽留有余地是必要的。
《邶風·擊鼓》是一首記有歷史人物名字、詩內詩外敘事均頗分明的作品。詩中提到的孫子仲,即公孫文仲,字子仲,其生活年代與州吁同時。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11)朱熹集注:《詩集傳》,第18—19頁。
此詩的“詩外之事”即背景,是篡權的衛公子州吁聯合陳、宋、蔡三國伐鄭(見《左傳》隱公四年)的戰爭。孫子仲是衛國的統帥。此詩以衛國一個兵士第一人稱敘述口吻出之。首章敘擊鼓出征,二章敘戰而無歸,三章敘戰爭失利,四章敘危境思妻,五章敘悲哀嘆息。全詩從擊鼓出征起,寫出一個時空轉換與心緒波動的過程,雖概括精簡卻非常具體:別人守土,我則隨軍出征不得回家。戰爭失利,生死難卜,危難中想到妻子,想到當年與她的誓約。“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堪稱神來之筆,令人如聞如見。現在愿望落空,使我孤獨,也使我失信!詩內所述如立體畫面,征人及其妻遙思而無奈之情滿溢紙上。《擊鼓》可謂詩內外之事呼應增色、詩歌含義豐茂的典范。
三、抒情詩的敘事分析
《詩經》風詩還有更多是無法與具體歷史人物聯系的作品,對這些詩歌進行敘事分析,基本上只能利用詩面的文字。
有的作品敘事色彩鮮明,如《邶風·谷風》《衛風·氓》和《鄭風》的《將仲子》《女曰雞鳴》之類,雖長短不一,但詩內之事寫得生動明晰,已略具敘事詩性質。《谷風》《氓》是兩位棄婦在娓娓訴說婚姻的變故;《將仲子》表現男女的熱戀,有活潑的行動和親昵的話語;《女曰雞鳴》則是新婚夫婦家常生活一景,既現實又充滿憧憬。這些篇章不但有順時或逆、倒、追、補諸式的敘事,還有人物語言和戲劇性場面的展示,敘述內容的多面多層及由之而來的豐富含義,均非常值得注意。
《詩經》風詩的敘事常常是與抒情(含議論感慨)成分的溶滲結合。文學敘事無不含情,或者說,文學中本沒有無情的敘述。同樣,世上沒有憑空而來、與事無關的情,詩之抒情亦必含敘甚至有賴于敘。當然,為藝術之委婉含蓄,詩歌往往將所因與欲敘之事置于暗處、隱處、遠處,而以抒情感慨議論為詩之明面、近景、主聲。這種含事之詩往往給人專在抒情言志的表象,敘事一翼遂易于有意無意間遭到忽視。中國詩歌被籠統稱為抒情詩,以為中國詩歌只有一個抒情傳統,今日我們則要糾正這種誤解和偏頗,對抒情詩做一番重新審視和分析:一是要探尋揭示其中的敘事因素;二是要分析它們的抒敘結構;三是要論證其與抒敘傳統的關系。總之,是要發揮讀者參與的能動性,運用敘事視角來看抒情詩,以發現詩歌中那些被“抒情傳統唯一”的偏見遮蔽的現象與表現,而以“抒敘兩大傳統貫穿”的觀點取代“抒情傳統唯一”的觀點,并努力使之成為文藝理論和文學史知識中的共識乃至常識。
探尋詩篇的敘事因素,一般可從敘述視角(人稱)入手。以前的習慣性認識是對抒情詩的作者、抒情人、敘述者和作品主人公不做區分,而將其渾然等同,將抒情詩內容簡單地看作作者本人的真實自白(12)不是沒有人對此持懷疑態度,如錢鍾書先生就曾多次強調詩歌創作的虛構性和語言的修辭特征,指出詩語的不可盡信。但舊習影響很深,說詩者仍不時陷入泥淖。。而從敘事學引進敘述視角的概念,則可改善這種粗疏囫圇的弊病。
風詩的敘述視角至少有兩種:一是第三人稱敘述;一是第一人稱敘述。
第三人稱敘述,主要由賦體構成,亦可稱賦體敘事,其特點是敘述的客觀性,作者與敘述者、抒情人有別,詩歌敘述的基本上是他人故事,而并非自己之事。如《關雎》,雖用興法開篇并連綴,所興亦是作者之所見,敘述者實處于客觀地位。詩中“寤寐思之”“輾轉反側”是對君子行為的描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云云,則是擬君子之思與言。《葛覃》第三章有“薄污我私”“薄浣我衣”之句,但前兩章造成的總體印象客觀性頗強,仍不妨為第三人稱敘事。《卷耳》首章即云“嗟我懷人,置彼周行”,直到末章“我馬瘏矣”“我仆痡矣”,都是“我”在敘述,那是典型的第一人稱敘事,或稱獨白敘事。這兩種敘事占了風詩敘事的絕大部分。
屬于第三人稱敘述的,如《周南》的《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漢廣》《麟之沚》,《召南》的《鵲巢》《采蘩》《采蘋》《甘棠》《羔羊》《野有死麕》《何彼秾矣》《騶虞》,《邶風》的《凱風》《式微》《旄丘》《簡兮》《新臺》《二子乘舟》等皆是。
而《召南》的《草蟲》《行露》《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邶風》的《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擊鼓》《雄雉》《谷風》《泉水》《北門》《北風》《靜女》等,則均是第一人稱敘述。
第一人稱敘事的極致是獨白敘事,即全詩每句話都是主人公自己在敘述,猶如戲劇中的獨白,而詩人(作者)則如劇作家一樣隱身幕后。除上舉《鄭風·將仲子》在語言表達上是獨白敘事,《魏風·碩鼠》也很典型。此外實例尚多,大抵未明寫背景、場合而能靠抒情人獨白見出事情者皆是。
由上可知,區分風詩的敘述人稱,主要看其敘述是“有我”還是“無我”,有我為第一人稱,無我多為第三人稱,無論何種人稱,敘述事情都是一致的,區別僅在具體事件之隱顯而已。讀者同時需要體會琢磨詩歌敘述的語感。有的獨白是真的自說自話,無須受述者,僅訴諸內心。有的獨白則不然,說者雖是獨白,但實有確定的受述者,此人雖未出場,但卻是重要的存在,如《鄭風·將仲子》詩中的青年仲子,《碩鼠》詩中貪婪無度的巨鼠。述者與受述者共同構成一個敘事場,二者在詩中的存在雖有隱顯明暗之別,但卻是相互依賴的關系。
區分人稱的目的在于判斷敘述的視角,分辨詩歌的敘述者、抒情人和故事主人公。比起小說的敘事視角,詩歌可能較為簡單,但也不能把詩歌的作者與抒情人、敘述者乃至主人公完全畫等號。詩歌的敘述視角也是有變化的,而這對理解詩意和題旨關系重大,故應細心分辨,不可忽略或籠統視之。
這里再舉《豳風·東山》一詩,說明人稱、視角的變化以及讀者對此理解的不同對詩意解說的影響。其詩四章,每章十二句,原文如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戶。町畽鹿場,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耀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13)朱熹集注:《詩集傳》,第94—95頁。
《豳風·東山》是《詩經》風詩中創作年代較早的作品,應是作于西周,周公東征平定管叔、蔡叔與武庚之亂以后。《詩序》說:“《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這是認為《東山》系周大夫所作,主題是贊美周公東征及其慰勞歸士之舉。后更有人干脆將詩的作者直接定為周公本人,如朱熹謂“成王既得《鴟鸮》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明確將《東山》解為周公之詞。看法類似的尚有王質、戴溪、嚴粲諸人,當然后代持不同觀點的研究者亦甚多。
其實,詩作者是誰并不重要,也很難真正弄清并證實,關鍵是要對作者與詩的敘述者/抒情人加以區分。即使《東山》一詩的作者真是周公或周公麾下的大夫,但從活躍于詩中的人物,從這個人物的所為、所思視之,其敘述者/抒情人都應該是作者的代言人,詩中頻繁出現的“我”應該是東征軍的一位將士,這樣才能把全詩講通、講順、講深。如果做了這樣的區分,整個詩的意義和題旨也會產生不小的差異。古代有些解詩者,自覺不自覺地站在禮教立場,強調此詩的政治意義。從假托孔子所言“于《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孔叢子·記義》)到《詩序》所謂“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悅)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到朱熹引述《詩序》后的發揮——“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于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愿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14)朱熹集注:《詩集傳》,第95—96頁。,們都大力強調此詩是周公對東征將士自上而下的慰問體貼,目的則在于讓他們和更多的民眾心悅誠服,既不怕苦也不怕死地聽從統治者(“上之人”)的驅遣,使國家和政權得以鞏固。他們的政治目的很清楚,這指導了他們對詩的分析,使他們把《東山》解釋為周公對將士的慰問。可是,如果把《東山》讀成征戍者之歌,那么我們聽到的就是從征者的聲音,就能體味到他們心中的悲苦和怨恨,這些苦恨的矛頭恰恰是指向包括周公在內的統治者。解讀者的立場和感情與作品內涵的關系極大,而他們對作品敘述視角、敘事聲音的理解和判定則可以說是一個敏感的切入口。
除第一、第三人稱視角的敘述外,風詩還有一些特殊的敘述方法。
對話敘事,通過對話表現出某種情節和故事,并激活人物形象。有全盤對話,如《鄭風·女曰雞鳴》,如果用新式標點可以寫成這樣:
女曰:“雞鳴。”
士曰:“昧旦。”
“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將翱將翔,弋鳧與雁。”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齊風·雞鳴》也是一對夫婦的床上對話,具體內容與《鄭風·女曰雞鳴》不同,而且形式也有區別,連開頭的“女曰”“士曰”都省略了,兩個人的聲口卻聽得明明白白: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
“匪雞之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
“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會日歸矣,無庶予子憎。”
兩篇都是夫婦起床前的對話,沒有另外的敘述,所言之事不同,形成了情節的差異,夫婦情濃則兩篇一致且表現得很充分,實際上形成了一個戲劇性場面。這個場面看似真實,實乃虛構,但很典型。這樣的篇章抒情色彩當然濃厚,但情是從對話和人物行為中表達出來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主題的揭示也是在這其中完成的。朱熹的解說頗中肯綮,他說前一首是“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后首是賢妃聞蒼蠅之聲而心存警畏,提醒君王莫耽逸欲,“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兩處用了“敘述”字樣,顯示他對詩歌敘事的藝術感受(15)朱熹集注:《詩集傳》,第51、58頁。。若以敘事學術語言之,這兩首詩的對話,前者因點明是誰所說,有如間接引語,而后者則是未曾點明說者的直接引語,小說中最常用之。二者均是詩歌作者借其塑造的人物之口所表達,對話具有表演性、場面感,是詩歌語言戲劇化的表現,也是兩種值得注意的詩歌敘事手法。
也有詩歌用部分對話、片段對話來敘事。
如《邶風·擊鼓》先敘從軍赴戰,后言“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在回憶中引出當初的誓言,昔日情景可見。
如《王風·大車》末章“榖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是在客觀敘述之后的加強表達,這四句是女子未必說出口的強烈心聲。
如《鄭風·溱洧》先寫春日游玩,男女相會,再寫“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同游士女開心說笑,如在眼前。接下去便是“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了。
如《魏風·陟岵》,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以及“母曰”“兄曰”的類似話語,此為詩歌主體,但均在游子登高眺望的敘述之后。
至于《魏風·伐檀》則在描述辛勞伐木后,道出“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狟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的怨言。
這些對話既是故事中人物的聲音,也是人物行為的一部分,從而也就構成了整個故事情節的一部分——抒情詩中的敘事部分。
更有戲劇性場面的營造,使敘述向表演發展,顯示了抒情詩敘事主體的非單一性以及人物的多樣性。《鄭風·將仲子》《魏風·碩鼠》皆以主人公獨白及其未出場的受述者一起構成戲劇場面,如畫面,亦如影視。上面已涉及,不再贅論。尚可另舉《魏風·園有桃》一例,其詩云: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16)朱熹集注:《詩集傳》,第64頁。
這首詩的抒情人“我”是一位落魄士人。他生活潦倒,飲食難繼,卻還在憂國憂民,不滿現實,自我清高(所謂“我歌且謠”,內容應與此有關),于是為一般人所不理解,遭到揶揄批評,被說成驕傲、荒唐。處境如此,不能不引起他的思想斗爭。“人們說得對嗎?”“你自己認為怎么樣?”這樣的問題糾纏于心,反復折騰。想來想去,既無知我者,只有拋開不想拉倒!當然,完全不想是辦不到的,這只是恨極無奈之詞而已。詩意大致如此,事情原委是由士人的自述道出的。敘述中引用了外界的批評語,寫到了自己內心的無聲語——抒情人化身為另一人與自己對話——抒情詩經由敘事發生了向戲劇小品的變化,內容和表現方式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豐富。
從時間、空間的轉移變化來觀察,也是對風詩做敘事分析的一個重要方面。這種轉移變化,有時表現得比較清晰明顯,如《邶風·谷風》《衛風·氓》敘述戀愛婚姻的變故,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均有所呈現;特別是《氓》,事態的演變很有層次感,女主人公生活境遇日趨惡劣的敘述與時間地點的變化扣得很緊。這是對時空關系的直接表現。
有的則通過景物、環境的描述加以婉曲地表現。如《王風·丘中有麻》,從第一章的“有麻”,到第二章的“有麥”,再到第三章的“有李”,借植物的生長顯示時間的變化,而人物故事即發生在這過程之中:先是請劉子嗟幫忙種麻,繼而請其父吃飯,次年李熟時節,乃有女主人公接受劉子嗟贈送佩玉之事。詩雖短小,卻將季節之變、植物之變、人事情感之變融匯在一起。
例如《齊風·著》,描寫一個女子接受親迎的過程和心情,便通過地點的變換來表現。“俟我乎著乎而”,著是古代大門和屏風之間的地方,前來迎親的新郎先在這里等待,新娘初次窺見了他。“俟我乎庭乎而”,新郎來到了中庭。“俟我于堂乎而”,親迎者已進入中堂。空間的漸變與新娘怦怦的心跳就這樣應和著。敘事筆墨簡潔,但人、事、情都描繪出來了。
風詩中多“敘中抒”現象,敘述盡管樸素平實但感情傾向明顯,典型的例子如《豳風·七月》在客觀敘述一年農事過程中,抒發了農人勞作的沉重、物質生活的艱苦,乃至農家女人身無保障的憂恐。的確,沒有不帶感情的文學敘事。凡敘述,或含褒揚贊美、同情憐惜,或含諷刺鄙夷、厭惡詛咒,雖可不著一字,傾向卻難掩抑。不帶感情色彩的敘述,除非那些非文學的說明性文字,如藥物或用品的使用說明書之類。
風詩的詩面中亦有純抒情的現象,表面看來未說何事,或言之模糊隱晦,或所言只及其他,讀來難以確指其事。但即使如此,也不會真的絕對無事,而都是隱含事由之作。像《邶風·式微》《唐風·采苓》以及《陳風》的《月色》《衡門》《豳風·伐柯》,詩面均是直抒,然背后之事(服役操勞、讒言為害、男女相戀等)還是隱約透露著而并非完全不可捉摸。
總之,就一首詩整體而言,其所用語非敘即抒,完全可以分辨清楚。敘者,敘事;抒者,抒情(包括訴說主觀情緒的感慨議論)。抒敘相互支撐、相互補充加強,是一種互惠關系,但抒敘也形成博弈(聞一多謂為“對壘”)。
互惠好理解,博弈則需略說。
首先,如果從一首詩來看抒敘博弈,那就是抒敘語言成分的分配。假設全詩的總分量是“十”,那么抒敘各占幾分,必是你多我少、此重彼輕。抒敘轉換交接的方式和重心的安排是詩歌結構的關捩。一首詩是敘事成分多還是抒情成分多,其總體色彩和風格特征是不一樣的。由于抒敘各具獨特功能,詩的藝術效果亦由此而有別。敘多者往往具體可見、質實沉重,抒多者的好處是易于清空靈動,其弊則是易流于浮泛空洞。若從詩作內容的充實厚重程度而言,則往往存在抒不如敘的情況。比如《邶風·谷風》《衛風·氓》《王風·中谷有蓷》三詩均為棄婦之詞,但三詩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卻并不一樣,這里的差異即與各詩抒敘成分與結構的不同有關。章培恒先生認為《谷風》是西周后期作品:“由于這是我國的早期詩篇,在藝術上自不可能成熟,加以篇幅較長,敘述有些雜亂,這大概是詩人在感情的激動下,思緒紛沓,想到什么就傾訴什么,因而多少影響了別人的理解。”(17)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 第二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0頁。這是說《谷風》的抒情有點多而亂,造成敘事不夠豐滿不夠清晰的缺陷,從而削弱了它的表現力。章先生又指出,《氓》產生于東周,“與《谷風》相比,《氓》的結構顯然優于《谷風》,其敘述層次分明。……像這樣的在各章之間具有明晰邏輯關系的結構,在《詩經》的較長詩篇中是很少見的。在《谷風》的章與章之間,我們就很難找到此類邏輯關系”(18)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 第二版),第64頁。。精辟地點出《氓》在敘事上大有進步,其優越之處主要就在于敘述層次分明、邏輯關系清楚,特別是敘事與抒情融匯結合得好,所以讀者容易理解,并且深受感動。程俊英先生在解說《王風·中谷有蓷》時也有相關論述。她說:“同樣反映棄婦的不幸,此詩和《谷風》《氓》相比,在表現手法上有較大的差別。后者含有比較完整的敘事成分,前者則是單純的抒情。同樣是控訴男子的負心,后者是通過瑣瑣屑屑的訴說,前者則只有慨嘆悲泣。主要原因在于《谷風》《氓》是自述,《中谷有蓷》的作者是一位同情棄婦者。”(19)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204頁。程先生明確地指出《中谷之蓷》的單純抒情比不上《谷風》《氓》的敘事加抒情,并且涉及詩歌敘述人稱的問題。《谷風》和《氓》是第一人稱敘述,作者與抒情人并不是同一人;《中谷有蓷》是第三人稱敘述,作者或抒情人從旁觀角度表達了同情,其感染力稍小是很自然的。章、程兩位先生在著作時恐怕并無揚敘事貶抒情之意,但卻實事求是地觸及、論證了抒敘博弈的問題。這樣的例子在為數甚多的詩詞賞析文章中不難發現。
其次,抒敘博弈是作者個人風格形成之因。每位作者的擅長都不相同,有的善敘、有的善抒,即使處于同樣場合,面對同樣景致,以相同題目作詩,他們也會自覺不自覺地動用和發揮所長,從而寫出抒敘比重不同、風格各異的作品來。抒敘博弈就滲透在這個過程之中。
再次,抒敘博弈表現于整個文學過程,往往體現于文體的盛衰變化。古人曾云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而所論無非是各文體在不同時代的興衰起伏,所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直至近代小說戲劇類敘事文體占領文壇主流地位,都包含著抒敘博弈的結果。故抒敘博弈實乃文學創作發展的一種動力,由讀者作者共同操縱左右,使文學史、詩史呈變化無窮、波瀾壯闊的面貌。
這后面兩點涵蓋的內容超過本文論題,茲不展開論述。
《詩經》風詩乃至全部作品都可以按抒敘成分的比例排成隊列,形成一個譜系。此意聞一多先生早已揭示,見下文引述。我們試借光譜來比喻這個隊列,具體論述另有專文。簡言之,此隊列可分為含事、詠事、述事、演事四個段落,劃分的原則是詩與其有關之事的遠近、疏密、多少之關系和表現方式。尋找并論定某詩在此隊列中的位置,則可以成為對其進行敘事分析的第一步。
四、《詩經》與中國詩歌抒敘兩大傳統
《詩經》風詩每一篇都是抒敘結合體,《詩經》總體則是中國詩歌抒敘兩大傳統的源頭。抒情、敘事在這個源頭不分先后地共生著,從開始它們就是互動互惠,同時也互競博弈。
以前把《詩經》說成是一個“抒情詩傳統”,僅強調“情志”是詩歌之源,這是對《詩經》風雅頌三類作品和《詩大序》的誤解。其實,無論從《詩經》作品還是從《詩大序》都能夠清楚看到古人對詩歌敘事及其傳統的認識。但是在二者的既互惠又博弈的傳統中,抒情一端被某些人強調到了不合適的程度,而敘事一端則受到壓抑遮蔽。事實上,在中國漫長的文學史、詩史中,敘事傳統從未消泯斷絕,敘事及其傳統與抒情及其傳統始終共存同在,而且二者不時互有起落升沉,形成波動不息的浪潮,涌現出杰出的代表人物。最為民眾所熟悉的,便是被稱為“詩史”“詩圣”的杜甫。杜甫在新樂府運動之前,就弘揚了《詩經》風雅和漢代樂府的傳統,直接啟發引領了元稹、白居易為首的新樂府運動。以后歷代詩壇均回響著以老杜元白為代表的抒、敘共榮傳統與單純抒情傳統的博弈之聲,直到今日這種博弈仍在走向深入而未曾止歇。
聞一多先生八十多年前在《歌與詩》一文中闡發論證的觀點,涉及詩歌的抒敘對壘、抒敘的互惠博弈、詩歌抒敘博弈的發展變化及其歷史意義,至今沒有人把問題說得如此明晰、如此深刻透徹,完全可以作為我們繼續深入研究的理論綱領。茲引錄聞先生所論與本文有直接關系的兩段文字如下:
第一段,講清楚了歌與詩、抒與敘二者原初的區別與關系:
上文我們說過“歌”的本質是抒情的,現在我們說“詩”的本質是記事的,詩與歌根本不同之點,這來就完全明白了。再進一步的揭露二者之間的對壘性,我們還可以這樣說:古代歌所據有的是后世所謂詩的范圍,而古代詩所管領的乃是后世史的疆域。……原來詩本是記事的,也是一種史。在散文產生之后,它與那三種(指《書》《禮》《春秋》)僅在體裁上有有韻與無韻之分,在散文未產生之前,連這點分別也沒有。(20)聞一多:《聞一多全集》第一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第187頁。
第二段,更精粹深刻地論述了《詩經》,特別是風雅二體作品抒敘博弈演變的歷史過程和巨大意義,為中國詩史與文學史的變遷勾勒了角度獨特、視野開闊而線索鮮明的軌跡,給我們以無窮的啟發:
詩與歌合流真是一件大事。它的結果乃是《三百篇》的誕生。一部最膾炙人口的《國風》與《小雅》,也是《三百篇》的最精彩部分,便是詩歌合作中最美滿的成績。一種如《氓》《谷風》等,以一個故事為藍本,敘述方法也多少保存著故事的時間連續性,可說是史傳的手法,一種如《斯干》《小戎》《大田》《無羊》等,平面式的紀物,與《顧命》《考工記》《內則》等性質相近,這些都是“詩”從它老家(史)帶來的貢獻。然而很明顯的上述各詩并非史傳或史志,因為其中的“事”是經過“情”的泡制然后再寫下來的。這情的部分便是“歌”的貢獻。由《擊鼓》《綠衣》以至《蒹葭》《月出》是“事”的色彩由顯而晦、“情”的韻味由短而長,那正象征著歌的成分在比例上的遞增。再進一步“情”的成分愈加膨脹而“事”則暗淡到不合再稱為“事”,只可稱為“境”,那便到達《十九首》以后的階段,而不足以代表《三百篇》了。同樣,在相反的方向,《孔雀東南飛》也與《三百篇》不同,因為這里只忙著講故事,是又回到前面詩的第二階段去了,全不像《三百篇》主要作品之“事”“情”配合得恰到好處。總之,歌詩的平等合作,“情”“事”的平均發展是詩第三階段的進展,也正是《三百篇》的特質。(21)《歌與詩》,文后署“二十八年六月一日”,初刊于《中央日報》1939年6月5日(昆明版)副刊《平明》第16期。文末注云:“這是計劃中的一部《中國上古文學史講稿》的一章。關于‘歌’的問題,不是與浦江請先生那一夕談話,我幾乎完全把它忽略了。論‘詩’部分,則得益于朱佩弦先生的《詩言志說》(載《語言與文學》第一集)者不少。謹此向二位致謝。”聞一多:《聞一多全集》第一冊,第190頁。
今日重讀,真是感慨萬千。聞先生曾對《詩經》下過大功夫,以上所論則為深入淺出之言,也可以說是真正“回歸到文學”的研究,值得我們結合聞先生的《詩經》研究做系統認真的學習,而不應該無端將此文設為“公案”,甚至樹為批判的靶子。